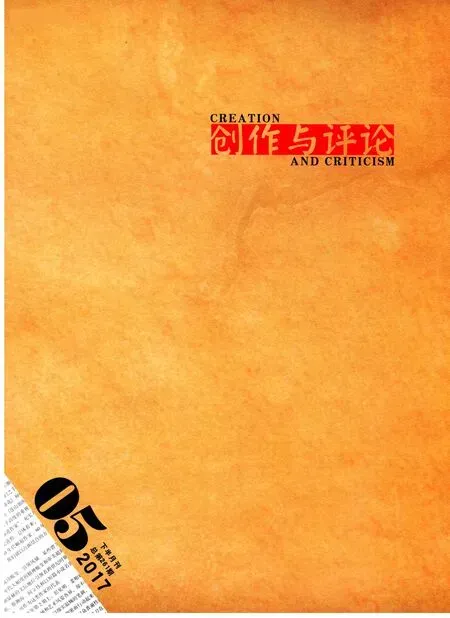『文學湘軍』的跨世紀格局與全國性定位
○劉起林
『文學湘軍』的跨世紀格局與全國性定位
○劉起林

劉起林
1963年生,湖南祁陽人。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浙江大學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與文學思潮研究,發表學術論文16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勝景與歧途:跨世紀文學的多維審視》《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主編著作《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論文集《文學“馬拉松”——<李自成>出版五十年研究文選》等,合著《湖南文學史(當代卷)》。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項、省部級課題6項。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第14、15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中國文聯、中國評論家協會的“2016年度中國文藝評論優秀作品”著作獎等多個獎項。
“文學湘軍”是社會各界對湖南作家“隊伍”一個約定俗成的稱謂。這個名號在中國文壇的流行,源于20世紀80年代前期湖南文學的豐富成果和廣泛影響。難以考察“文學湘軍”的名稱第一次使用于何時、何處,也很難說形成這一稱呼的思維定勢是否與曾國藩所創建和統率的、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命運的“湘軍”有關。但在新時期以來30余年的湖南文學發展歷程中,“文學湘軍”的稱呼一直被沿用著。從概念外延的角度看,雖然官方的各種文件和報告常用“文學湘軍”來統稱湖南的整個文學創作隊伍,但在社會文化層面,“文學湘軍”的稱號往往特指湖南小說作家群,人們提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湘軍”的輝煌,主要也是指當時的湖南小說頻頻獲得各類全國性文學大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難以看到“散文湘軍”“詩歌湘軍”等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學湘軍”中成規模的存在,湖南的兒童文學源遠流長又在全國卓具影響,官方文件之外對“文學湘軍”的稱呼中,也少見將其囊括于內的現象。
湖南當代小說創作是從相當薄弱的基礎起步的,20世紀50年代作家隊伍未成陣勢,60、70年代成就和影響上臺階,處于創作活躍、積累充分的狀態,80年代形成“文學湘軍”并創造了頻頻獲獎或廣受爭論的創作輝煌,又于90年代前期陷入審美的困境與創作的低谷。短暫的沉寂之后,以隊伍分化、代際更替和精神突圍、審美開拓為表征,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紀前十余年的跨世紀時期,“文學湘軍”建構起了創作的新格局和審美的新風貌。
一、“文學湘軍”的跨世紀格局及其審美風貌
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文學湘軍”就不斷地出現著一些“新進作家”,湖南文壇具有或大或小全國性影響的作品,已更多地出自他們之手。從20世紀90年代前期唐浩明的《曾國藩》、閻真的《曾在天涯》、何頓的長篇小說《我們像葵花》和中篇小說《生活無罪》,到90年代中后期王躍文的《秋風庭院》和《國畫》、向本貴的《蒼山如海》、陶少鴻的《夢土》,無不如此。“江山易手無人識”,文學界和學術界對此未曾給予高度的重視,仍然在為那些作家的流失而遺憾和沮喪。但正是這此起彼伏地登上文壇的“新進作家”,充實乃至重構了“文學湘軍”的審美陣營,開啟了湖南文學“跨世紀”轉型的歷史進程。總體看來,“文學湘軍”在“跨世紀文學”時期,表現出一種80年代實力派作家、90年代崛起作家、60年代出生作家和湖南文壇“散兵游勇”各呈異彩的創作陣營和審美風貌。我們就以點面結合的方式,來對“文學湘軍”的這種新狀態略加勾勒與概括。
其一,20世紀80年代實力派作家成功蛻變、引領風騷。某些曾為20世紀80年代湖南文壇“大兵小將”的實力派作家,在90年代大幅度的精神蛻變和審美超越之后,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生命力,以堅實的創作成果和顯赫的文壇地位引領著跨世紀時期湖南文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80年代曾獲全國性文學獎的彭見明、蔡測海、何立偉和以短篇小說名世的聶鑫森,以及曾為“湘軍七小虎”成員的陶少鴻、姜貽斌,可作為這類作家的代表。
在《時代文學》雜志的2000年第2期上,彭見明、姜貽斌、陶少鴻曾共同做了一個短篇小說“三人行”專欄。這組小說審美內涵和藝術風姿各異,卻不約而同地顯示出“文學湘軍”進行新型審美探索的征候。彭見明的《說說》以綿實溫婉的筆調,有條不紊地敘述了主人公老安為兒子說情的過程。對他那有心無膽、盤算時急切細密而行動起來則羞怯茍且的窘態,給予了充滿體諒和同情之心的敘述,從中精微地揭示出一種弱勢民眾普遍性的心理和行為習性。作品的著眼點顯然是不良的社會風氣,作者表現時卻并不鋒芒畢露、單刀直入,而是選擇老安這么個古板、懦弱而自矜的老頭為表現對象,對他被逼無奈時的出擊欲望加以細細描述,從而寓內在的緊張于閑散從容之中,曲折迂回地表達出殷殷的關切之情和憂患之心。姜貽斌的《老古釣魚》運用亦莊亦諧的、“閑話”式的筆調,表現的也是自命清高、優越的主人公在這功利時代欲行又止、尷尬迷惘的弱勢狀態。作者不從正面挑開讀書人清淡無為的心理和世俗實利化的生存現實之間的緊張矛盾,而是通過老古不愿使自己“將釣下的魚送人”的詩意化行為,從人情民心的細微處,透露出時代重大問題的信息。陶少鴻的《幸福一種》所表現的,則是下崗職工夫妻在艱難辛酸中的忠誠與體貼。作者從處于弱勢狀態的丈夫的角度落筆,從而使小說因其猜疑形成了波瀾,由其釋疑氤氳著溫情。初看起來,這似乎是一般性渲染情感的小說所慣用的構思方式,但如果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現實主義沖擊波”里大量從基層行政管理角度入手的作品略加比較,我們就會感到這篇小說獨特的藝術智慧;如果放到“文學湘軍”的審美傳統中加以考察,我們則更會感到這種藝術特色絕非偶然。
在這組作品中,彭見明、姜貽斌、陶少鴻這些“文學湘軍”特色鮮明的作家,共同體現出一種駐足邊緣、關懷弱勢的精神人格風貌。其中充分表現出,湖南作家既具見識、勇氣和歷史責任感,密切地關注現實、跟蹤時代,注重作品主題內蘊的社會性和價值目標的功利性;又有靈動的藝術才情和表現智慧,寓時代風云于人情民心畫卷,從底層生態出發折射時代,堅持側面表現、講究藝術情趣。這種審美視野和精神眼光,確實既深刻地傳承了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文學審美傳統,也高度契合了“文學湘軍”和湖南社會文化在中國精神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具體說來,湖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客觀情勢,使湖南作家在時代大潮中必然地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都市文明的發展,則使他們把審美注意力由鄉村的風景風情轉向了社會覆蓋面更廣泛的世態人心;而自身邊緣、柔弱的文化處境,又使湖南作家們容易對各種生存環境中的弱勢群體產生一種天然的親和心理與共鳴感。實際上,這正是“文學湘軍”成功地化社會文化劣勢為審美文化優勢的精神關口之所在。
果然,在“跨世紀時期”的20余年時間里,彭見明的《玩古》《鳳來兮》《天眼》和《平江》等境界和底蘊獨具的成熟之作,一部接一部穩健地推出;陶少鴻審視鄉土滄桑的《夢土》《少年故鄉》和展現時勢創傷的《溺水的魚》《花枝亂顫》并呈于世;何立偉既有長篇《你在哪里》《像那八九點鐘的太陽》,又有中篇《老康開始旅行》《老何的女人》,由詩意入世俗,由簡約而恣肆,在咀嚼躁動與失落中哀挽著淳真;姜貽斌的創作靈動機敏、多方探索,終至《火鯉魚》的自我藝術高峰;蔡測海精研細磨、苦吟細品,慢工出細活,以《非常良民陳次包》和《家園萬歲》后發制人;聶鑫森的短篇小說漫天開花,審美境界中蘊含著豐厚的文化修養和敏銳的文化意識。他們各以自我不同于流俗的創作,體現和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的湖南實力派作家在精神蛻變之后所能達成的審美境界與藝術高度。
其二,20世紀90年代崛起作家積累厚實、開拓雄健。在“文學湘軍”的跨世紀審美陣營中,也有一些作家年齡與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不相上下,但他們或者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創作而一鳴驚人,或者長期艱苦磨練而到世紀之交才尋找到具有突破意義的審美空間,他們也處于跨世紀時期湖南文壇的主流位置。其中一鳴驚人的唐浩明、閻真和磨練有成的向本貴、鄧宏順,當屬這一類作家的代表。
唐浩明以長篇歷史小說著稱于世。《曾國藩》轟動海峽兩岸,作品全面展開了清朝末年社會動蕩、文化轉型的歷史情境,內蘊豐滿地呈現出中國近代歷史生活所體現的傳統文化蘊涵,進而深刻揭示了主人公個體人格美質與時代環境錯位所導致的奮斗意義迷失、生命價值失落的人生悲劇。隨后,唐浩明又創作出《楊度》《張之洞》兩部同樣卓具影響的優秀作品,以正史之筆,敘廊廟之音,在遼闊的歷史與文化時空中發掘出王朝衰變期獨特的功名文化人格。《曾國藩》《楊度》《張之洞》這“晚清人物三部曲”,成為了當代歷史題材創作從革命文化認知向執政文化審視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代表作。
閻真致力于探究中國社會轉型期典型性人生的命運狀態和生命意義,作品兼具深邃的思辨色彩和濃郁的藝術情韻。《曾在天涯》以驚人的坦誠和透徹,用如泣如訴、一唱三嘆的筆調,敘述了主人公在極為卑微的生存搏斗中身心交瘁而孤苦無告、欲罷不能的人生境況,展現了主人公心靈的膨脹與萎縮矛盾到滑稽程度的精神狀態和由此生成的精微的生存體驗、渺遠的生命遐想,痛切地揭示了20世紀中國漂流海外的最后一代知識分子處于生命意義懸浮狀態、找不到生存的背景和依據,卻又驚恐于時代的陰影而急功近利,結果只能是“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的生命狀態,作品在20世紀中國留學生文學中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后意義。隨后,閻真一步一個腳印,官場題材的《滄浪之水》、女性題材的《因為女人》和高校教師題材的《活著之上》均以深刻的揭示和痛切的思辨震撼文壇,在整個中國文壇都頗具精神空間的開拓與創新意味,成為“跨世紀文學”同類題材創作的優秀代表作。
向本貴、鄧宏順都是以深厚的生活實感和深刻的農村社會體察而撼動文壇的作家。向本貴的《蒼山如海》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期的“現實主義沖擊波”中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他隨后又創作了《盤龍埠》《鳳凰臺》《遍地黃金》等眾多表現當代農村、礦山歷史命運和現實狀況的憂患之作。鄧宏順的《紅魂靈》通過一對農村基層干部父子的矛盾,深刻揭示了當代政治文化遺產帶給時代新生活的沉重負面影響,他的《貧富天平》《天堂內外》顯示出更為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剖析力度,《鐵血湘西》則將審美的眼光深入到了20世紀湘西歷史風云的遼闊藝術時空。向本貴、鄧宏順都是從農村生活的深層有力地崛起的作家,他們的創作遠遠超越了那種風情與民生融為一體的、“嚴峻的牧歌”式的審美思路,對于當代農村復雜矛盾與艱難時世的正面展開和層層剖析,以及蘊藏于其中的生活的厚重感、內涵的充實感和農村基層干部式的責任意識、體察情懷,使得他們的創作顯示出一種“詩史”性質的藝術品格。
“文學湘軍”中的20世紀90年代崛起作家不管與當代湖南文學的“周立波傳統”和80年代湖南文學的審美思路存在怎樣的關聯,創作中都顯示出一種嶄新的審美氣象和文化氣息,他們的作品極大地開拓了湖南文學的審美境界,也在整個中國文壇獲得了良好的反響。
其三,20世紀60年代出生作家群為“文學湘軍”帶來了新的審美活力和強大的創作后勁。跨世紀時期的湖南文壇還崛起了“文學湘軍”的新一代,他們就是世紀之交的湖南文學界曾以“湖南20世紀60年代出生作家群”命名的一群青年作家。他們大多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嶄露頭角,而到新世紀大放異彩,成為湖南文壇的的中堅力量。在小說創作方面,20世紀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可以王躍文、何頓、薛媛媛、肖仁福作為代表。
王躍文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中篇小說《秋風庭院》被頻頻轉載并入圍首屆“魯迅文學獎”,他的長篇小說《國畫》《梅次故事》等作品更在世紀之交成功地開創了“官場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審美道路。新世紀以后,王躍文既以《西江月》《蒼黃》等官場現實題材作品繼續引領官場小說的風潮,又以充滿文化訓誡意識與人格示范色彩的歷史官場小說《大清相國》享譽中國政壇和文壇。鄉土生態題材的中篇小說《漫水》和社會心態透視的長篇小說《愛歷元年》,則表現出王躍文開拓多種創作題材和審美思路的藝術魄力。
何頓是一個創作相當豐富的多產作家,他早期的作品如《生活無罪》《我們像葵花》等,著力展示都是底層青年的生存欲望、蓬勃生機和價值邏輯,成為中國社會世俗化、欲望化生態的藝術表征。新世紀以來,何頓的《黑道》《時代英雄》等作品在都市生態揣摩方面愈發深入和豐富;他還以強烈的人文責任感和深刻的悲憫情懷,開拓了在世紀性的歷史視野中塑造和謳歌國民黨“抗戰老兵”的審美境界,三部曲《湖南騾子》《來生再見》《黃埔四期》有力地強化了新世紀抗日題材文學創作的歷史認知厚度和精神探索深度。
薛媛媛早期的《外婆》《銬在電線桿上的黎太階》等小說,在歷史滄桑和人性狀態相交融的視野中體察人物的生命欲求與苦苦掙扎,顯示出將風俗民情性人生場景的描述和人物苦澀幽怨、尋求解脫心態的刻畫融為一體的特色。新世紀以來,她的創作日益精進,《湘繡旗袍》等中短篇小說反響良好,長篇小說《湘繡女》和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則獲得了更大的全國性聲譽。
苗族作家肖仁福的初期作品語言精致,具有鮮明的鄉土氣息和民族色彩,小說集《簫聲曼》曾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肖仁福進入“官場小說”的題材領域,《官運》《心腹》《仕途》《家國》《平臺》等大量作品既具良好的圖書市場效應,也引起了文壇一定程度的關注。彭東明的《故鄉》《最后家園》等中、長篇小說,或者以洞庭水鄉的人事為題材,或者以家鄉連云山的變遷為重心,均顯示出較為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一定的歷史厚度。劉春來的《銅鼓坡紀事》《水災》等長篇小說既著意傳承周立波創作的藝術神韻,又顯示出對新的社會現實的關切。
20世紀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家同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湘軍”一樣,大多出身于社會底層,其中多數來自農村,有過貧苦的童年和奮發的青少年時代。但他們又不像20世紀80年代的前輩作家那樣長期沉浸于鄉土基層,而是迅速通過高考等途徑,以鄉村才子的聰慧和堅韌躋身于城市社會。這種人生歷程及相關的社會閱歷,使他們形成了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湘軍”的重要精神特征。首先,勇敢的闖蕩、顯眼的人生位置和不斷豐富的生活閱歷,使他們思想視野開闊、時代感觸敏銳,對社會的體察也日漸深入。其次,作為橫跨城鄉的“兩棲”人,他們在價值選擇方面,顯示出農村人美德意識和城市人名利心兼而有之的特征;在心理上,他們又總是自覺為鄉村的遠行人和都市的漂泊者,即使在城市找到了生活的位置,也難以具備別無它想的安身立命感,精神心理的迷茫和生命意義的探索就成為他們內心隱蔽而執著的企求。再次,這批作家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不僅作品的書卷氣息、文化意味超過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湘軍”,對于地域文化的反省和超越意識也顯得相當自覺;但另一方面,湘楚地域文化的浪漫情韻和近世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特征,當代湖南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和濃郁的地方色彩,也深深浸染于這批作家的創作之中,使得他們的作品命意具體、包容實在而又總是氤氳著靈秀之氣。正因為如此,他們在世紀之交雖然還只是一個正在成熟過程的作家群體,但發展的大好前景和對于湖南文學的巨大推動作用,在當時就已從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來;新世紀之后,這批作家中的優秀者就大多表現出更為雄健而堅實的發展。
其四,“散兵游勇”性質的作家常給人以意外的驚喜。在跨世紀時期的湖南文壇,還存在著數量不菲的“散兵游勇”和“基層作者”性質的作家。他們也大多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創作,但隨后在文學創作上就長時間地銷聲匿跡或成績平平。因為與文壇主流缺乏緊密的聯系,這類在20世紀90年代后反而能夠“輕裝上陣”,直面歷史與人性的隱秘。其中眾多基層作家的文學成果夯實了湖南文學的審美與文化基礎,優秀者則不時會出人意外地脫穎而出,拋出他們令文壇刮目相看的優秀之作,表現出一種“散兵游勇顯神威”的藝術風姿。永州作家王青偉的長篇小說《村莊秘史》和《度戒》、懷化作家李懷蓀的《湘西秘史》、婁底作家小牛的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秘方》,正是這種出人意外地或深邃、或厚重、或別致的作品。從生活出發、從對歷史和人性認識的深化出發,是這類作家顯得別具生氣與情懷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給予湖南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界的重要審美啟示。
所以,“文學湘軍”在跨世紀時期的隊伍重構,實際上是湖南文學發展一種重要的歷史性轉型。在經歷了這種巨大的轉型與重構之后,湖南的作家們很快就以豐富的境界開拓和堅實的創作實績,顯示出湖南文壇的審美新氣象,從而獲得了繼20世紀80年代“文學湘軍”之后、湖南文學又一輪沉甸甸的創作收獲。
二、世紀之交:耐人尋味的“湖南長篇現象”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文學湘軍”即以創作隊伍的新格局顯示出一種審美的新氣象,尤其在長篇小說創作領域,更呈現出佳作迭出的文學景觀;但文壇內外并未對這種成果給予應有的關注與重視,更未根據新形勢及時調整視角和思路,來重新打量與估價“文學湘軍”。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和鮮明對照,構成了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中國文壇耐人尋味的“湖南長篇現象”。
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湘軍”的長篇小說堪稱群星閃耀。唐浩明剛以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轟動海峽兩岸、文壇內外,《楊度》又連獲第10屆“中國圖書獎”、第3屆“國家圖書獎”和“八五期間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彭見明的《玩古》與《楊度》1998年同進“八五期間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20部入選作品之列;向本貴的《蒼山如海》先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既而又名列“向建國50周年獻禮10部優秀長篇小說”。另外,唐浩明的《楊度》和陶少鴻的《夢土》雙雙入圍第5屆“茅盾文學獎”的25部終評備選篇目;閻真的《曾在天涯》不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海外版,并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3屆“人民文學獎”提名獎;王躍文的《國畫》則暢銷得使全國各地的盜版者也大發了一筆橫財,以至文壇有人稱1999年為“王躍文年”。
2001年更是湖南長篇小說創作的豐收之年。僅在權威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有4位湖南作家的作品被隆重推出,即唐浩明的歷史小說“壓卷之作”《張之洞》、劉春來的《水災》、閻真的《滄浪之水》和王躍文繼《國畫》之后的又一部長篇小說《梅次故事》。而且,《張之洞》在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同時出版發行,還繼《曾國藩》獲得第一屆獎項后,又獲得了第二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水災》和《滄浪之水》均被《當代》以全文發表的形式刊載。此外,向本貴在這一年之內同時出版了《盤龍埠》和《遍地黃金》兩部長篇小說,并分別由福建省委宣傳部和作家出版社推薦為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備選作品。
應當說,在短短四五年的時間里,如此清一色的長篇小說,取得如此的關注與反響,比起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文學湘軍”,即時效應并不遜色什么。即使是20世紀90年代最為震動中國文壇的“陜軍東征”現象,5部作品中也就是《白鹿原》和《廢都》卓立文壇,不僅佳作規模有所不及,整體水準也很難說比世紀之交的湖南長篇小說就高出了多少。
再以文壇口碑而論,歷史小說創作是唐浩明、二月河齊名;“主旋律”作品“北有何申,南有向本貴”;百年反思題材,曾經《繾綣與決絕》《夢土》并列;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則《羊的門》《國畫》媲美……應當說,在不少的題材領域,湖南作家都已經在領中國文壇一時之風騷。而且,“并列”“媲美”的另一端往往來自北方的不同省份。二月河與《羊的門》的作者都是河南人,何申則是河北的,《繾綣與決絕》的作者趙德發卻出自山東,湖南作家竟然以一省的分量,扛起了這些“并列”“媲美”的一端,這令入不能不刮目相看。
更進一步從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角度來看,因為時代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前期“文學湘軍”的獲獎作品多為中短篇小說,而且無論長篇還是中篇、短篇作品,都有不少如今已黯然失色。世紀之交的湖南長篇小說最終命運如何,當然誰也不敢先知先覺地預料,但至少在超越單一的政治話語模式、思想藝術時空大大拓展、作品內蘊更為深廣厚實等方面,這一批作品具有20世紀80年代“文學湘軍”的作品所無可比擬的優長。
客觀事實充分說明,世紀之交“文學湘軍”已經從長篇小說量的豐富和質的優異雙重角度,構成了湖南文學的新輝煌。但是,從中國社會文化領域、中國文壇到湖南文學界,卻一直既無人從橫向角度,將這一時期的湖南長篇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刮目相看”,也無人從縱向角度,歡呼“文學湘軍”已經重新崛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失察”的現象呢?其中的意味確實耐人尋味。
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文學湘軍”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名噪一時,大致源于以下因素:第一是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巨大熱情和全力關注;第二是連年舉行的全國中短篇小說獎和同期舉行的“茅盾文學獎”;第三是文壇一浪接一浪且具全局性影響力量的文學思潮;第四是“文學湘軍”的作品均具鮮明的地域風情色彩和地方文化特征。天時、地利、人和加上自身內在素質同時起作用,當時的“文學湘軍”形象才顯得異常鮮明強烈,使人極易捕捉。
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文化和中國文壇的狀況,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評獎體系和機制的復雜、混亂所導致的獲獎作品聲譽的貶值,影響了湖南長篇小說形成“亮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出現了許多評價標準、運作方法和評獎部門皆不相同的與文學相關的獎項。全國性的獎項就有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出版部門的“國家圖書獎”和“中國圖書獎”,文壇內部的“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以及在社會歷史進程的重大關頭臨時組織起來的“獻禮”性優秀作品遴選,等等。各大出版社和文學刊物也大都有從自身角色出發的評獎。種種其它部門和民間群體還時常基于各不相同的背景與動機,弄出自己的評獎與排行榜。在開放的時代、多元的社會,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是,獎項既多,反而難以如20世紀80年代那樣,一旦哪部作品獲獎,即成眾星捧月之勢;獎項太雜,又往往令不明內情者覺得眼花繚亂,有所研究者則多半會對許多獎項與獲獎作品不以為然。而且,這些獎項各有各的評選標準,雖然可能互相影響,卻極難獲得全面的相互認同。某些獎項還時時因各種緣故大搞“平衡”、妥協,以致評不出已入圍作品的最優秀者,并不時爆出謠傳或確實存在的“暗箱操作”現象。媒體對這些獎項評獎過程和結果的評價與介紹,亦難以具有公允、穩健、獨立的品格和全局性的眼光,總有許多因價值立場的差異和自我炒作的需要而立論偏激、最終攪亂了大勢的文章“火爆登場”。結果,各種獎項的信譽度、權威性和受關注的幅度、程度,就都不能不大打折扣。
湖南的長篇小說獲獎雖多,但這種因評獎機制的復雜、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社會心態所造成的獲獎作品聲譽貶值的損傷,它們都無法避兔。而且在諸如“茅盾文學獎”這樣文學界內部認同面較廣的獎項面前,“文學湘軍”的作品又總是以一步之遙功敗垂成。結果,湖南作家即使相當優秀的作品也難以形成真正的“亮點”,最終為無心者與挑剔者所忽視也就在所難兔。
其次,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取向及其相互之間矛盾對峙、各有偏頗的狀態,這是湖南長篇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受到漠視的更為內在的時代原因。
世紀之交的中國呈現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足鼎立之勢,文學作品也相應地出現了“主旋律文學”“純文學”和“暢銷書作品”三種類型。它們雖然各有所長,難以互相取代,但極少有作品能在三大文化板塊內皆一致叫好,不少作品由此遭遇的褒貶與熱情程度甚至大相徑庭。在此情勢之下,一個地域的一批優秀文學作品如果處于同類文化的精神時空,自然極有可能因該類文化勢力的推崇與運作,而形成一種眾人矚目的地方性文學整體效應,“陜軍東征”現象、河北的“三駕馬車”、南京等地的“斷裂”作家群等等現象,就都是這樣。
令人遺憾的是,世紀之交的湖南長篇小說并非如此。具體說來,《蒼山如海》《水災》屬“主旋律文學”,《夢土》的價值基礎是傳統農耕文化;《曾國藩》《楊度》立足傳統廟堂文化立場,《曾在天涯》《滄浪之水》卻注目于個體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玩古》以對民間消閑文化的描摹取勝,《國畫》承接的是20世紀初中國市井譴責小說的衣缽……這就是說,湖南長篇小說創作的個體性精神特征,未能在客觀上形成一種集群性的地方文化色彩。同時,20世紀80年代前期“文學湘軍”所擁有的地域風情色彩,在這批作品中也因精神視野、思維重心的超越而不復存在。因此,湖南長篇小說自然就難以給人以頗成“陣勢”的印象,難以形成整個社會和文壇聚焦于此的傳播效應。
再次,評論屆的浮躁、狹隘心態和自我中心意識,以及由此導致的時代全局感、社會整體性學術視野的匱乏,則是湖南長篇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受到忽視的直接原因。
文學批評本應以“撥云見日”、發現和研究優秀作品與重要文學現象為己任,但當今中國的文學批評看起來風風火火,在電視、網絡、大小報紙、評論和學術刊物上漫天開花,實際上,因為每年出版和發行的文學作品實在太多、太千奇百怪,各地負責和不負責的評論也太多、太雜和太濫,以致一般性的評論與炒作并不能真正引起社會的關注。不管是學理批評還是媒體批評,在文壇和社會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擁有決定性話語權的,其實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幾個已經形成“品牌效應”的批評家群體,以及某些機敏勤奮而常常“語不驚人死不休”、且占據了“有利地形”的青年文學批評工作者。在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和權威性的一些文學評論報刊上,基本上是他們的聲音和傾向。其他各種文學評論的“地方隊”和“散兵游勇”,即使批評文章確實精湛貼切,對推出優秀作品也難以起到無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立場、視野、精力和社會聯系的局限,幾個“品牌”型的批評家群落,事實上不可能對每個省的文學發展狀況都有準確、細致的把握。他們所關注的大致是這么幾種類型的作品:首先是已形成“品牌”而思想立場、藝術趣味較為投合的作家的作品,其次是社會和文化思潮的熱點、趨向范圍內的“風頭”性作品,再次是各方面信息均相當看好且已在全社會形成包括發行量在內的良好影響的作品,以及“哥兒們”的有特色的作品和各種“問題作品”。這樣,以他們為中心而處于“邊遠地區”且無人緣聯系的作家的優秀作品,就只有在評介和口碑的“累積”達到相當程度時,才有可能被他們納入批評的視野,成為“全國性”的優秀之作。如果這種“累積”的厚度或速度不夠,以致他們還來不及對其進行關注,其它的“耀眼”之作就又出現于文壇,那么,這些作品就只有令人沮喪地被淘汰“出局”。
湖南省長篇小說佳作的命運正是如此。就筆者所知,世紀之交的湖南長篇小說中,只有《滄浪之水》的評介頗為成功,因為在北京獲得了幾乎所有“重量級”評論家的推崇,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又獲得了以文學博士群體為核心的青年評論家們的普遍看好,于是一時之間,篇幅長短不一的各種評論撒遍了全國的大報小刊。其他的湖南作家作品即使評介較多,也難以和全國其他省份的同類作品相比。《蒼山如海》很幸運地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創作與評論》等報刊上均有評論,但比起文壇內外對河北“三駕馬車”和湖北劉醒龍作品的連篇累牘、經久不息的長文研討來,無疑大大地遜色。《楊度》的評論亦曾稀稀拉拉地散見于《小說評論》《中國圖書評論》《創作與評論》和《文藝報》,不過,它既未享受到劉斯奮的《白門柳》出版煌煌近40萬言的研究論文集《名家評說〈白門柳〉》的“殊榮”,更比不上大報小刊對二月河“落霞系列”小說熱火朝天的炒作。另外一些同樣相當優秀的作品,則或者因重意蘊而鋒芒內斂,如《玩古》;或者其實會被青睞而“聯系渠道不暢”,如《夢土》;或者因受到體制制約而難以“組織”評介,如《國畫》,最終都未能及時進入上述幾個批評家群落的學術視野核心區域,這些作品除了在湖南省文聯的評論刊物《創作與評論》上有長篇評論外,別的報刊都只是零星地、附帶地提及。結果,雖然作品的質量并不遜色,事實上這些作品都未曾引起各個“品牌”型批評家群落的熱切關注。這些群落沒有一擁而上“開口說話”“集體發言”,就無形中使人們產生了相關作品在文壇“分量不夠”的錯覺,一部接一部的作品老是這樣“分量不夠”,湖南長篇小說整體在全國文壇的地位,又怎會變得舉足輕重呢?不能不說,這既是評論界的輕率,也是湖南文學界和湖南作家的落寞與悲哀。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的整體情勢,顯示出一種體制內話語權弱化、公共社會的話語空間漸成強勢的歷史走向,而且還生發出一種表面喧囂多元而實質上價值標準無主流、批評話語無全局性視野的不健康的癥狀。“湖南長篇現象”的出現,正源于這種話語權轉換與病態、畸形現象并存的時代語境的遮蔽。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除北京、上海等地外,其它取得較大創作成就的省份,整體方面相繼被概括出了陜西的“陜軍東征”、河北的“三駕馬車”、河南的“中原突圍”等等文學現象;個體方面,山東張煒、趙德發、畢四海、劉玉堂、尤鳳偉等人的優秀長篇,湖北池莉、方方、劉醒龍、鄧一光等作家的長、中、短篇佳作,都是一問世即獲得各方面大量的重頭評論。只有“文學湘軍”的創作,卻出現了令人尷尬的“湖南長篇現象”。由此可見,即使在同樣的時代語境中,湖南文學界的現狀也有值得自我反省之處。那么,湖南文壇形成這種現象的自身根源又在何處呢?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復雜、而且許多方面難以盡言的問題。筆者只擬從湖南文學界主導性的思想觀念、文學創作者和評論者的思想意識等方面,對其中所存在的偏差與薄弱之處略作剖析和探討。
首先,在主導性的思想觀念方面,湖南文學界傳統社會的體制正統意識、政治中心意識頗為強烈,商品經濟時代的市場意識、公共空間意識則相對地較為淡薄。
在湖南的文學組織工作中,對體制內的、特別是政府行為的評獎,大都是思想重視而措施有力的,但針對其它類獎項而進行的鼓動、宣傳和努力,則顯得相形遜色。對于作品本身在全國范圍內的宣傳與評介工作,世紀之交的湖南文學界更是處于空呼口號而實質上放任自流的狀態。從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體制內獎項方面的努力與運作其實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當今中國公共話語空間漸成強勢、多元文化皆具影響的時代環境中,不應時順變,缺乏“全面出擊”式的多方面努力,缺乏全方位的自我“包裝”與“推銷”,作品質量的“實至”而整個社會影響“名不歸”,就只能是一種必然的命運。
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撇開種種現實的具體人事因素,從較為開闊的歷史文化時空來看,筆者認為,體制正統心態和政治中心意識實為根本原因。湖南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政治意識強烈的省份,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原則,實質上是以政治性人生和體制內功業作為努力的根本目標。按照這種思路進行行為抉擇,必然會首先致力于謀求體制內的褒貶,然后再決定自我的動與靜、言說與沉默,至于公共話語空間的反應與態度,則往往只能“無暇”和“無力”顧及了。
其實,在20世紀末期,以“電視湘軍”為龍頭,湖南文化界已經開始出現淡化政治意識、走向世俗和市場社會的趨勢,呈現出體制內外齊頭并進的狀態,而且總體看來獲得了“雙贏”的效果。然而,文化底蘊更為深厚的湖南文學界,卻因傳統文化心理的束縛,反而未能及時、有效地適應迅速變革著的時代。雖然“電視湘軍”在注重公共話語空間的同時,表現出某種市俗化、市場化的傾向和對時代文化主流趨勢缺乏穩健把握的弊端,其內在的長短得失尚需進行深入、細致的區別和討論,但世紀之交的湖南文學界缺乏這種意識和觀念的轉變,已經使湖南長篇小說的應有影響受到了本可避兔的巨大損傷,卻也是難以諱言的事實。
其次,從文學創作者的角度來看,世紀之交的湖南作家仍然普遍存在“小生產者”式獨自耕耘的作品傳播意識,對于現代社會中文化商品“品牌打造”的手段和方式則表現得矜持而笨拙。
湖南作家在文本審美境界中精于揣摩和揭示的,往往只是政治性權位世界的機心與品性,在對公共社會空間生存智慧的研探方面,他們就顯得甚為隔膜,即使有所描述,也是基于享受和消遣人生而非認同性創建人生的態度。如果我們對湖南的長篇小說佳作細加品味,從“主旋律文學”《蒼山如海》《遍地黃金》,到官場文化考察性的《曾國藩》《楊度》,官場生態仿擬型的《國畫》,直到慨嘆商品經濟時代優雅人生方式扭曲和失落的《玩古》,皆可明顯地感受到這一特點。
延伸到文本之外,湖南作家就以一種經典不靠外在策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清高”姿態,放逐了對作品影響的運作。我們不妨再以《國畫》和曾經與之齊名的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羊的門》為例,來對這個問題略加分析。可以肯定地說,《國畫》的發行量遠遠超過了《羊的門》,但是,只從兩部小說初版時的封面設計來看,《羊的門》大排名家贊語的宣傳攻勢就遠遠超過了《國畫》;事實上,《羊的門》剛一出來,各種極具影響的報紙和文學評論刊物就迅速進行了相當充分的評介與研討,而有關《國畫》的學術性評論,則可說是寥寥無幾。出現這種令人惋惜的狀況,除了作品思想、藝術內蘊本身的原因,與作者和有關部門對于即時性影響的重視與“運作”“經營”不夠,顯然也大有關系。其實,商業炒作和學術研探是既相互矛盾、又相輔相成的,一概排斥完全沒有必要。是好作品當然可能傳之久遠,但是,無現在又何以圖將來呢?
并且,長期以來的觀念局限還導致了一個帶根本性的現實問題,即許多湖南作家對“影響運作”的心理準備、經驗和資源積累都相當欠缺。應當說,這實際上是與湖南文學組織機構的行為特征互為依存的一種歷史慣性。
再次,“湖南長篇現象”的形成,也和湖南文學評論與研究方面的局限密切相關。
在世紀之交的那個歷史階段,湖南的社會性文學評論力量較為薄弱,但“經院式”中國新文學研究的隊伍其實是頗有份量的。不過,這支隊伍多半只注重對某一特定學術領域的研究,對文學創作的現實狀況則缺乏充沛的熱情。湖南文學創作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相對沉寂,也使他們形成了與之保持疏離狀態的慣性。而且,湖南的文學評論界很少作為學術實力集團“集體發言”。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在作為學者面對業已定型的、經典性的文化史實進行研究,和作為文化工作者進行現實文化創造之間的價值定位問題方面,湖南的文學研究者有著自己不無偏執的考慮。筆者認為,雖然從學科細化的歷史發展趨勢來看,二者越來越涇渭分明而且均需全力以赴方可克奏大功,但是,如果真正達到了卓有成效的程度,二者之間其實是很難說存在高下之分的;而且,“經院式”的文學研究者保持對當代現實的適度敏感與關注,反可從思想文化史的高度拓展視野,吸納當代思想的精華與靈性,從而增添思維的活力,也就是說,“治學”與“批評”二者實可相得益彰,進而融會貫通、升華超越,最終釀成大器;更何況當代文學本身,就是不斷發展中的中國新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保持“學術領地”的一定程度的“彈性”,而不“劃地為牢”,也許恰是一種更具學術前景的研究道路。
從湖南文學的現實發展來看,學院派研究力量的深入參與,對評論力量較弱的湖南文學創作在全國影響的形成和增強,其作用應當是不可低估的。但由于這方面的力量未曾真正用心地參與到對湖南當下文學的評論中來,結果,湖南省的評論刊物《創作與評論》所發表的熱情推介湖南作家、作品的評論,既未全面顯示湖南學術界的思想眼光和學理深度,也未對湖南文學力作的思想藝術意蘊,充分展現本地學術實力地給予深入的開掘。同湖南省思想文化地位相似的其它省份,像湖北、山東、河南等等,就都有相對較強的“學院派”當代文學評論隊伍,并對推出和研究本省作家的優秀作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能不說,湖南評論界在這一方面的忽略和欠缺,也是“湖南長篇現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總之,湖南文學界的內在缺失與時代文化語境的不健全狀況相結合,導致了“文學湘軍”優秀作品的影響力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也導致了“文學湘軍”的整體影響力難以與整個社會文化層全面接軌,這樣一來,“文學湘軍”作為一個創作整體應有的文學和文化聲譽,自然也就難以獲得有效的承認與有力的提高。“湖南長篇現象”正是這種耐人尋味的尷尬局面的具體表征。
但不管怎么說,“湖南長篇現象”畢竟是“文學湘軍”在跨世紀時期的20余年時間里未能獲得文壇主流位置的客觀事實。由此看來,“文學湘軍”存在著審美的欠缺與局限也是毋庸諱言的,而超越獲獎目標的境界開拓和審美卓越之路,也許就在對這些局限與欠缺的克服之中,所以有必要對其略加審視。
綜觀“文學湘軍”在跨世紀時期的文學創作,其中程度、側面各不相同的審美欠缺與創作局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文學湘軍”的熱點題材創作中,往往對題材獨特內涵的展現相當豐富,發掘其人文和審美普遍意義卻有欠充分。湘西等地域生態類題材的作品,往往局促于對地域生態景觀的搜羅與鋪陳,跨地域的精神感覺涵蓋力和文化意味參悟力則有所欠缺,難以“跳出湘西看湘西”,文本審美境界中具象描寫沉實而繁復、詩性氣息卻不夠豐腴和充盈。都市、官場等題材的作品中,作者往往滿足甚至自得于生活表象的鮮活和世相體察的潑辣,對內蘊豐厚和藝術余味的追求卻普遍忽略。鄉土題材小說的創作大多藝術技法純熟自如,文本題旨和審美興奮點卻讓人似曾相識,缺乏時代氣息充沛的精神新鮮感。
其次,在“文學湘軍”的審美境界建構中,存在著生活實感和藝術情味、問題意識和文化容量之間不平衡的傾向。眾多“經驗型寫作”的作家,審美建構以社會問題意識和人生現實感觸取勝,卻往往缺乏精神意趣的滲透與文化詩意的氤氳。某些注重審美玄奧性和意象神秘感的作家,創作中則或者生活內涵不夠充實,或者文化趣味流于偏狹,或者審美精神有欠正大。少數難能可貴地追求意義深度的作家,又沉湎于堆砌種種人生細節的微言大義,以致個體生命意義的思辨不免流于繁瑣;或者對價值參照系闡釋和描述淺嘗輒止、單薄蒼白,反而抑制了審美境界的歷史厚實感。
再次,在“文學湘軍”的創作演變歷程中,常常會表現出“下一個題材在哪里”的焦慮。實際上,這是因為作家缺乏一個既題材爛熟而能靈感源源不絕、又精神融通而能思緒自由馳騁的“文學領地”,同時也缺乏“打一口深井”的藝術自信與審美激情。“文學湘軍”的許多創作正是這樣。他們對題材的選擇都是從社會文化熱點出發的一種追逐和揣摩,帶有鮮明的功利追求和“命題作文”性質,既不是自我人生體察和生命感悟的透徹呈現,也未能具備對相應歷史與文化時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深刻領會。這樣一來,相關創作就只能寫一部作品算一部作品,創作演變過程也就會不斷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對每一題材和精神領域進行獨步文壇的成功開掘,都需要艱難的積累和獨到的功力,因此,能夠成功創作的“下一個題材在哪里”,就成為了作家勢所必然的精神焦慮。最為關鍵的問題則在于,如果在題材和精神領域相當程度的變動和拓展之后,最終真能將其融會貫通起來,那么,這些創作就匯成了一個浩瀚汪洋般的藝術大世界,作家所呈現的也就是一種文學乃至文化大家的氣象與境界;如果不同題材的作品不過是一個個藝術的“孤島”,那么,題材變更的意義也就頗為有限了。
在筆者看來,這種種欠缺與局限的彌補和克服,既需要作家透過時尚生活的表象、超越地域歷史的拘囿,在審美境界的建構中形成一種寬廣深遠的思想空間和視界融合的思維方向;也需要作家從歷史、文化和人類精神的深處出發,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確立一種正大的精神氣象和獨立的思想品格;還需要作家超越謀獎策略,將文學創作由經世之“術”升華為審世之“道”,在創作的道路上形成一種文學大手筆的遼闊胸襟和雄偉氣魄。也許,這才是“文學湘軍”雄健發展的正道和大道,也是“文學湘軍”提升創作水平和文壇地位更重要、更根本的途徑。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