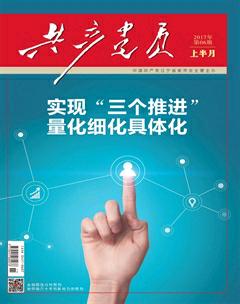趙忠賢:五十年做精一件事
冀魯
“忠誠超導數十載,后學盡忙撓耳腮。哲賢升溫銅雀臺,人皆仰止齊喝彩。前征途中覓鐵開,楷法自然非意外。輩輩概從磁中猜,模模均朝機理開。”
這是中科院物理所超導八組全體成員恭賀趙忠賢七十壽辰時的祝辭。短短八行詩,道出了同仁后輩受其潛移默化并仰佩崇敬的心聲,也濃縮了趙忠賢一生的奮斗歷程。
少年播下強國夢
趙忠賢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超導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擔任超導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專門從事低溫與超導研究,探索高溫超導電性研究。曾榮獲2015年馬蒂亞斯獎,這是中國大陸科學家首次獲得該獎項。
1941年1月30日,北方極寒之時,趙忠賢出生于遼寧省新民縣。那是個艱苦的年代,教育資源十分匱乏,幾個縣只有一所中學。趙忠賢酷愛讀書,一直堅持讀到高中。他所在的學校有個傳統——特別重視體育,每天必須跑步,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學生們對體育老師“恨”得不得了,可老師壓根不理。趙忠賢后來回憶說,就這樣堅持下來,不僅培養了吃苦的精神,也強健了筋骨,給身體打下了好底子,不然,后來哪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好的體力搞科研。
少年時代的趙忠賢被國家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深深影響著。他偶然得到一本蘇聯雜志,上面介紹的衛星、火箭、半導體等科技方面的新進展深深吸引著他,讓他不僅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心中也有了讓中國成為科技強國的渴望。1959年,趙忠賢如愿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技術物理系錄取。幾載春秋苦讀,1964年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在洪朝生任組長的研究組從事超導研究。酷愛鉆研的趙忠賢很快在物理所嶄露頭角,成為所里重點培養的青年才俊。
這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并最終結出了碩果——2017年1月9日,201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趙忠賢榮獲201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習近平主席親自為他頒了獎。
“我覺得,我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但是并不枯燥,因為超導研究充滿挑戰與發現。能將個人的興趣與生計結合起來,是最理想的選擇,這有多快樂!”
“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我每研究一段時間后就能看到新的東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每個人對幸福的感覺不一樣。能夠看到嶄新的世界,我就感到很幸福,很高興。雖然有時生活苦一些,干活累一些,但我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就感到很快樂。”
談起超導研究為他帶來的快樂,趙忠賢的眼中閃爍著光芒,臉上露出孩子般真誠的笑容。
挑戰權威贏得認同
“文革”期間,超導研究受到很大影響,大部分基礎研究被迫停止。1973年,經周恩來總理批示,一批年輕學生和學者被派往國外學習。趙忠賢被從干校召回,于第二年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接觸到了世界超導研究最前沿的知識。1975年回國后,趙忠賢就提出要“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簡稱“高溫超導體”)。
所謂“高溫超導體”,是指臨界溫度在40K(約零下233攝氏度)以上的超導體。麥克米蘭根據獲1972年諾貝爾獎的BCS理論計算,認為超導臨界溫度最高不大可能超過40K,他的計算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普遍認同,40K也因此被稱作“麥克米蘭極限”。
經過調研和縝密思考,趙忠賢支持少數理論家對國際廣泛認同的麥克米蘭極限提出挑戰。1977年,他在《物理》上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指出結構不穩定性又不產生結構相變可以使臨界溫度達到40-55K,進而提出復雜結構和新機制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達到80K。
趙忠賢作為當時極少數的“歸國人才”得到了支持,開始在全國組織和推廣“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研究,在科研條件相對簡陋的情況下開始研究銅氧化合物超導體。
1986年底,趙忠賢的團隊和國際上少數幾個小組幾乎同時在鑭-鋇-銅-氧體系中突破了麥克米蘭極限,獲得了40K以上的高溫超導體。一時間,世界物理學界地動山搖,傳統理論的崩塌讓“北京的趙”多次出現在國際著名的科學刊物上。
就在這次突破中,趙忠賢團隊還發現了70K的超導跡象,但當時國外的研究組沒人能夠重復70K跡象,海外有學者質疑中國的結果。趙忠賢他們卻意識到:名義上“同樣的體系”只是基本化學配比相同,但實際成分是不同的——他們的實驗樣品用的原料是1956年公私合營的工廠生產的,含有很多雜質。這啟發他們注意到,可能是雜質發揮了某種作用,從而導致70K跡象的出現。于是,他們開始主動“引入雜質”。1987年2月19日深夜,終于在鋇-釔-銅-氧中發現了臨界溫度93K的液氮溫區超導體,24日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了這一發現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元素組成。2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報道了這一消息,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轉載,在世界上刮起了一陣液氮溫區超導體的旋風。趙忠賢作為五位特邀報告人之一參加了美國物理學會三月會議,這標志著中國物理學家走上了世界高溫超導研究的舞臺。趙忠賢變成了在國際物理學界代表中國的符號。
趙忠賢所在集體因此榮獲1989年度國家自然科學集體一等獎,他也作為團隊代表獲得了第三世界科學院物理獎,這大大提升了中國物理學界的國際地位。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如果說艱苦奮斗不易,那輝煌中的冷靜和輝煌后的踏實則更為難得。獲得許多獎勵和榮譽的趙忠賢沒有被巨大的成功沖昏頭腦。他繼續潛心研究20年,終于帶領中國團隊再次引領世界熱潮。
2008年,日本科學家Hosono報道在鑭-氧-鐵-砷體系中存在26K的超導,與趙忠賢的新思路是一致的。他立刻意識到這一類鐵砷化合物很可能是新的高溫超導體,于是提出了高溫高壓合成結合輕稀土元素替代的方案,并帶領團隊很快將鐵基超導體的臨界溫度提高到50K以上,創造了55K的紀錄并保持至今,為確認鐵基超導體為第二個高溫超導家族提供了重要依據,實現了高溫超導研究領域的第二次突破。在這期間,他以67歲的高齡三次帶領年輕人幾乎通宵工作,完成了初期最關鍵的三篇論文。
美國《科學》雜志三次報道趙忠賢研究小組的工作,而小組的成果作為“40K以上鐵基高溫超導體的發現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質研究”的重要部分,獲榮201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五十多年前,當那個年輕的趙忠賢孤身一人背起行囊來到北京的時候,中國的超導研究才剛剛起步,高溫超導更是天方夜譚。如今,古稀之年的趙忠賢身邊已經凝聚起一支世界領先的中國高溫超導研究隊伍,中國的高溫超導研究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今天,象征著中國科技領域最高榮譽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趙忠賢,不僅僅是表彰他本人的杰出貢獻,更是期待著受他影響的幾代青年科學家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在未來第三次高溫超導突破中取得新的成就,為祖國科技事業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