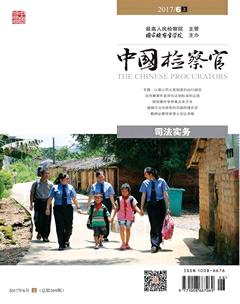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能動作用
閆偉
編者按:事之當革,不為則害。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適應新形勢、準確及時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是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升訴訟效率的重要探索,有利于推進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關于在部分地區展開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各試點院開展了大量積極有益探索,澡熨故俗,總結了諸多經驗,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本期專題特選取5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摒棄該制度研究前期的純理論,側重實務,緊緊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方面挖掘問題,翔實論證后提出對策,對檢察實務工作獨有裨益。
摘 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是我國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提高司法公信力、節約司法成本方面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國外的辯訴交易較為類似,但又是針對我國特有的國情所提出的一項司法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中,大部分工作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完成的,檢察機關職能的行使對該制度具體實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認罪認罰 檢察職能 律師參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在司法改革中新探索的一項刑事訴訟制度,要旨在于通過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坦白從而使其獲得從寬處理結果,實際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坦白從寬的具體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維持證據裁判規則下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變,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達到控辯雙方追求效率和輕判的雙贏結果。從該制度設計上看,檢察機關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要履行原有的職責,繼續行使公訴權,另一方面又要在辯護律師提出認罪認罰從寬申請的基礎之上,堅守證明標準,提出合法合理的量刑建議,具有能動的推進作用。
一、保障辯護律師權益,實現認罪認罰從寬過程的相對平衡
認罪認罰制度是控辯雙方就認罪與否、從寬與否進行協商的過程,既然是協商,協商主體就應當具有一個相對平衡的地位。控方以檢察機關為主,辨方如果僅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很難公平實現這一過程。認罪認罰不僅是程序問題,也是實體問題。如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應當適用何種程序、可能會判處何種刑罰等。沒有專業法律人員作為輔助,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無法進行的,其權益也無法保障。“兩高三部”《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5條規定了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即凡是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進入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都應當獲得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該條第2款還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根據人民法院、看守所實際工作需要,通過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駐值班律師及時安排值班律師等形式提供法律幫助。這樣不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也能夠大大提高刑事辯護率。但是,法律援助機構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值班律師是根據工作需要,并非強制要求,當沒有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師時,該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法律幫助權,《辦法》并未做明確規定,也沒有對如何保障辯護律師參與以及辯護權利受損后的救濟途徑做具體規定。
檢察機關作為監督機關,在認罪認罰過程中不僅是與辯護律師進行對弈的一方主體,也扮演著法律監督的角色,具有維護辯護律師辯護權、案件參與權的職責。譬如看守所、偵查機關、法院沒有通知辯護律師或者侵犯了辯護律師的其他權益,檢察機關就有權對該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和糾正,辯護律師也有權向檢察機關申訴控告。只有辯護律師的辯護權行使得到保障、辯護環境得以改善,才能真正的保障認罪認罰過程的真實性,從而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后,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獲得對應的訴訟利益。
二、推動刑事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適用,提高辦案效率
《辦法》中對該制度的適用范圍做了規定: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為不構成犯罪的三種情形外均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包括無期徒刑、死刑案件甚至是自訴案件。可以看出我國當前刑事政策的謙抑性,無論重罪輕罪、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都可以適用該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辦法》還規定了不同案件在認罪認罰從寬過程中又可以適用不同的刑事訴訟程序,譬如該制度中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應用。但簡易程序、速裁程序能否大量適用還有待證實。有統計顯示,我國的刑事一審案件數量有增加的趨勢,輕罪逐年遞增,重罪明顯減少。[1]輕罪案件刑罰較輕,針對逐年增多的案件數量提高辦案效率顯得尤為重要。《辦法》第16條擴大了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適用速裁程序的范圍,規定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當事人對適用法律無異議且被告人認罪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或者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最大的程序效益無非是提高司法效率減輕當事人訟累。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對辦案時間有硬性要求。但是在基層法院、檢察院,往往會出現案多人少的情形,《規定》中要求檢察機關在辦理刑事速裁程序時,可能判處1年以下的10日內決定是否起訴,可能超過1年的可以延長至15日,法院的審結期限也是10日和15日。很多基層院由于辦案效率低、案多人少等問題,為了增加辦案期限,適用簡易程序都較為慎重,認罪認罰制度下的速裁程序能否達到設計之初預想的效果還有待考驗。雖然員額制、司法責任制改革已經初見成效,但是凸顯的一些問題也是不能否認的,如有資格辦案的法官檢察官中有很多都是沒辦過刑事案件的,能辦理案件的又沒有辦案資格等。法院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檢察院不提出適用何種程序,一般都會適用普通程序。所以在適用該制度過程中,檢察機關應當身先士卒,率先提高辦案人員的辦案能力和職業素質,加大人才引進,尤其應當加強基層院的人才配備,對于能夠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積極適用,同時多向法院提出適用申請,以便提高司法效率。
三、明確法律監督職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合法權益
檢察機關的定位從其產生到現在,一直是大家爭論的問題,尤其對檢察官而言,既不愿意淪為“次等法官”,也不愿意成為“高級的司法警察”。大陸法系國家包括創制檢察官的法國更多的是將檢察官定位為“政府代理人”或者“法治國的代言人”,[2]不僅代表國家公訴,還享有指揮偵查、裁量起訴、刑罰執行等廣泛權力。美國的檢察官定位更為簡單一些,主要負責起訴等。我國的檢察官制度借鑒了部分前蘇聯的法律監督模式,但沒有前蘇聯檢察機關作為最高法律監督機關的龐大職權,我國憲法中檢察機關被定義為法律監督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雖然訴訟程序可能會簡化,但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責不能簡化。
(一)嚴格監督偵查行為,保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
認罪認罰首先要保證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防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的使用。檢察機關偵查監督權的行使一直因為沒有太多的后果性、懲罰性規定而飽受爭議,對于偵查機關的違法偵查行為只能提出檢察建議、糾正違法通知書等毫無制裁力的書面措施。因此,檢察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在強化偵查監督、規定相關對違法偵查行為的制裁措施的同時,還要加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和認罪認罰自愿性的保障力度。檢察機關應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甚至要探索更為嚴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制約偵查機關,才能保證認罪認罰過程的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統一。認罪認罰制度對案件的階段沒有做規定,即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階段也能夠適用該程序。對于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行為的監督能否納入到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范疇還需要進一步明確。
(二)履行檢察官客觀義務,彌補法律援助制度不足
司法實踐中,法律援助律師尤其是基層法律援助律師的法律援助效果不盡如人意。筆者曾經接觸過一些法律援助類型的刑事案件,發現無論在審前的閱卷還是開庭過程中的辯護,法律援助律師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一個維護當事人權益的辯護人,而是一個形同虛設、走走過場的客串角色,辯護律師的辯護積極性不是很高。雖然在法律援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支付代理費用,但法律援助律師一般都是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領取正常工資的同時還可以獲得政府因提供法律援助而給予的補助。“免費的午餐”不一定就要簡單做。吃這個“免費午餐”的往往是最需要幫助的人,要么是未成年人要么是無期徒刑、死刑的人。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辯護律師被賦予了更重要職責,不僅要提供原來應當提供的法律服務,而且還需要站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立場向檢察機關提出適當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為有利的從寬建議。當法律援助律師怠于行使援助義務或者提出的建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對應的利益明顯不成正比的時候,檢察官還應當嚴格履行客觀義務,結合案件事實公正地提出意見,包括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意見。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同時,檢察機關的客觀義務之履行也能彌補這一不足。
綜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主要實現階段在審查起訴環節,檢察機關作為連接偵查、審判的中心機關,其權力行使以及義務履行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只有檢察機關充分發揮自身的能動作用,才能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現創造一個良好的司法環境,實現司法公正的同時提高司法效率。
注釋:
[1]參見魏曉娜:《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國語境下的關鍵詞展開》,載《法學研究》2016年第4期。
[2]參見林鈺雄:《檢察官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