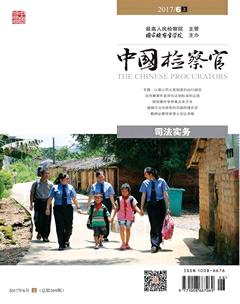逮捕司法化轉(zhuǎn)型的實踐困境反思
邢小兵 張仁杰 李德勝
摘 要:審查逮捕的司法化轉(zhuǎn)型是破除審查逮捕形式化和行政化的有力革新,特別是對基層檢察機關(guān)而言,審查逮捕的司法化更是化解“捕后緩刑”和“捕后輕刑化”問題的利器,但基層檢察機關(guān)推進審查逮捕的司法化卻面臨證據(jù)標準的應(yīng)用紛爭、刑事辯護律師的角色性缺位、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的執(zhí)行異化、逮捕公開化的建構(gòu)含混四大實踐問題有待化解。
關(guān)鍵詞:審查逮捕 司法化 實踐困境 證據(jù)標準 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
長期以來,理論界和實務(wù)界對逮捕制度的實踐異化問題爭議頗多,論者們開出了“推倒重構(gòu)”和“改良適應(yīng)”兩副藥方。推倒重構(gòu)論者認為,逮捕制度的異化癥結(jié)在于享有批準和決定逮捕權(quán)的檢察機關(guān)實為追訴機關(guān),改革的路徑在于確立法院審查模式,將逮捕決定權(quán)統(tǒng)一交由人民法院行使。[1]改良論者則主張,在尊重既有的逮捕權(quán)配置模式的基礎(chǔ)上,推進逮捕制度的訴訟化改造以實現(xiàn)逮捕制度的技術(shù)性改良。[2]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對逮捕制度進行了調(diào)整,強化了犯罪嫌疑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弱化了逮捕對犯罪嫌疑人自由的剝奪和限制功能,初步建構(gòu)起了訴訟化構(gòu)造的審查逮捕模式。[3]筆者認為,審查逮捕的司法化是以監(jiān)督和限制偵查權(quán)為核心,是以訴訟化模式為基礎(chǔ)的審查逮捕實質(zhì)化。基層檢察機關(guān)長期受“捕后緩刑”和“捕后輕刑化”問題的困擾,推進審查逮捕向司法化轉(zhuǎn)型的問題眾多,尤其是證明標準把握的差異、刑辯律師的角色缺位、受制于辦案需要的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異化、司法化審查的實踐模式建構(gòu)不足等四大問題已成為阻礙審查逮捕司法化轉(zhuǎn)型的四只攔路虎,有必要立足于基層檢察機關(guān)審查逮捕的實踐現(xiàn)狀,對以上四大困境予以檢討。
一、司法化的前置性障礙——證明標準的實踐應(yīng)用紛爭
無論審查逮捕司法化的實踐模式如何創(chuàng)新,審查分析的基礎(chǔ)還是在案證據(jù)。但當(dāng)前的司法實踐中,司法實務(wù)人員對證明標準和證據(jù)審查模式的實踐應(yīng)用分歧較大,這種理念層面的認知差異根源性地制約著審查逮捕的司法化轉(zhuǎn)型。司法化轉(zhuǎn)型語境下,審查逮捕階段證明標準問題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刑事偵查取證的階段性和各階段訴訟任務(wù)的差異性決定了訴訟進程中證明標準把握的差異性,審查逮捕階段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有違刑事訴訟的基本認知和程序設(shè)計初衷,因而不宜適用“兩個基本標準”。第二種觀點認為,審查逮捕階段對證明標準的把握應(yīng)區(qū)分案件類型,不能一概按照法庭裁判標準處理。對罪行輕微、案情簡單的應(yīng)以起訴、判決的標準作為逮捕標準;對罪行較重,可能判處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案件要把握兩個基本標準。第三種觀點則主張,以審判為中心情境下,審查逮捕案件辦理應(yīng)堅持法庭裁判的排除合理懷疑標準。
證明標準的實踐把握分歧根源于實務(wù)人員對證明標準的功能定位認知含混,因而對證明標準的理解和應(yīng)用應(yīng)回歸這一概念本身的制度性功能。證明標準是一個關(guān)涉主客觀因素的實踐理念,是為確保裁判結(jié)論的正當(dāng)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而建構(gòu),是裁判者事實認定活動的最低終點線。[4]實踐化的證明標準深受證明對象和司法證明機理的影響,同時人類認識能力的相對性決定了證明標準的實踐認知必然深陷客觀化與主觀化的內(nèi)生性博弈之中,人們對證據(jù)和事實的認定都不是絕對真理,而只能是相對真理。[5]無論證明標準如何客觀化和具體化,其本身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為沒有證明標準能夠完全消除不確定性,或使法律推論活動的溯因推理永遠保持正確性。[6]這就注定證明標準存在應(yīng)然性與實然性的差異,證明標準的實踐異化也就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合理性。
一旦證據(jù)標準的適用爭議延及到實際辦案,必然引發(fā)證據(jù)審查分析的主觀化和個體化,嚴重制約證明標準應(yīng)用的規(guī)范化和統(tǒng)一化,進而形成不同的證據(jù)審查分析模式。在案證據(jù)對證明對象印證的充實性程度是證明標準的實踐化衡量,在案證據(jù)的充實性實際上是證明標準的證實程度問題,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chǔ)在于對每一在案證據(jù)的證據(jù)能力和證明力的審查研判。一切的證據(jù)審查分析都是經(jīng)驗性的思考和把握,對證明程度的把握一直處于一定程度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之中,[7]逮捕司法化情境下,證據(jù)審查將呈現(xiàn)親歷化與實質(zhì)化趨勢,以訊問嫌疑人為基礎(chǔ)的證據(jù)核實模式需要統(tǒng)一的證據(jù)標準做支撐,無論是非法證據(jù)的排除,還是證據(jù)充實性的評判,均需明確評價標準和具有充實感性的實踐證據(jù)接觸,而司法實踐對證明標準的把握卻相對主觀化和具體化,實務(wù)人員對證據(jù)本身的經(jīng)驗認知也存在諸多欠缺,司法的親歷性欠缺和證據(jù)審查的形式化依然普遍存在。
二、司法化的實踐主體缺失——刑事辯護律師的角色性失靈
刑事辯護律師在審查逮捕階段的角色性失靈導(dǎo)致審查逮捕司法化面臨主要參與主體嚴重缺位的困境。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賦權(quán)刑事辯護律師介入審查逮捕,擴大了刑事辯護律師的介入范圍,但從實證調(diào)研統(tǒng)計的數(shù)據(jù)看,刑事辯護的律師介入率較低問題依然明顯。有的實證調(diào)研反映:涵括法律援助在內(nèi),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律師的介入率只有30%左右。[8]而逮捕階段則更低,有學(xué)者的實證調(diào)研反映: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審查逮捕階段律師參與的比例在5%至10%之間,且只有一半左右的律師提交書面辯護意見。[9]以北京市某基層檢察院近三年辦理的審查逮捕案件中辯護律師介入情況來看,也存在類似問題。近三年審查逮捕階段律師的年均介入率為5.36%;從介入形式看,50%左右的辯護律師提交了書面辯護意見;從律師介入的訴求看,主要為提交證據(jù)材料證明嫌疑人無罪和申請取保候?qū)彛灿新蓭熖岢鲩喚淼囊螅粡慕槿胍庖姷膶嵸|(zhì)性作用看,多數(shù)律師的介入意見缺乏針對性和有效辯護性;從辯護意見的最終采納情況看,只有約有20%左右的辯護意見被采納,且主要集中于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問題上。
以上的調(diào)研統(tǒng)計凸顯了基層檢察機關(guān)辦理的審查逮捕案件中辯護律師介入不足和介入成效不佳的問題,這種參與力量的不足對司法化審查轉(zhuǎn)型的實踐拓展形成了潛在的制約。在缺乏律師參與的情況下,司法化審查極可能淪為檢察機關(guān)的獨家戲,最終只能停于表面,流于形式。因為導(dǎo)致律師介入不足問題的成因相對復(fù)雜,既有立法規(guī)制的細化性配套規(guī)范不足導(dǎo)致的律師介入方式和介入之后的檢律互動缺乏,也有現(xiàn)實辦案需要主導(dǎo)下的嫌疑人權(quán)利保障不力或嫌疑人權(quán)利意識不足。[10]因而審查逮捕階段刑事辯護律師的角色失靈將難以在短期內(nèi)得以改進。要破解審查逮捕階段律師介入比例偏低問題,治本之策不在于完善律師介入權(quán)限設(shè)計和介入權(quán)利保障,而在于涉案嫌疑人的辯護權(quán)利保障,能否建構(gòu)起針對大部分在押人員的免費或相對低廉的法律服務(wù)機制是關(guān)鍵。
三、司法化的實踐軟肋——檢察機關(guān)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執(zhí)行異化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賦權(quán)檢察機關(guān)在審查逮捕階段調(diào)查核實證據(jù)的權(quán)力,為審查逮捕從形式化的書面審查向?qū)嵸|(zhì)化的司法化審查轉(zhuǎn)型奠定了制度基礎(chǔ)。但從該制度的運行實踐看,法律規(guī)制的彈性化和辦案需要的差異化導(dǎo)致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深陷備而不用、備而少用、甚至備而濫用的異化困境。言詞證據(jù)的易變性和案件事實的復(fù)雜性決定了辦理案件時必須兼聽而明,然而調(diào)查核實作為兼聽和親歷的重要途徑卻在司法實踐中被折扣執(zhí)行,在小案不易生錯案的僥幸心理和現(xiàn)實辦案壓力雙重擠壓下的檢察人員并未認識到司法親歷的重要性。實際上“司法人員只有深入到具體案件中親歷親為,親自審查各種證據(jù),才能對事實作出正確的判斷”。[11]刑事訴訟法和相關(guān)司法解釋均明確了應(yīng)當(dāng)和可以訊問的情況,實踐中一些省市甚至要求辦理審查逮捕案件無論簡單與否每案必問,意圖通過審查逮捕的訊問實現(xiàn)對在案證據(jù)的全面調(diào)查核實。但檢力資源的有限性與案件繁雜程度的差異性決定了具體執(zhí)行時必須有所選擇和側(cè)重,即使是每案必提,大部分提訊也是形式化的走過場,實踐執(zhí)行中的逮捕提訊嚴重偏離了立法規(guī)制的預(yù)期軌道。
從司法實踐看,逮捕訊問的異化頑疾主要集中體現(xiàn)為以下幾種現(xiàn)象。一是,逮捕訊問異化為刑事訴訟權(quán)利義務(wù)的告知。因辦案期限短的問題,審查逮捕訊問集中化,訊問演變?yōu)楹唵蔚臋?quán)利義務(wù)告知,而對案件關(guān)涉的實質(zhì)性問題很少提及。二是,為了辦案需要,變通性地理解和執(zhí)行應(yīng)當(dāng)訊問的條件。從相關(guān)規(guī)定看,檢察機關(guān)對應(yīng)當(dāng)訊問執(zhí)行起來無異議的主要限于三類人員,而其他情形下是否有必要進行訊問完全取決于檢察人員的自由裁量。但對“案情重大疑難復(fù)雜”和“是否符合逮捕條件”的理解和執(zhí)行就相對主觀化,不同的辦案人員對案件的理解和訊問必要性的把握就不一樣。三是,對嫌疑人未被刑事拘留的提捕案件,逮捕訊問基本處于停止?fàn)顟B(tài),辦案風(fēng)險防范的需要成為了不予訊問的有力托詞,此類案件的提訊不僅要有事前的辦案風(fēng)險防范和傳喚聯(lián)系環(huán)節(jié),還要就嫌疑人可能翻供問題與偵查機關(guān)溝通協(xié)調(diào),最佳的辦案選擇就是不予傳喚,不予訊問。四是,受辦案風(fēng)險和辦案效率的雙重制約,對訴訟參與人的詢問基本流于形式。從司法實踐看,在辦案風(fēng)險和壓力的雙重擠壓下,檢察人員很少對訴訟參與人進行詢問,詢問訴訟參與人的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實際上也是備而不用,流于紙面。要化解以提訊為基礎(chǔ)的調(diào)查核實虛化,則需從加大審查逮捕業(yè)務(wù)辦理的信息化,著力推進遠程視頻提訊技術(shù)的實際應(yīng)用,以降低提訊對辦案時間的羈押。
四、重要執(zhí)行載體的缺陷——逮捕公開化的建構(gòu)含混
審查逮捕的公開聽證作為審查逮捕司法化的重要方式在全國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實踐探索,但從各地實踐的情況看,審查逮捕的公開聽證極其混亂。公開聽證的試驗?zāi)J讲灰弧⑿Ч鳟悾械牡胤介_展的審查逮捕聽證停于表面,流于形式,異化為司法作秀,實質(zhì)上是“為聽證而聽證”,這種異化的實踐嘗試消解了聽證制度的實際功效,亟需進一步規(guī)范和整合聽證設(shè)計。就聽證建構(gòu)問題,學(xué)者們立足于不同的立場對公開聽證制度的建構(gòu)提出了不同的設(shè)想。比如,有的論者認為:逮捕聽證程序可按檢察機關(guān)居中裁判,公安機關(guān)和嫌疑人兩方控辯對立的主體配置,公開對案件中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和公安機關(guān)的偵查取證合法性進行聽證審查,聽證結(jié)論作為逮捕與否的重要依據(jù)。[12]也有論者從逮捕聽證的參與主體、案件范圍、案件類型、聽證內(nèi)容、啟動方式,聽證形式等方面對逮捕聽證進行了建構(gòu)。[13]還有論者提出從平衡訴訟效率和保障人權(quán)的雙重目的出發(fā)建構(gòu)分流式審查逮捕聽證機制,但對具體如何建構(gòu)卻未能提出詳細的論證。[14]實際上論者們對逮捕聽證的建構(gòu)和運作依然認知不一,特別是在影響實踐操作的聽證案件范圍和具體聽證內(nèi)容的設(shè)計上認知差異頗大。
從各地的探索情況看,各地對審查逮捕的公開聽證探索相對混亂,在聽證主體、聽證案件范圍、聽證程序設(shè)計、聽證結(jié)論效力等方面規(guī)制和應(yīng)用不一。梳理既有的實務(wù)探索,審查逮捕公開聽證存在的爭議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聽證案件范圍。有的地方提出應(yīng)集中于案件社會危險性的聽證,也有地方認為應(yīng)以不構(gòu)成犯罪和無逮捕必要案件為限,更有主張對審查逮捕的所有事項均可考慮納入聽證范圍。二是,聽證參與主體。有的地方是檢察機關(guān)、偵查機關(guān)、嫌疑人所聘請的辯護律師三方參與,有的地方是在三方的基礎(chǔ)上邀請人大代表或政協(xié)委員觀摩,有的地方還邀請被害人參與表達訴求。三是,聽證程序設(shè)計。有的地方將聽證區(qū)分為簡易聽證和普通聽證,有的地方不做區(qū)分,單純就只有一種聽證模式。四是,聽證內(nèi)容的范圍,既有關(guān)涉基本犯罪事實的,也有關(guān)于社會危險性,更有關(guān)涉?zhèn)刹榛顒颖O(jiān)督事項的;五是,從聽證結(jié)果的實際效力也是差異較大,并未對檢察機關(guān)最終做出處理決定有實際的約束力,逮捕聽證已經(jīng)陷入聽而不用或聽而慎用的局面。
作為審查逮捕司法化轉(zhuǎn)型的重要程序設(shè)計,審查逮捕的公開聽證要避免陷入適用亂局就必須著力解決三個核心問題。一是公開審查的參與主體應(yīng)由誰參與,二是審查聽證的案件范圍和聽證內(nèi)容應(yīng)如何圈定,三是審查聽證結(jié)論的實踐效力應(yīng)如何定位。對第一問題的解決關(guān)涉逮捕聽證的司法化是否能夠真正建構(gòu),在審查逮捕日趨司法化和職業(yè)化的今天,若在聽證主體上引入人大代表或政協(xié)委員參與,既不利于司法經(jīng)濟,也不利于逮捕聽證的常態(tài)化開展,實有司法秀之嫌,因而逮捕聽證的主體建構(gòu)應(yīng)向法院刑事庭審靠齊;而聽證案件范圍和聽證內(nèi)容是公開聽證的核心所在,逮捕的訴訟階段定位決定了某些案件和某些案件內(nèi)容不能進行聽證,同時若在案件范圍和聽證內(nèi)容上過于放開,逮捕聽證將異化為庭審的預(yù)演,因而不能將所有案件和逮捕審查的所有內(nèi)容進行聽證,對不公開審判的案件類型和關(guān)涉案件基本事實認定的問題不納入公開聽證范圍;聽證結(jié)論的法律效力實質(zhì)上關(guān)涉聽證各方參與聽證的熱情和動力問題,因而應(yīng)將聽證結(jié)論作為逮捕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jù)。
注釋:
[1]參見劉計劃:《逮捕審查制度的中國模式及其改革》,載《法學(xué)研究》2012年第2期。
[2]參見郭晶:《逮捕制度改革的兩條道路及其反思—以逮捕功能異化現(xiàn)象為立論基點》,載《時代法學(xué)》2014年第4期。
[3]向澤選:《修改后刑訴法的實施與審查逮捕》,載《人民檢察》2012年第12期。
[4]楊波:《審判中心下統(tǒng)一證明標準之反思》,載《吉林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6年第4期。
[5]朱孝清:《刑事訴訟法實施過程中的若干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14年第3期。
[6][美]拉里.勞丹著,李昌盛譯,《錯案的哲學(xué):刑事訴訟認知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頁。
[7]栗崢:《司法證明模糊論》,載《法學(xué)研究》2007年第5期。
[8]顧永忠:《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16年第2期。
[9]馬靜華:《逮捕率變化的影響因素研究:——以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為背景》,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15年第3期。
[10]參見葉青:《審查逮捕程序中律師介入權(quán)的保障》,載《法學(xué)》2014年第2期。
[11]朱孝清:《司法的親歷性》,載《中外法學(xué)》2015年第4期。
[12]葉青:《審查逮捕程序中律師介入權(quán)的保障》,載《法學(xué)》2014年第2期。
[13]肖中華等:《審查逮捕聽證制度研究》,載《法學(xué)雜志》2013年第12期。
[14]參見彭志剛:《論審查逮捕制度的分流聽證式改造》,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