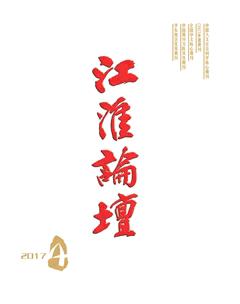論初唐四言詩唱和的成因及其文學史意義
嚴維哲+李定廣
摘要:魏晉時期大量創(chuàng)作四言詩的現(xiàn)象,在唐初貞觀年間的宮廷詩壇重新出現(xiàn),部分被收錄于《翰林學士集》中,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現(xiàn)象。許敬宗等一批深受南朝詩學熏陶的宮廷詩人,繼承了傳統(tǒng)四言詩的雅頌主題,仿效詩經(jīng)句式,重拾兩晉時期的四言詩風,在宮廷唱和活動中進行新的創(chuàng)作。其產(chǎn)生的原因既與當時流行的雅正中和文學觀密不可分,又受到統(tǒng)治者審美趣味的引導,同時也和郊廟音樂的創(chuàng)制之時代背景相關。它既是南北朝宮廷詩學觀念的延續(xù),也是唐代宮廷唱和活動中四言體式的“絕響”,對唐代的復古派詩人有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初唐四言詩;宮廷唱和;《翰林學士集》;成因;文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4-0147-006
先秦以來,四言詩作為中國最早的詩體,在經(jīng)歷了漢魏兩晉的發(fā)展之后,在南朝陷入低谷,在唐代更是不為重視。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唐時期的宮廷唱和詩集《翰林學士集》殘卷中,保存著部分四言詩作。初唐宮廷詩人何以對這種已經(jīng)幾乎被遺忘的詩體投入如此大的興趣,并在宮廷唱和活動中加以運用,其原因值得深究。在前人著述中,對初唐詩學與唱和活動的研究已經(jīng)有不少涉獵。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如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一書,通過唐人集會總集與相關詩人群體活動的關聯(lián),考察宮廷詩人群的作品風格;尚定的《走向盛唐》則對初唐詩風的淵源與演變進行了新的探索;岳娟娟的《唐代唱和詩研究》從唱和詩的角度探討初唐宮廷詩歌的得失與變遷;其他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還有李定廣、陳伯海合著的《唐詩總集纂要》,陳伯海的《<翰林學士集>考索》,呂玉華的《太宗朝詩風與<翰林學士集>》等。這些論著各有所長,但對于初唐宮廷詩人的四言詩創(chuàng)作部分均涉及不多。忽視初唐宮廷詩人的四言詩唱和活動的文學價值,會妨礙我們對南北朝初唐詩歌流變規(guī)律的認識理解,故本文擬從《翰林學士集》中四言唱和詩切入,探究傳統(tǒng)的四言體式在初唐宮廷唱和活動中復興的原因,結合漢魏以來的四言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予以分析解讀,探究初唐宮廷四言唱和詩的詩學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一、《翰林學士集》中四言唱和詩人群
對南朝詩學的接受
從四言詩發(fā)展的軌跡來看,在先秦的《詩經(jīng)》四言體大量產(chǎn)生之后,歷經(jīng)兩漢的發(fā)展,在魏晉時期文人四言詩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其語言結構也有了很大變化。曹操、阮籍、嵇康等人皆有較為成熟的四言詩作品。西晉太康時期,四言詩被視為雅音,摯虞《文章流別論》就說:“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1]陸機、束皙、傅咸是當時四言詩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家。永嘉南渡之后,玄言詩興起,四言詩更是被視為鋪敘玄理的合適體裁,王羲之所組織的蘭亭集會,四言詩的創(chuàng)作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陶淵明甚至被視為四言詩的“最后的作家”。南北朝時期,普遍被認為是四言詩的消歇期。但是在謝靈運、顏延之、沈約、蕭統(tǒng)等著名作家的詩集中,依然可以看到一定數(shù)量的四言詩作品。其主題內容大都是釋奠、應制、贈答之作。對于四言詩與五言詩在體裁上的區(qū)別,劉勰與鐘嶸都予以了關注。《文心雕龍·明詩》曰:“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2]鐘嶸《詩品序》評論四言詩:“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3]這些文學批評著作,均肯定了四言詩的文學地位,同時鐘嶸也指出四言詩在南朝“世罕習焉”的事實。在南北朝后期,集南北詩歌大成的庾信其詩歌雖以五言為主,但其創(chuàng)作的北周郊廟歌詞均為典型的四言體,對后世影響很大。入唐之后,唐詩中絕少四言,錢良擇《唐音審體》甚至說:“唐人四言詩甚少,錄之僅得三首。”[4]其實,在初唐詩歌選本《翰林學士集》中依然保存著十七首唐人的四言唱和之作,唐人如若菲薄四言,何以在宮廷詩歌創(chuàng)作中較多采用?唐人對于四言詩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學話題。
今存《翰林學士集》之殘卷中收錄唐人四言詩共計十七首,分別為鄭元璹、許敬宗、于志寧、沈叔安、張后胤、張文琮、陸搢等七人之唱和作品《四言曲池酺飲座銘并同作七首》,以及許敬宗之《四言奉陪皇太子釋奠詩一首應令》十章(此聯(lián)章體一首十章,實為十首)。許敬宗之詩雖是應制之作,實則亦屬于唱和范疇,當時必然有同題唱和作品,可惜亡佚殆盡,本文一并討論。
關于詩歌唱和活動的時間,學者存在不同見解:據(jù)傅璇琮、陶敏考證,《曲池酺飲座銘》唱和詩作于貞觀四年[5],彭慶生《初唐詩歌系年考》從其說[6],然賈晉華先生在《唐代集會總集詩人群研究》書中則認為當為貞觀八年。[7]許敬宗《四言奉陪皇太子釋奠詩一首應令》的詩歌本事,據(jù)《唐會要》卷三十五《釋奠》記載:“(貞觀)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圣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裔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yè)趙宏智為終獻。旣而就講宏智演孝經(jīng)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可見,太子釋奠許敬宗上四言詩事當在貞觀二十年二月。創(chuàng)作時間雖略有爭議,然大致是在唐太宗貞觀一朝。又因現(xiàn)在所見之《翰林學士集》僅是殘卷,其四言詩唱和,當遠不止現(xiàn)在所見的篇目。總體來說,四言詩在唐初的宮廷詩壇上的復現(xiàn)和流行,當無異議。
這些四言唱和詩的七位作者,大都是由隋入唐的文人,其文學淵源都和南朝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試辨析如下:
于志寧(588—665),是北周太師于謹之曾孫。隋末棄官,后為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其嗣父于宣敏有詩才,據(jù)《隋書·于宣敏傳》載:“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8]1147趙王宇文招博覽群書,“學庾信體”[9],于宣敏既受其賞識,其詩才當與南朝詩歌有共同之處。
許敬宗(592—672),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許善心之子,其宗族世仕南朝。唐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其父許善心是隋代雅樂歌辭的創(chuàng)制者之一。《隋書·樂志》記載:“仁壽元年,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征等創(chuàng)制雅樂歌辭。”[8]360
鄭元璹,滎陽開封人,乃隋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之子,其父精通禮樂。《隋書·鄭譯傳》載:“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8]1138鄭譯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8]1135可見鄭元璹的繼母為蘭陵蕭氏皇族,與南朝詩學淵源頗深。
沈叔安,吳興武康人。武德七年,出使高麗。后為潭州都督。《元和姓纂》卷七記載:“(沈)琛次子楚。五代孫君攸,陳衛(wèi)尉卿;生叔安,唐刑部尚書、吳興公。”[10]吳興沈氏是南朝大家族,沈約是永明體代表作家,也是梁代郊廟樂詞創(chuàng)作者。叔安之父沈君攸也是后梁著名文人,其文化淵源來自江南自不待言。
張文琮,貝州武城人。貞觀中為持書侍御史。從父弟張文收尤為精通禮樂,據(jù)《舊唐書·張文收傳》記載:“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更博采群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chuàng)制禮樂,召文收于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11]2817張文琮雖為北人,然其宗族張文收有覽蕭吉樂譜之事,按蕭吉亦出自南朝蕭梁宗室,《北史·蕭吉傳》記載:“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12]
張后胤,蘇州昆山人。《舊唐書·張后胤傳》載:“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后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zhèn)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11]4950
陸搢,字士紳,吳郡人。宋范成大《吳郡志》引《大業(yè)雜記》言其家世:“祖暎,梁侍中。父陟,咨議參軍。世有文集,搢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yè)中,為燕王記室。唐貞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13]
簡而言之,進行四言詩唱和的七位作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首先,這些作者深受南朝文學的熏陶,他們或是南朝舊臣之后,如許敬宗、沈叔安;或是江南土著,如張后胤、陸搢;即便是北方人,有的人直系親屬中精通南朝文學,如張文琮家族;有的甚至與南朝皇族有著姻戚關系,如鄭元璹。其次,這些作家的家族中有深厚的雅文學傳統(tǒng),宗族中不乏精通雅樂之人,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力,許敬宗、鄭元璹、張文琮的家族即是杰出代表。
二、《翰林學士集》四言唱和詩的內容句式特點
初唐宮廷詩人身處大一統(tǒng)王朝的核心,他們在南北朝詩人的藝術實踐基礎上,對傳統(tǒng)的詩歌創(chuàng)作方式予以新的審美觀照。通過詳細分析這十七首四言唱和詩,我們可以看出初唐詩人們在四言詩創(chuàng)作之內容體式上的一些特點。
(一)對傳統(tǒng)四言詩的“雅頌”主題的繼承。初唐詩人的四言宮廷唱和詩主要還是沿襲了兩晉時期四言詩歌功頌德的創(chuàng)作主旨,但也不乏一些自身的特點。許敬宗等人所撰的四言唱和詩其題為曲池酺飲座銘。按酺飲,即聚飲。這里似指君王賜宴,群臣會飲之意。酺,古指國有喜慶,特賜臣民聚會飲酒。《漢書·文帝紀》:“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14]108顏師古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14]110座銘,原指座右銘之意。這里似指席間所作以記其盛的文字。
這些唱和詩的內容基本如出一轍,交代飲宴之事,描繪周圍風景,歌詠太平盛世。雖不脫“頌圣”之意,但有些寫景狀物之處,依然新鮮活潑,情景交融,帶有鮮明初唐詩歌的特色。鄭元璹之詩云:“離酺將促,遠就池臺。酒隨歡至,花逐風來。鶴歸波動,魚躍萍開。人生所盛,何過樂哉。”歡宴隨著飲酒而氣氛愈加濃烈,隨風飄送陣陣花香,從側面渲染宴游之盛況,表達內心愉悅之情。這種對貴族生活的細膩描摹,顯然與南朝詩歌的影響有關。許敬宗的另一首詩歌主題為“皇太子釋奠”,更是典型頌圣之作。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令太子李治于國學釋奠于先圣先師,許敬宗獻詩以美其事。唐代統(tǒng)一之后,新王朝的典章制度需要重新確立。而以《詩經(jīng)》體為依歸的四言詩,格調古雅,符合統(tǒng)治者的要求,并在唱和活動中積極采納,這也充分展現(xiàn)了初唐詩人對四言詩的文體認識。
(二)對《詩經(jīng)》句式的效仿。在這十七首四言詩中,其詩歌體式有很明顯的向《詩經(jīng)》復歸的痕跡。許敬宗的《奉陪皇太子釋奠》詩十章,每章八句,前三章從天理說起,繼而說典章制度、倫理綱常,雅正之風因亂世而衰微。幸而得太宗父子英明神武,才使國泰民安。第四、五章之后轉入對太子的描寫,歌頌太子的聰明睿智,德行過人,修習課業(yè)之誠。第六章寫釋典的開始,第七章寫釋奠中設置酒食,講演忠孝的場景,第八章寫整個過程各方面都奉行職事,濟濟一堂。第九章寫典禮結束之景。最后一章表達寫詩頌圣之意。這種分章敘事的結構,正是典型的《詩經(jīng)》雅頌體的模擬。而《曲池酺飲座銘》之唱和,有些句式也帶有較為明顯的詩經(jīng)氣息,如“和風習習”、“勉矣君子,俱奉堯心”等句子是典型的詩經(jīng)體,“鶴歸波動,魚躍萍開”的景象也使人想起《詩經(jīng)》中的“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句子。當然,由于相距先秦時代已遠,這種效仿的痕跡遠較魏晉四言來得淺。
(三)對兩晉四言詩的借鑒。許敬宗編選的《文館詞林》,現(xiàn)存殘卷中,收入以釋奠為題的,有18首。收入兩晉詩人四言詩作品45首,從中不難看出唐初宮廷詩人對兩晉詩風的熱衷。無論許敬宗聯(lián)章體的釋奠之作,還是七人《曲池酺飲座銘》唱和詩,大多數(shù)的句子都是對偶句,且多用實字,類似以嵇康、陸機等人為代表的魏晉四言詩風。如于志寧之作:“水隨灣曲,樹逐風斜。始攀幽桂,更折疏麻。”張后胤的作品:“鶯多谷響,樹密花繁。波流東逝,落照西奔。”皆是模擬魏晉四言詩的對偶技巧,構成雍容大雅、清新明麗之風格。曲池酺飲的唱和方式,也與東晉時期王羲之主持的蘭亭雅集非常接近。可以說,曲池酺飲的唱和,某種程度是晉代蘭亭雅集的再現(xiàn)。此外,有一些詩句也間接反映了唐人四言詩與晉人的聯(lián)系,許敬宗的詩句“雅誥咸蕩,微言殆絕”,與其所監(jiān)修《晉書·儒林傳》的四言論贊“雅誥弗淪,微言復顯”表達方式相似。[15]2367而“雅誥”與“微言”正是唐人四言詩取法前人的標準。
當然,這些四言唱和詩畢竟是唐人所作,在一些創(chuàng)作的細節(jié)方面,又顯示出貞觀詩壇的一些審美風氣。比如詩歌在聲律上遠比《詩經(jīng)》與魏晉詩人來得嚴格。這些作品基本偶句押韻,許敬宗的皇太子釋奠詩將平聲韻與仄聲韻交替使用,曲池酺飲唱和,則是每首八句,除了許敬宗一首押仄聲韻外,其余都是押平韻。每首八句,中二聯(lián)對仗,顯得整齊典雅,節(jié)奏性很強。在寫作技巧上,普遍重視辭藻,純用賦法。《詩經(jīng)》中的比興手法逐漸淡化,而對于煉字方面則更為講究。相比傳統(tǒng)四言略顯呆板的二二句式,顯得更加靈動,如“鶯多谷響,樹密花繁”,形容詞與動詞的使用遠遠比魏晉詩人來得自然生動。可見初唐詩人在南朝詩歌的實踐基礎上,對于描摹物象已然熟極而流,進一步地向精致化的方面發(fā)展。
三、《翰林學士集》四言唱和活動成因探析
四言詩在初唐詩壇的復現(xiàn)與最終消失,值得玩味。初唐詩人何以如此重視四言體式,并在宮廷唱和活動中使用,這與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翰林學士集》中的四言唱和詩的出現(xiàn),是多方面共同造就的結果。其原因可從以下三方面來看:
其一,雅正中和文學觀的影響。《翰林學士集》中的唱和之作,是初唐宮廷詩歌的代表作品,其創(chuàng)作風格深受當時雅正文學觀念的影響。當時宮廷詩人的代表人物虞世南就以“體非雅正”來勸諫唐太宗的宮體詩唱和。北方文人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的評價尤為尖銳:“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8]1730唐太宗作為統(tǒng)治者,內心雖偏愛南朝詩歌,但其《頒示禮樂詔》中曰:“時更戰(zhàn)國,多所未遑,雅道淪喪,歷滋永久。”[16]369在《帝京篇》序言中則主張:“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節(jié)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16]3實際創(chuàng)作的詩歌更是明確表示:“去茲鄭衛(wèi)聲,雅音方可悅。”無論是“雅道”還是“中和”,其實都是對南朝宮體詩的一種有意識的糾正。而四言詩從詩歌體式上就是復古的,是“雅音”的代表,加之四言本身就有簡練、莊重的特點,有一種雍容大雅之美。這種風格特別適合表現(xiàn)宮廷貴族的儀式。故許敬宗等人在宮廷唱和活動中,采取四言詩的方式,既符合當時主流的文學觀,也適用于歌功頌圣的詩歌主旨。當然,貞觀君臣在審美意識上還是深受南朝詩風的影響,文學觀念與創(chuàng)作傾向存在著明顯不完全一致的現(xiàn)象,但許敬宗等人的四言唱和詩可以看作當時雅正文學觀念的一次創(chuàng)作實踐。
其二,君王審美趣味的主導。唐太宗作為貞觀詩壇的主導者,他的審美旨趣往往會成為宮廷詩人創(chuàng)作所依傍的方向。而唐太宗最欣賞的兩位前代文人,就是陸機與王羲之。在《晉書》的編撰之時,唐太宗親筆撰寫《陸機傳》和《王羲之傳》的史論,其重視可見一斑。其在《陸機傳論》中曰:“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15]1487評價之高,可謂空前絕后。從“深而雅”與“博而顯”可以看出太宗所肯定的是陸機文辭中典雅豐贍的風格。唐太宗對王羲之的書法十分喜愛,甚至決定死后以王羲之的《蘭亭序》殉葬。《王羲之傳》論曰:“末代去樸歸華,舒箋點翰,爭相夸尚,競其工拙……所以察詳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15]2107其論雖是從書法著眼,但審美意識仍然透露出了對前代“去樸歸華”之風格的不滿,而對“研精篆素”的王羲之表示出了極大的推崇。統(tǒng)治者的這種藝術審美傾向,當然會直接對宮廷文化產(chǎn)生極大的引導。
而陸機的詩歌,有部分就是四言詩,風格以模仿《詩經(jīng)》為主,其中不乏當時貴族文人的贈答之作,如其《答賈謐詩》、《皇太子賜宴詩》、《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這類作品風格典麗華美,符合唐太宗宮廷的審美趣味。而以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蘭亭序》的偏愛,當然不可能沒有讀過王羲之蘭亭雅集之時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品。故許敬宗等宮廷詩人在唱和過程中采取四言詩的形式,也是一種必然。
其三,郊廟歌詞創(chuàng)作的關聯(lián)。郊廟歌詞在傳統(tǒng)上多用四言體,風格典雅莊重。許敬宗等人進行《曲池酺飲座銘》四言詩唱和之時,正是初唐郊廟音樂創(chuàng)制的時期。《舊唐書·音樂志》記載:“《冬至祀昊天于圓丘樂章》八首,貞觀二年,祖孝孫定雅樂。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作此詞,今行用。”[11]1090《樂府詩集》題解亦曰:“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唐樂,貞觀二年奏之。”[17]這些雅樂之作,是結合南北朝宮廷雅樂而來,就其形式而言,多為四言句式,風格莊重典雅。褚亮、虞世南等人,深受南朝文化之陶冶。其文化淵源,與四言詩唱和者許敬宗、張文琮、沈叔安一致。且許敬宗之父許善心是隋代雅樂歌辭的創(chuàng)作人之一,張文琮之從父弟張文收更是與祖孝孫合作,直接參與了初唐時期的雅樂制作。故貞觀初年,郊廟音樂的創(chuàng)制必然使宮廷詩人重拾對四言詩的寫作熱情。
而許敬宗所作皇太子釋奠之詩,也和郊廟音樂密不可分。《舊唐書·音樂志》記載皇太子親釋奠樂章五首:迎神用承和,皇太子行用承和,登歌奠幣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送神用承和(詞同迎神)。這些儀式中迎神、登歌、奠幣、送神所采用的樂章,皆為典型的四言詩。試舉迎神所用承和為例:“圣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弦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這與許敬宗所作頌詩:“尊師上德,齒學崇年。登歌暢美,啐爵思虔。雩童鼓篋,碩老重筵。辭雕辯囿,矢激言泉。”兩者格調一致,可視之為郊廟歌詞與四言詩創(chuàng)作雙向影響的一個范例。
總之,貞觀時期,宮廷詩人四言詩唱和的興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既與當時主流的雅正文學觀有著密切聯(lián)系,也深受統(tǒng)治者個人審美趣味的影響,此外,同時期創(chuàng)作的郊廟音樂也為宮廷四言詩唱和提供了歷史契機。四言詩在初唐的出現(xiàn)是各種原因綜合的結果。
四、《翰林學士集》四言唱和活動的文學史意義
初唐宮廷詩人的四言詩唱和活動,是傳統(tǒng)四言詩創(chuàng)作的繼承,它的出現(xiàn)在中國詩學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其意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觀察:
(一)《翰林學士集》四言唱和活動是南北朝宮廷詩學觀念的延續(xù)。四言詩在兩晉之后,逐漸進入低潮,但南朝詩人在宮廷文學創(chuàng)作之時,依然不乏佳作問世。顏延之、謝靈運、王融、沈約皆有四言詩流傳于世,昭明太子蕭統(tǒng)更是作《示徐州弟》詩四言十二章,以贈其弟蕭綱,抒發(fā)兄弟之情。這些充分顯示了四言詩在南朝貴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視程度。從南北朝到初唐,四言詩雖然并非主流詩體,然而在宮廷活動中,依然有一定的地位。許敬宗等人編選的《文館詞林》,今殘存詩五卷,時間跨度從漢魏直至隋代,均為唐前四言詩。其中現(xiàn)存四言詩選中,后漢1首,西晉29首,東晉15首,宋詩8首,南齊詩10首,梁詩20首,后魏詩2首,隋詩3首。[18]上層文人的贈答與釋奠等貴族文化活動成為詩歌的主要題材。而以《詩經(jīng)》為傳統(tǒng)的四言詩,正是格調雅正的代表,在思想上符合統(tǒng)治者的要求,且四言詩之雍容舒緩,注重辭藻的詩體特征也能為受到傳統(tǒng)南朝文化熏陶的宮廷詩人所接受。《翰林學士集》中所收錄的四言唱和詩是初唐詩人接受南北朝宮廷傳統(tǒng)文化之后,在創(chuàng)作中取法前代上層貴族作家四言詩創(chuàng)作的明證。
(二)《翰林學士集》中的四言唱和詩也是唐代宮廷唱和活動中四言體式的“絕響”。如前文所言,初唐宮廷詩人其文化淵源多來自南朝文學,他們或直接受到南朝宮廷詩學的熏陶,或在家族文化傳統(tǒng)中受到江南文化的影響,由此形成的文化氛圍,直接影響到了宮廷唱和活動。但是在貞觀之后,宮廷詩人在文學活動中,并不以四言為重,即便許敬宗本人,在之后的宮廷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不以四言為主,其“頌體詩”的形式,多通過五言形式來表達。主要的原因當在于四言的節(jié)奏過于單調,不及五言靈活,且五言詩歷經(jīng)南朝詩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其成熟程度已達到很高的地步,四言詩難以與之匹敵。而在武則天、中宗之后,七言律詩在宮廷唱和中逐漸出現(xiàn),七言句式氣勢流宕,句法比五言詩更為多變,藝術表現(xiàn)力遠超四言。故四言詩逐漸退出了唐代宮廷文學的舞臺,實屬必然。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初唐詩人在此之上進行的探索與嘗試。宮廷唱和活動作為當時主流的文學活動,具有不可替代的導向作用。從四言到五言,直至最后的七言,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唐代宮廷詩人創(chuàng)作活動中對詩歌藝術的認識與審美態(tài)度的轉變。
(三)《翰林學士集》中的四言詩唱和活動,對唐代的復古派詩人產(chǎn)生過一定的影響。四言詩一般多為“二二”句式,較為板滯。隨著唐人對于詩歌聲律鉆研的日益精密,李嶠、張說、沈佺期、宋之問等為代表的新變派詩歌,追求聲律辭藻的形式美學。遭受冷落的四言詩,只能散見于唐代復古派詩人的創(chuàng)作中。初唐復古派代表陳子昂,參與洛陽王明府山亭唱和活動,有《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四言詩作;盛唐大詩人李白是復古派健將,在理論上重視四言,他曾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調俳優(yōu)哉!”[19]可惜他的四言詩作品其名不著。中唐復古派領袖韓愈、柳宗元,亦有四言詩作品傳世,韓愈的《元和圣德詩》,柳宗元有《奉平淮夷雅表》,有一定影響。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中感嘆說:“獨唐韓、柳《元和圣德詩》、《平淮西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后人所及。自時厥后,學詩者日以聲律為尚,而四言益鮮矣。”[20]當然,無論陳子昂李太白還是韓愈、柳宗元,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四言詩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影響,都已被其五七言詩掩蓋。但《翰林學士集》中的四言唱和詩作為唐人四言詩的先聲,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范式作用。
綜上所述,初唐宮廷詩人的四言詩唱和活動,并非單純是一次偶然的文學創(chuàng)作,它沿襲魏晉南北朝宮廷文學傳統(tǒng),其產(chǎn)生原因與貞觀時期的政治意識與文學建設以及君王的個人審美意識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唐人的宮廷詩學創(chuàng)作的標本性案例,對唐詩后來的發(fā)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大唐的詩學正是在這基礎上逐漸融合、發(fā)展,逐步走向新的輝煌。
參考文獻:
[1][清]嚴可均,輯.全晉文[G].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820.
[2][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67.
[3][梁]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3.
[4][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輯錄.清詩話[G],北京:中華書局,1963:780.
[5]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8:49.
[6]彭慶生.初唐詩歌系年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30-31.
[7]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15.
[8][唐]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9][唐]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202.
[10][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M].北京:中華書局, 1994:1131.
[11][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2][唐]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2953.
[13][宋]范成大,撰.陸振從,校點.吳郡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6:315.
[1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5][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6][唐]李世民,撰.吳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7][宋]郭茂倩.樂府詩集[M].中華書局,1979:2.
[18][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 2001.
[19][唐]孟啟,等.本事詩本事詞[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16.
[20][明]吳訥.文章辯體序說文體明辯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30-31.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