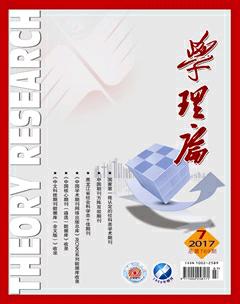清末幼教機構研究
楊莉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南京 210023)
摘 要:湖北幼稚園是中國第一所官辦幼稚園。在此之前,中國兒童教育基本都是在家庭內部進行的。20世紀初,以湖北幼稚園的誕生為轉折,中國近代幼教機構開始產生并逐步發展,中國兒童教育也逐漸學校化、機構化、社會化,幼教領域展現出新的面貌與風采。本文將以湖北幼稚園為個案研究對象,分析其產生的社會背景、推動力量、籌辦始末、教育模式、對后世的影響等諸多問題,從而歸納出清末新政時期以湖北幼稚園為代表的幼教機構所共有的西學東漸的特點。
關鍵詞:湖北幼稚園;張之洞;學習日本;西學東漸
中圖分類號:K2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7-0166-03
中國兒童教育的發展,在20世紀逐漸由傳統走向現代,其中最明顯的表現莫過于教育兒童的責任開始由家庭轉向社會機構。湖北幼稚園——中國第一所官辦幼稚園的創辦標志著兒童教育已然突破傳統家庭教育的框架,代際間的文化傳遞方式也從家庭內部逐漸學校化、機構化、社會化。一方面,傳統兒童教育的近代轉型暗合了中國“家天下”崩潰的社會背景;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鋒與碰撞,順應了近代西學東漸的發展趨勢。
一、更生的契機——清末幼教機構出現的社會背景分析
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有著重視兒童教育的傳統,且幼教方式無一例外都選擇了在家庭內部進行。直到20世紀,家庭式的兒童教育逐漸被各種社會幼教機構取代,幼教的責任也由家庭轉嫁給社會。
(一)從“育嬰堂”出發的社會育嬰機構
育嬰堂作為清代社會專業的慈善機構,主要負責把被遺棄的嬰孩收入堂內,由社會承擔起哺育的責任,使他們有所歸依。“育嬰堂”式的保育包含對收養嬰孩必要的啟蒙教育以及知識與技能的傳授,“擇其秀者,教以讀書寫字,粗笨者,教之打草鞋,打繩索,編竹器篾籃,以及一切皆可以自食其力之事。”如此育嬰堂初步具備了一些公共教育的社會功能。
然而育嬰堂到底還是慈善性質,與教育性質的幼稚園有明顯差別。第一,育嬰堂對入堂嬰孩有嚴格的限制,只有“父母俱亡赤貧待斃者”才能被接受,富貴家庭不愿將子嗣送入堂中,而貧窮家庭則不能;第二,由于育嬰堂里傳授知識的多是雇傭的專職乳婦,受囿于乳婦自身的認知水平,她們很難對孩童進行系統有效的教導,故其在教育內容上與民間家庭教育并無區別;第三,由于清廷只將育嬰事業作為標榜仁政的“道婆之政”,對育嬰堂的關注也難免聊勝于無,再加上各地育嬰堂長期受著經費來源不穩定的制約,因此難免時存時沒。
(二)傳教士來華辦學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憑借《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獲得的在華居住和自由設立學校的特權,開始創辦各種學校。據美國傳教士林樂知統計,當時外國在中國設的幼教機構“有小孩察物學堂(即幼稚園,作者注)六所,學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
教會幼兒園采用福祿貝爾教育法,十分注重兒童的身心發展。有美麗的教室、小巧的設備,并且十分注重游戲、恩物的意義與價值。傳教士還通過出版兒童報刊來啟迪兒童思想,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當時的兒童報刊如《小孩月報》《福幼報》等都相當有影響力。
所以,盡管教會幼兒園只是來華傳教士傳教布道的一種輔助手段,但其有計劃的教育活動、注意培養兒童實際操作能力的理念,嚴重沖擊了中國以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的兒童教育,這也使一大批有識之士開始探索兒童教育科學化的道路。
(三)中國有識之士的思想推動
最早倡導兒童公育思想的是康有為。康在1844年寫《禮運注》時提出“人人教養于公產而不恃私產”,后他又在《大同書》中首次設想了從胎教到學前教育的完整的兒童公育體系:“自三歲至五歲入”慈幼院,“以其(女保)代為眾母,非其子而撫之如子”。
追隨康有為兒童公育思想的是梁啟超。19世紀90年代末,梁啟超在《論幼學》中明確表示他對兒童教育的關心:“人生百年,立于幼學”。然此時的梁啟超雖關注幼學,但幼教觀念僅局限在批判傳統兒童教育“惟苦口呆讀”上,絲毫未提及設立幼稚園。待其變法失敗東渡日本,梁的幼教思想便打破了原先局限在家庭教育范疇內談論幼學的束縛。1902年梁在《教育政策私議》中明確表示學齡前兒童應入幼稚園學習兩年。梁啟超由家庭教育向兒童公育思想的轉變可謂當時有識之士幼學思想轉變的一大典型。
同時代的羅振玉也有此想。1901年羅振玉在《教育私議》中提出“至嬰兒于未就傅之歲,宜設幼稚園,選保姆保育之,導以運動、游戲、歌曲等,以長養其身體而戶牖其智慧。”次年又在《學制私議》上進一步估測“將來必立幼稚園,以三歲至五歲為保育年限。”
由此可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兒童公育思想已然浮出水面。在他們的有心推動下,中國幼教機構的創辦勢在必行。
二、陳格的變易——湖北首開風氣,幼教奠基
當兒童公育思想在晚清中國愈演愈烈時,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中國首所官辦幼稚園終于在湖北獲得實踐。
(一)張文襄公督鄂
在集權專制的中國,任何革故鼎新都與行政首腦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光緒十五年,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在張之洞心中,有對教育興國最忠貞的信仰。他認為,“自強之策,以教育人才為先;教戰之方,以設立學堂為本”;又認為“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理在學”,形成了“國勢之強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長在學校;環球各國競長爭雄,莫不以教育為興邦之急務”的教育功利觀。
于是他決定大力興辦學校。同時他也認為必須藉西學益華人之智創辦新學,引進西學西藝,鞏固“中體”。他要求所培養的學生,不但要“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而且要“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教育觀、人才觀為西學的引進打開了方便之門,加速了湖北乃至全國教育的近代化。
除此以外如何確保教育經費的充足與穩定亦是棘手的難題。晚清中國在戰爭頻繁、賠款外債的逼迫下,國家自身早已財政困頓、應接不暇,根本沒有財政預算和政府直撥專款的條件。于是湖北主政人員從民間捐贈和官款分撥兩方出發,竭盡所能籌集經費,為包括湖北幼稚園在內的新式學堂的興起提供了財力的保障。
關于湖北地方籌措經費,一方面是沿襲成法,即仿傳統辦學接受民間捐贈,鼓勵民間個人以不同形式為新興教育事業做出貢獻。張之洞本人就曾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率先捐出湖廣總督兼職湖北巡撫公費18 000兩,悉數移交湖北學務處充教育經費。另一方面是依靠地方政府從有關公款中挪借擠用。公款費用主要抽自鹽道、統捐局和厘簽局等機構,光緒二十九年,署理湖廣總督端方將“川淮入鄂之鹽,每斤加抽4文用作興學等費用(其中用作興學費一般為40—50萬兩),同年還開掘到漢口簽捐局彩票盈余這一款源”。
(二)外來經驗保障:湖北幼稚園的準備與學習日本
20世紀初的中國沒有辦近代教育的實踐,以張之洞為首的教育改革籌劃者往往“不得不講西學”。當時在我國境內創辦幼教機構有兩種名稱:一種叫蒙養院,一種叫幼稚園。“代表蒙養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種代表幼稚園的卻是出于教會的手澤。”
1.極力排斥教會式幼稚園
如上所述,西方傳教士雖早早溯江而上,但在國內反洋教事件風起云涌的背景下,傳教士普通的育嬰活動卻也常常以政治風潮的形式出現。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不久,法國天主教在南昌成立教堂,嗣后即因育嬰謠言引發教案,總理衙門遂頒行《傳教章程》,首條即要求教會不要介入育嬰活動。然外國勢力極力抵制,有關教會育嬰的謠言也從未停息。19世紀80年代末,廣東再次因此爆發教案,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上《商定稽查外國育嬰辦法折》,其中詳細描述其情形:“竊自通商以來,外國教士在各口岸每設有育嬰堂收養嬰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復不少。在彼以行善圖名,未必遽加殘害,無如民間訛言易滋疑惑,遇有嬰孩病故,道聽途說,輒謂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輾轉傳述激成眾怒,因而焚毀教堂,殺戮教士,事變倉卒,遂至一發難收,類此之案,不勝枚舉。”面對內外交困,清政府除對“涉案”民眾嚴酷鎮壓并盡力賠款外,也認識到教案常因教會育嬰謠言而起,因而鼓勵本國育嬰事業發展以消除禍根。
2.備受青睞的日式幼稚機構
張之洞曾概括中國學習日式幼教之原因:“東瀛風土文字,皆與中國相近,華人僑寓者亦多,翻譯易得,便于游覽詢問,受益較速,回華較早。且日本諸事雖仿西法,然多有參酌本國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刪減變通者,與中國采用尤為相宜”,且我國“于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中國之性質無歧趨,則而行之,無害而有功”。因此,學習日本成為清末興起的一批幼稚園的主要特征。關于如何學習辦學經驗,大致有如下三種途徑。
一是邀請外國顧問。清末掌權朝臣面臨清廷危機,往往利用權柄直接聘請外國顧問,以助充分“師夷長技”。單就湖廣總督張之洞而言,他的幕府中就有大量洋員。據筆者統計,張之洞幕府洋員共239人,其中日本洋員80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日本洋員中,又有76%的人從事學堂教習。由此可見,張之洞聘請日本顧問、學習日式教育實乃有據可憑。
二是請教歸國駐外使節和留學生。張之洞關注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與留日歸國人士的接觸與交流。1901年底,張之洞派羅振玉等人前往日本,羅振玉一行在考察日本教育時也關注了日本幼稚園的情況,給張之洞很大啟發。還有幫助張之洞制定癸卯學制的劉邦驥,也是在日本留學過四年、對日本教育情況極其了解的人士。
三是高薪聘請洋教習。在汪向榮著的《日本教習》中大量記載了清末赴華從事教育事業的日本教習,湖北幼稚園的第一任園長就是張之洞聘請的日本女教習戶野美知慧,她仿照日本幼稚園的教育模式訂立了《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讓清末興起的幼稚園走上仿日的道路。
三、蒙養的新生——湖北幼稚園的創辦與發展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撫端方在武昌閱馬場創辦幼稚園,聘請了戶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保姆負責經辦,并擬定了《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中國幼教機構就此誕生。
(一)借鑒與移植東洋兒童教育
湖北幼稚園的籌劃、建立和經營,主要由三位日本女教習主持。她們參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定》來設計湖北幼稚園,將在日本所學幼教之識完全照搬于此,制定了光緒三十年的《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
在保育宗旨方面,湖北幼稚園著重要求對兒童自然智能和涵養德性的開發,具體提出兒童要在體育、智育、德育方面全面發展,這種濃重的德、智、體育色彩深受日本幼教宗旨的影響。光緒二十八年,張之洞上奏《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明確提出中國教育要學日本實行德智體三育:“考日本教育總義,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端,洵可謂體用兼賅,先后有序,禮失求野,誠足為我前事之師。”湖北幼稚園正是這種日式幼教大義的具體實踐。
在教學內容方面,湖北幼稚園開設的七門課程中,有“游戲、唱歌、訓話、手技”四門完全照搬了日本保育條目,課程中甚至還有日語課程的學習,“唱日本翻譯改訂的幼稚園歌曲”。這在方便日本保姆教習幼兒的同時,也給湖北幼稚園烙上了“日本化”的印記。
在保教對象上,中日均明確規定孩童年歲必須3歲以上方可入園,每個保姆平均育兒人數湖北方面大概27人前后,日本規定的較為寬泛,即每保姆育兒不超過40人,然仍可見湖北幼稚園規定的保姆幼兒比其實也是符合日本保育規定的。
再細致到校舍設備,湖北幼稚園的硬性設備也像是對日本章程的擴展性解釋:保育室分成開誘室、訓話室,游戲室又有游戲場、游戲山等設備,職員室有保姆助教休息室、會計辦公室、接應賓客室等等,盡善盡美地勾勒出了日本章程所要求的物理環境與空間的設計布置。
至于在保育年限與具體每日保育時間上,兩者雖不甚一致,但若從整體結構上觀,卻是日本于1899年在幼教上規定了哪些方面,湖北幼稚園也對此相應做出反應。由上可知,湖北兒童教育的近代化,育兒新知在湖北幼稚園的登堂入室,完全是借鑒移植東洋文化的結果。
(二)癸卯學制頒布后的湖北幼稚園
中國早期幼教機構雖竭力模仿日本,但與日本創辦的幼稚園仍有一最大不同,即日本先有學制,后來創辦幼稚園;而湖北幼稚園創辦之時中國新的學制尚未建成。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湖北幼稚園開辦后的幾個月,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其中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規定:幼兒機構為蒙養院,“專為保育教導三歲以上至七歲之兒童”。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很大程度上也模仿了日式幼教規章,要求教導兒童“專在發展其身體,漸啟其心知”“體察幼兒身體氣力之所能為,心力知覺之所能及,斷不可強授以難記難解之事”;在保育時間和教育課程上,規定蒙養院兒童在院時間每日不得超過4點鐘,課程分為游戲、歌謠、談話、手技四項,這些均與湖北幼稚園相符,晚清政府可以說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湖北幼稚園的開辦原則,也肯定了這種依靠社會機構辦學育兒的近代幼教模式。
但湖北幼稚園在癸卯學制頒布后還是遇到了危機,尤其表現在師資來源方面。湖北幼稚園開辦之初,園內選聘的主要是由畢業于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戶野美知慧女士等3名日本保姆任教員。其后張之洞料到幼教風氣大開之日,幼師必然奇缺,于是首開在幼稚園內附設幼稚師范學校先例。于是在他的親自主持下,湖北幼稚園內附設了女子學堂,招收年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女子,專習幼兒師范課程,成為轟動一時的盛舉。
然設女子專門學校與癸卯學制相悖,章程明文禁止在蒙養院中附女子學堂,說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斷不宜令其結隊入學”。于是湖北幼稚園中的女子學堂在剛創辦不久后就被停辦了。在禁止女學的同時,為了解決幼兒師資問題,清廷即令各省廳州縣分別在育嬰堂和敬節堂內劃出一院為蒙養院,在蒙養院內為乳媼及保姆講習保育教導幼兒之事。培訓所使用的教科書是從《孝經》《四書》《女誡》《女訓》及《教女遺規》等書中摘錄部分內容而加以編排,當然也“選取外國家庭教育之書,擇其平正簡易,與中國婦道婦職不相悖者”加以教導,由此培訓出來的乳媼節婦自然成為“三從四德”模范的執行者和宣傳者。清廷這一舉措不僅扼殺了早期女子專門教育,而且相較于師范生育兒,這些保姆在如何科學合理開發兒童自然心性智能方面也難免缺乏專業。就此,湖北幼稚園的師資來源經歷了從培養專業的女師范生變成了“所學較淺”、然“遠勝于尋常之女傭”的乳媼節婦。
四、結語——湖北幼稚園創辦始末特點之西學東漸
湖北幼稚園誕生于清末新政時期,清末新政是一種適應性改革,其中的自救努力,是內外交困下迫不得已的選擇,幼稚園的出現也不例外。從前文可知,幼教機構得以產生,一是盼望教育興國、救國自強事;二是傳教士辦學引發國人不滿情緒,急欲自創以打擊之。然無論何種原因,概括講來都是來自西方的沖擊刺激了中國本土的改變,讓兒童教育囿于家庭的現象戛然止步。當然光有刺激顯然不夠,張之洞曾言,“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就幼教方面而言,時人選擇了向日本學習,讓湖北幼稚園在癸卯學制頒布前奇跡地走上國際化、現代化的軌道。
晚清幼教在近代轉型過程中同時也兼顧了“中體”。湖北幼稚園成立之初,日本女教習模仿日式規劃校園,但癸卯學制頒布后,湖北幼稚園也不得不“削足適履”,在教育的最重要環節——師資方面讓步,體現了清廷絕不容許踐踏封建倫常的堅持。
除了學習內容、師資來源必須符合“中體”外,幼稚園最明顯的局限在于,那個時代的教育本身是與當地政府官員是否重視教育息息相關的。因為教育本身在晚清并不獨立,經費也無穩定來源,因此它的發展完全受著地方行政人員的控制,也就難保“人亡政息”。
參考文獻:
[1]趙建群.試述清代拯救女嬰的社會措施[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4).
[2]中國學前教育史編寫組.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3]楊云舒.從育嬰堂到蒙養院:論早期學前教育的現代化轉型[J].青年文學家,2010(12).
[4]卞利等.民間文獻與地域中國研究[M].合肥:黃山書社,2010.
[5]林樂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M].廣學會譯.1903.
[6]包鋒.教會幼稚園的興辦與中國新式幼兒教育的產生[J].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08(16).
[7]康有為.孟子微[M].北京:中華書局,1987.
[8]康有為.大同書[M].上海:中華書局,1935.
[9]梁啟超.變法通議[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M].上海:中華書局,1936.
[11]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2]張之洞.勸學篇[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3]舒新城.中國近代史教育史資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4]董寶良,熊賢君.從湖北看中國教育近代化[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15]張之洞.張之洞全集[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6]黎仁凱.張之洞幕府[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
[17]劉彥華.中國學前教育史[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