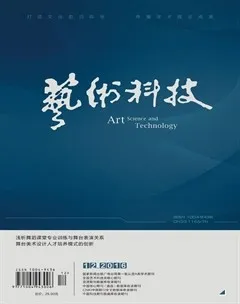淺談“開放式教學(xué)法”在高校攝影課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龔延恒
摘 要:“攝影基礎(chǔ)課程”是一門技術(shù)性和應(yīng)用性很強(qiáng)的綜合性課程,集基本理論、攝影實(shí)踐與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于一身。“開放式教學(xué)法”就是教師在自由民主、開放平等的課堂氛圍中,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的主體能動(dòng)作用。隨著我國教育事業(yè)的不斷發(fā)展,攝影教學(xué)方法也要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與時(shí)俱進(jìn),要能夠有效地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的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開放式教學(xué)法”在“攝影基礎(chǔ)課程”教學(xué)中效果明顯,深受廣大師生的歡迎。
關(guān)鍵詞:攝影基礎(chǔ);“開放式教學(xué)”;教學(xué)情境;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策略
“攝影基礎(chǔ)”是一門實(shí)踐性和實(shí)用性都很強(qiáng)的課程,當(dāng)前高校選修“攝影基礎(chǔ)”的學(xué)生逐漸增多。但我國高校在其教育方式上普遍存在注入式教學(xué)、教條式教學(xué)等問題,嚴(yán)重影響了學(xué)生的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能力。在全社會(huì)迫切要求培養(yǎng)應(yīng)用型人才的大背景下,高校也在尋求教學(xué)方法改革之路,不少高校把“開放式教學(xué)法”引入攝影課堂教學(xué)中,著力提高大學(xué)生的鑒賞能力和審美意識。因此,加強(qiáng)對“開放式教學(xué)法”的應(yīng)用策略研究至關(guān)重要。
1 “開放式教學(xué)法”
“開放式教學(xué)法”的基本內(nèi)涵:
“開放式教學(xué)”是相對“封閉式教學(xué)”而言的。“開放式教學(xué)法”,就是教師根據(jù)攝影基礎(chǔ)課程的特點(diǎn),靈活設(shè)計(jì)課堂內(nèi)容,營造民主平等、和諧自由的課堂環(huán)境,引導(dǎo)學(xué)生在各個(gè)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都能積極學(xué)習(xí)、主動(dòng)練習(xí)、提高能力的教學(xué)方法。“開放式教學(xué)法”,是教學(xué)思想、教學(xué)方法的開放,能夠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的主體作用和教師的主導(dǎo)作用;是課堂教學(xué)環(huán)境的開放,教學(xué)地點(diǎn)可以在野外、城市、社會(huì)活動(dòng)等環(huán)境中;是教學(xué)題材的開放,教師可以選擇教材、生活或?qū)W生等作為教學(xué)題材,可以編制開放性的綜合題來訓(xùn)練學(xué)生;是師生關(guān)系的開放,教師既是指導(dǎo)者,也是參與者,其不斷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探索研究、主動(dòng)獲取知識。總之,“開放式教學(xué)法”是對“封閉式教學(xué)法”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能給學(xué)生提供更多的參與機(jī)會(huì)、發(fā)展機(jī)會(huì)和成功機(jī)會(huì),有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必要的社會(huì)品質(zhì)。
2 “開放式教學(xué)”在高校攝影課中的重要性
2.1 教學(xué)思想上有利于營造和諧的課堂氛圍
“開放式教學(xué)法”秉持“學(xué)生主體、教師主導(dǎo)”的教學(xué)思想,教師想方設(shè)法地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積極性,使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課堂互動(dòng),勇于表達(dá)自己感受,喚起學(xué)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培養(yǎng)其發(fā)散思維能力。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過程中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對所提問題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并利用攝影設(shè)備拍攝自己感興趣的題材,在“玩中學(xué)、學(xué)中玩”,感受攝影藝術(shù)的魅力。
2.2 教學(xué)內(nèi)容上有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獨(dú)立思考能力
攝影是一門藝術(shù),要求攝影者善于觀察、獨(dú)立思考,用攝影作品來記錄生活中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通過作品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觀點(diǎn)。“開放式教學(xué)法”,對攝影課的課堂內(nèi)容不予以限制,可以在課堂上展示優(yōu)秀的攝影作品,可以到攝影實(shí)訓(xùn)基地進(jìn)行實(shí)地拍攝,也可以瀏覽國內(nèi)外著名攝影網(wǎng)站上的大量優(yōu)秀作品,在形象刺激與累積過程中使學(xué)生獲得感悟,以此來激發(fā)學(xué)生的思考能力,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
2.3 教學(xué)方式上有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個(gè)性創(chuàng)新能力
攝影屬于實(shí)踐重于理論的綜合性學(xué)科,學(xué)生拍攝的作品質(zhì)量是學(xué)生掌握知識與技能的重要體現(xiàn)。“開放式教學(xué)法”,尊重學(xué)生個(gè)性,充分發(fā)揮每一位學(xué)生的攝影潛能;“開放式教學(xué)法”,解放學(xué)生“天性”,教師當(dāng)“教練”,學(xué)生當(dāng)“運(yùn)動(dòng)員”,教師的作用是啟發(fā)、引導(dǎo)、督促學(xué)生多做多練,而不是越俎代庖。教師放手讓學(xué)生去做、去練,并要求學(xué)生大膽實(shí)踐和不斷創(chuàng)新;要構(gòu)思新穎、角度獨(dú)特,善于運(yùn)用一些與眾不同的技巧來創(chuàng)作;從而讓每一位學(xué)生都成為美的創(chuàng)造者。
3 “開放式教學(xué)法”在高校攝影課中的應(yīng)用策略
3.1 創(chuàng)設(shè)攝影教學(xué)情境,激發(fā)學(xué)習(xí)攝影興趣
教師根據(jù)高校攝影課教學(xué)目標(biāo)和教學(xué)內(nèi)容,結(jié)合學(xué)生生活實(shí)際和攝影知識經(jīng)驗(yàn),巧妙設(shè)置一個(gè)形象生動(dòng)、情感豐富和美感十足的攝影教學(xué)情境,讓學(xué)生能在自由寬松的環(huán)境中學(xué)習(xí)攝影知識技能。教師可以應(yīng)用多媒體電腦演示攝影圖片,也可以舉辦各種高層次攝影展覽和攝影學(xué)術(shù)講座,從而激發(fā)大學(xué)生強(qiáng)烈的學(xué)習(xí)攝影的興趣,使其始終有“我要學(xué)習(xí)攝影”強(qiáng)烈欲望,為其積極主動(dòng)探索攝影審美理論和掌握嫻熟攝影技能等提供動(dòng)力。
3.2 布置開放式攝影作業(yè),培養(yǎng)學(xué)生發(fā)散思維能力
開放式攝影作業(yè)的顯著特征就是答案的不唯一性,教師可以引導(dǎo)大學(xué)生對答案進(jìn)行分析比較、評價(jià)優(yōu)劣,促使其發(fā)現(xiàn)美的所在和創(chuàng)造美的途徑,從而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的發(fā)散思維能力。布置開放式作業(yè),作業(yè)既要含有學(xué)生已有的知識和技能,又要涵蓋將要學(xué)習(xí)的新知識和新技能;要根據(jù)個(gè)人喜好來選擇拍攝主題,給學(xué)生“留白”,給其充足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空間,使其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作業(yè)難易程度的設(shè)定要在讓學(xué)生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的前提下、在有限的時(shí)間內(nèi)能夠完成。學(xué)生完成作業(yè)后,教師要及時(shí)組織學(xué)生對作業(yè)進(jìn)行點(diǎn)評,可以在集體評論的基礎(chǔ)上提煉出有價(jià)值的建議,也可以針對學(xué)生的個(gè)別問題進(jìn)行個(gè)人點(diǎn)評,以此來大大激發(fā)學(xué)生的發(fā)散思維能力。
3.3 整合攝影教學(xué)資源,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
教師要整合利用校內(nèi)外各種攝影教學(xué)資源,使學(xué)生全面學(xué)習(xí)攝影知識和熟練掌握攝影技能。其可以展示攝影作品,讓學(xué)生探索和發(fā)現(xiàn)大自然的和諧之美;可以組織學(xué)生深入現(xiàn)實(shí)生活,學(xué)會(huì)面對生活、觀察生活,發(fā)現(xiàn)生活中的價(jià)值、捕捉生活中的閃光點(diǎn),從而提煉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攝影創(chuàng)作主題,為攝影創(chuàng)作提供充足養(yǎng)分和能量;也可以布置內(nèi)容不限的課后作業(yè),讓學(xué)生在課堂里展示自己的作品,暢談自己的攝影感受,進(jìn)一步激發(fā)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能力;還可以組織學(xué)生攝影采風(fēng),在生活中尋找攝影題材,拍攝他們想拍攝的事物,以提高學(xué)生對社會(huì)的認(rèn)識程度,增進(jìn)學(xué)生之間的情誼,讓學(xué)生認(rèn)識自己的獨(dú)特性,并挖掘自己的內(nèi)在潛能。
4 結(jié)語
“開放式教學(xué)法”對高校攝影課而言,無疑是激發(fā)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提高其學(xué)習(xí)能力,促使其掌握攝影技巧的“一劑良藥”。在強(qiáng)調(diào)素質(zhì)教育的今天,高校應(yīng)高度重視“開放式教學(xué)法”在攝影課程中的應(yīng)用,使攝影課能真正地提高大學(xué)生的鑒賞能力和審美意識,能使其形成良好的個(gè)性心理品質(zhì)和審美情趣,從而開啟大學(xué)生幸福、健康的人生之旅。
參考文獻(xiàn):
[1] 段旭光.當(dāng)前高校攝影教學(xué)的思考[J].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2009(32):198-199.
[2] 孫鋼軍.開放式教學(xué)在新聞攝影課中的應(yīng)用[J].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2):78-80.
[3] 張泉?jiǎng)?對當(dāng)前高校攝影教育的幾點(diǎn)思考[J].美術(shù)教育研究,2012(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