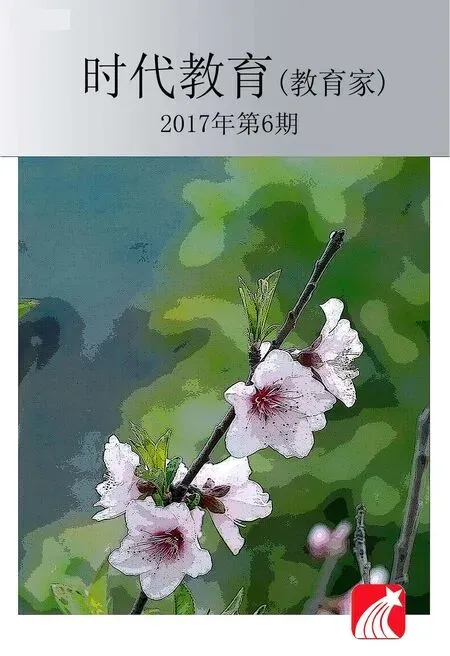視點
視點
VIEW POINT

喪文化:為什么年輕人喜歡頹喪、自嘲與負能量
去年流行的“葛優躺”僅僅是這場青年亞文化的開端,隨后類似氣質的文字與形象席卷了整個社交網絡,這其中對我們來說最為熟知的“喪文化”有:代表美國中產階級空虛生活無奈的動漫《馬男波杰克》;反映日本年輕人生活現狀的影視劇如《逃避可恥但有用》《瀨戶內海》《我不受歡迎,怎么想都是你們的錯》;中國本土的“每天一點負能量”,彩虹樂團的《感覺身體被掏空》等。這些內容與前些年流行心靈雞湯所倡導“努力就會成功”的道理剛好相反,常常是“一天又過去了,是不是離夢想又更遠了”“真正努力過的人,就會明白天賦的重要”“這么努力,忍受那么多寂寞和糾結,我們也沒覺得你有多優秀”……
@拾文化:
有人說,喪文化是“垮掉的一代"這種歷史專有名詞,因為喪文化與頹廢消極、不思進取極其相似。其實,不管喪的姿態如何負能量,它都是困在生活中的一種無奈的自我疏導。事實上,只要你仔細觀察這個群體,會發現這樣一個現象,群體的想法普遍是這樣的:一份既能放肆的玩耍又能開心生活的工作,不能太閑,也不能太忙。這群天天抱怨著不想上班的年輕人 ,并非完全不想付出勞動。而是他們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看重個人價值的體現。
@新芽:
這種文化正是那些不停地經歷著加班、經歷著睡眠不足,買不起房沒時間談戀愛的“空巢青年"的積憤與怨念,進而發出的自嘲式的調侃,也可以說是一種溫柔的反抗。說到底,“喪文化"是年輕人借助互聯網宣泄負面情緒的一種形式。用心理學人士的話說,主體通過這樣的表層自我否定,似乎可以起到“堵住他人之口"的效果,減輕或免受他人攻擊,以避免可能帶來的更大痛苦——“我都承認我是個廢物了,那你還能怎樣對我的人生指手畫腳呢?"
@張小敏:
作為獨生子女的90后青年們,他們承受著社會轉型的巨大壓力。他們暢想著“我希望,我以后可以讓世界為我有一點點改變。"然而,當今飛速發展的科技,全球化下多元文化的沖擊,身份的焦慮,認同的危機,穩定的生活顯得遙不可及,年輕人祈愿著:不要再被每天的變化追著跑了。所以,年輕人對“喪文化"的喜愛,時常掛在嘴邊的自嘲,其實更多的時候只是把它當作一種解壓方式,傳達的只是某種生活狀態而不一定是價值觀的站隊。在某些時候,適當放低姿態、首先自我開涮則是一種拉近關系的社交辭令。
@小茗:
雖然喪文化的句子個個都很頹喪,但卻戳中了很多事實真相。一方面,每個時代大多數人都會無足輕重,也許之前蕓蕓眾生沒有任何發聲的渠道,現在互聯網給了大家發聲的機會,那么這種生存的焦慮、對意義的尋求就會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在現代化的生活中感到挫敗是一件尋常的事情,我們越來越被席卷入宏大的世界中,無法脫身,無法隱匿,只能接受挑戰與失敗。
輟學生逆襲
5月25日,扎克伯格在輟學13年后,重回母校哈佛大學發表畢業演講,并獲頒哈佛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扎克伯格對此次演講十分重視,不僅曾向同樣從哈佛輟學的前輩比爾·蓋茨取經,還于當日一大早更新狀態,“媽,人家跟你保證過一定會重返學校,拿到學位的!”“完成這個演講,將是我在哈佛第一次真正完成某件事情。”
@扎克伯格:
你們當中多少人還確切記得,當初收到哈佛錄取通知郵件時在做什么?當時我正在玩《文明》游戲,然后我跑下樓,找到父親,不過他的反應很奇怪,居然開始拍攝我打開郵件的過程。那個視頻可能看著挺難過吧。但我發誓,被哈佛錄取,是最令我父母為我感到驕傲的事情。
今天我想談談目標,但我不是來給你們做一些程序化的宣言,告訴你們如何發現目標的。我們是千禧一代,我們會出于直覺和本能發現目標。相反地,僅僅發現目標還不夠。我們這代人面臨的挑戰,是創造一個人人都能有使命感的世界。目標是我們意識到我們是比自己更大的東西的一部分,是我們被需要的、我們需要更為之努力的東西。目標能創造真正的快樂。

幼升小,考家長查三代?
據新京報報道,5月6日至7日,上海市集中舉行171所民辦初中、小學入學面談。而自6日起,陸續有家長發布消息稱,部分學校入學面談,對家長提出考核要求,包括要求家長作答類似公務員行測題的問卷,以及填寫包括祖父母學歷在內的背景調查表等。7日晚,上海市教委回應此事稱,已對涉事陽浦小學、青浦世界外國語學校(簡稱青浦世外學校)兩所民辦學校,在全市教育系統內提出通報批評,要求其所在區教育局進行追責,并將要求兩校公開致歉,同時核減下一年度招生計劃。
@肖峰: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娃會打洞",仿若新時期的血統論,父母們硬著頭皮答題,默認社會規則。這個事件的真命題是一次社會階層的提前分化。幼升小就是一次社會階層劃分:或者是按學區房的資本劃分,或者按社會關系劃分,你要是什么都沒有,就只能按智商來劃分了。
@法制晚報:
搞好民辦教育,是為了滿足社會多元化辦學的需求,但其宗旨仍然是為了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這一事件的背后是一些民辦名校在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當下“恃名而驕"的現象。于政府而言,除了要加強公辦學校校際之間教育質量均衡化之外,對民辦學校也需要差異化競爭。為學校劃分不同類別,縮小極少數高端人群特殊化教育的需求,將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向更廣泛群體擴散,來避免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民辦學校之間的不公平競爭。
林奕含:藝術是否具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26歲的女作家林奕含自縊身亡,今年初出版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講述女學生遭補習班名師性侵的故事。自殺前,林奕含接受媒體采訪時證實這是她的親身經歷,告訴讀者這不僅是一個女孩子被誘奸被強暴的故事,也是一個女孩子愛上誘奸犯的故事,并追問:當用語言、修辭將充滿裂縫的思想彌補成美的、堅不可摧的狀態,那么藝術是否具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蘇枕書:
作者以十分痛苦的方式,深深認清這一類男性的虛偽、無知、自私、知識體系的不堪一擊,但自我救贖如此艱難。反映到小說里,李國華從頭至尾對思琪都沒有愛與尊重,只是出于男性的自私、猥瑣、虛偽、欲望,他粗魯殘暴地操控了思琪的人生,林奕含大概無數次替思琪幻想過,如果自己是張愛玲,如果對方是胡蘭成──只要有一點愛,就可以奉獻一切,不問未來,堅持下去,然而沒有。
@映畫臺灣:
生活在一個周遭一切事物皆非簡單化的世界,個人的立場和社會角色會影響他對事件的敘述甚至是認識,主觀性的視角極易導致不可避免的觀點的對立,這也就是古往今來如此諸多“羅生門"出現的原因。真相是“相對"的,即便如此,當我們轉換視角去看待無論是房思琪還是林奕含本人的故事時,當李國華的疑似原型臺灣補習班名師發文強調林奕含的精神隱疾并否定自己是狼師時,這場被“侵入"的慘劇也絕不可也不能演變成《狩獵》(2012 丹麥電影)里無中生有的污蔑。
@吳小曼:
林奕含的寫作無疑是在一層層剝開她的傷口,不僅不能用文學救贖,發現文學甚至是在為事件的發生尋找合理性的借口,這其實是現代小說的困境:讓欲望合法化。林奕含劈開胡蘭成思想的裂縫,也就劈開了李國華的“傳統文化"包裹的虛偽外衣,她所愛戀的部分的坍塌恰恰是對她自我判斷力的否定,原來她甚至是“共犯",這是它不能正視的自身的“黑暗",如果說愛曾減輕過她對性的罪惡感,而一旦獲悉愛不過是借口,其實質是一種權力、思想控制,那么房思琪的結局就是走向瘋狂,而對林奕含來說,卻不僅是個人的幻滅,她還指向了文學本身的幻滅。
@冰橘綠茶:
在師生關系中,一種是男老師赤裸裸的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女學生做交換,交換中存在脅迫的成分;另一種是自以為有知識光環加持半推半就誘惑學生就范,告訴她們為自己喜歡的人做些事情是美好的,兩種行為都令人發指。前者是師生關系中不平等的權力導致權色交易;后者則更難以辨別,且對受害者造成的創傷極大,正如影片《聚焦》中牧師假借信仰之名性侵兒童時,孩子們不知道如何拒絕上帝之手,老師假借愛情之名去誘奸學生時,他們難以分辨這是對方對愛情的表述還是色食性也的本能,一種用美好來裝點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