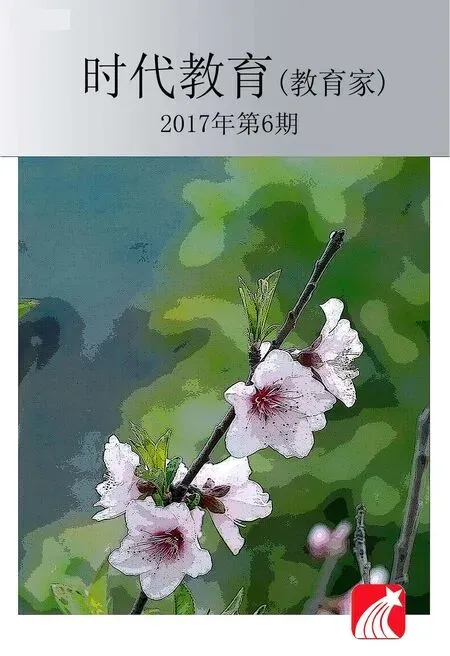亨利·米肖與中國文化
文_張喁 圖片_網絡
亨利·米肖與中國文化
文_張喁 圖片_網絡

亨利·米肖
《我從遙遠的國度給你寫信》,這樣的篇名,放在今天的微信公眾號上,應該沒有人覺得是標題黨,并不能激起很多讀者的好奇和興趣。
但它是法國詩人亨利?米肖(1899—1984)膾炙人口的名篇。亨利?米肖一生是個浪游者,所謂“遙遠的國度”,并沒有說明是曾經游歷的南美洲、印度、中國或日本,因為米肖的詩作以晦澀著稱。
米肖的晦澀具體表現為:一段時期的文字暴虐與受虐,一段時期的向往寂靜,以柔克剛的弱者角度,重設想輕演示的反西方思維。
僅僅“從遙遠的國度給你寫信”以及晦澀,遠不能成就亨利?米肖20世紀法國最重要詩人的名聲。《我從遙遠的國度給你寫信》,突破了在今天看來已經無奇的標題,展現了詩人偉大的神經、超凡的智力和奇幻的想象。更重要的一點,在西方的文學傳統中,異國情調并不罕見,在20世紀及以前,在“歐洲中心”之外,大部分地球和它的原住民,對于“文明的”歐洲讀者而言,都呈現出氤氳和陌生的異域魅力,以及這魅力之后的野蠻和危險性。這種異國情調相當主流,因為它是“歐洲中心論”的,呈現的是歐洲的視角,“文明”的價值觀。
亨利?米肖在“遙遠的國度”中,將自己設身處于遠離歐洲和西方主流文明的地方,那地方亦真亦幻,夾雜著自己的親身游歷和腦中幻想,最重要的,詩中的自己也不再是“自己”,口吻是一位柔弱的女性,代表著東方道家文化的“陰”,而詩中的“你”,則寓意歐洲中心的“陽”——一陰一陽謂之道,這才是亨利?米肖的殺手锏。
更甚于此的著作《一個野蠻人在亞洲》,是詩人1930年后游歷亞洲后,直截了當地將自己的“歐洲文明”身份和亞洲表面晦暗的現實顛倒過來,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反思,而是寧愿矯枉過正,用徹底扭轉的視角看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
在詩人最喜歡的印度和中國,青年米肖眼中并沒有這里的政治、經濟,連市井生活和風土人情似乎也提不起他的興趣。或許為這一次冥冥中注定的游歷,詩人已經準備了很多年,以便擺脫歐洲文明世界直接摘取重點的“政治、經濟、風土”眼光。而且從詩人早年的成長經歷而言,現代文明的印記在他身上留下的是累累的傷痕,而博覽群書的詩人早年熱衷的,是西方神秘主義大師們的作品。因此,詩人關注的是東方的文化和精神特征。在北京的街頭,他駐足幾個小時,看起來是在逛街,實際上街上的現實中最引起他的注意的,是迎風招展的寫有漢字的店招布幡,詩人就這么饒有興致地入定了。
并不是隨便哪里的天涯海角在詩人這里都有這樣的待遇,在游歷亞洲之前,青年米肖是個水手,去過巴拿馬,去過南美洲,并留下詩作《厄瓜多爾》,其中充滿厭倦、疲乏,用最準確的中國字來形容,是“殆”。在順亞馬遜河而下至出海口之后,詩人寫道:“亞馬遜河在哪?我看不見”。
而在印度和中國,詩人第一次發現,“在這個地球上還存在著符合人類本質的民族”,評論家在評論《一個野蠻人在亞洲》時說:“在南美洲,米肖所問的是:我在這兒干啥;在亞洲,他的問題是:他們在做什么。”

上世紀30年代北京店招上的漢字
米肖在中國一共呆了三四個月,路線歷經廣東、香港、澳門直至北京。“旅途中,我讀書、觀察、學習、思考、沉思,一無倦怠。即便在酷熱天,仍懷有一種寧靜。于道相合,融于一切。”他在北京的時間最長,沉下心來觀察老子的哲學在生活中的體現,就是中國人的思維言行方式,比如在描寫中國的社會動蕩時,不同于別的西方人:“農民、小販多次被搶,一而再,再而三。然而即使被搶了10次,他還是有耐心。生命和財產得不到保護,在西方人眼里,這種不安定感難以忍受,令人焦慮,中國人卻善于巧妙地周旋。”再者,百姓為了謀生,有著一些方寸之間施展智慧的技巧,這也沒能逃過米肖的眼睛:“挑夫、小販表現了平衡的智慧:一頭是冒著熱氣的鍋與爐,一頭是罐與碟,間或加一個入睡的小孩。這需要何等的靈巧啊!”“中國人是天生的能工巧匠,不巧做不了中國人。”“中國人即便吃飯也刻意追求相當的功夫,因為中國人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樣發明刀叉,只是使用刀叉不需要什么技巧,中國人不屑為之。”
并不是只有盲目無腦、為在本國嘩眾取寵的贊美,米肖也從長城看到了中國閉關自守的文化心態,詩人還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人的壓抑:“中國人好像從未松弛過。他們謹小慎微,處處設防,很可能會喪失笑的能力。由于長期的壓抑、隱藏、絞盡腦汁,中國人不再會笑,多么可怕的沉疴啊。”
在30年代的北京,米肖成為了京劇戲迷和梅蘭芳的粉絲。他看得相當認真,看出了門道:“沒聽過梅蘭芳唱戲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溫柔,那撕心的,令人銷魂的溫柔;也不知道什么是眼淚的滋味,什么是優雅精細的痛苦。”
和別的走馬觀花不同,中國之行對亨利?米肖的寫作生命終身有效。中國戲曲對米肖的詩學追求啟發最大,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戲曲特色,啟發了米肖旁敲側擊、少著文字但多得風流的“間接筆法”和“斷續寫作”,這正是中國藝術精神區別于西方藝術傳統的關鍵點:“西方人把什么都演出來了,一切都擺在臺上,應有盡有,無一欠缺,甚至透窗可見的外景;中國人只隨劇情需要,擺置可以象征平原、樹之類的東西,手搭涼棚,向遠一眺,便可生動展示遠景。他們能比我們表現更多的景物。”
從此,米肖終身練習道家精功,持之以恒,直至逝世。他離群索居,深居簡出,淡泊名利不領獎,不上媒體不拍照,甚至從不以為自己是什么詩人。他的住處四壁空空,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柜,一個書桌,幾把椅子,成為后世西方“斷舍離”模仿的范本。
一種文化應當恥于淪為噱頭,米肖從道家文化中尋求的是真功夫:“從前,我易怒。現在我踏上了一條新路:在桌上放上蘋果,然后,進入其中,何等安寧!這事看起來簡單,我卻摸索了20年。”
40年代中期,米肖開始在詩中說禪:“請讓學者遠離我,喝師說,他知識的棺木限制了他的理性。”這里所寫的喝師,是中國禪宗臨濟宗的棒喝。米肖升入禪宗新境界的重要途徑是解除對立,在悖論中覓求真理:“他冷于不冷,熱于不熱,不渴而飲,無水但并非無浪的海,沒有纖維素卻挺拔的樹。”
解除對立、融為一體的修為,對從小對西方文化感到幻滅的米肖來說是一種解脫,這種解脫不是徹底的逃避,而是幫助他重新擺正了自己在本位文化中的位置。在晚年的《米肖自略傳》中,米肖自論從東方悟道之后,不再是簡單的抗拒:“漸漸放棄抗拒歐洲文化之念,開始從中汲取養料。”這就如同米肖從東方喜好月亮所發現的精神,誠然,月亮代表著陰,如果你逃避灼目的太陽,自會在陰柔的月亮身上尋求到舒適的慰藉,但是月亮反射的,仍然是太陽發射出的光芒。
體認東方文化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六十年代,米肖開始借助致幻類藥物悟道和寫作,這是一段深不見底的神經漫游。幸而,米肖從未遠離中國文化,1971年,米肖為張龍顏著《中國書法》做了一篇長序,后來序文以單行本出版,名為《中國會意文字》。米肖對中國文字充滿了熱愛和遐想,因為西方拼音文字體系,文字符號和所指向的事物之間,即名和實之間,并無必然性等可以看見的視覺規律,這就讓詩人的母語寫作,似乎必須借助一雙無情的別人的雙手。米肖想要從中突破出來,雖然他并沒有系統學過中文,但他深入研究了中國文字名與實之間的親密關系,窺見了“字與物的原始神圣聯系”,領悟了“人與原始會晤的驚喜”。
米肖不僅在詩學上追求東方智慧,他本人還是一位畫家,更是在視覺形象表達上,直接采用大量東方元素,以期東西方藝術的融合。
米肖在法國主流文化圈中離群索居,但對中國人總是一無保留。初到法國的中國畫家趙無極,正是因為其八幅充滿水墨意象的石版畫引起了亨利?米肖的注意,并且為每一幅畫都配了一首詩,從而進入西方主流藝術圈的視野,重要的是以東方的背景和姿態:“米肖的話使我徹底安心,而且表達出了我模糊的感覺,只因為我曾經一心要擺脫中國傳統,所以并未在意這種感覺。與米肖的相遇,對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亨利·米肖著作與中國書法

亨利·米肖書籍
亨利?米肖作品選
杜青鋼譯
《迷惑》
我失去的女友,一直住在巴黎。行走,歡笑。我期待,遲早一天,她母親找到我說:“先生,不知道她怎么了。又沒啥異常現象,這個月,又瘦了4公斤。”
女友體重55公斤時,她母親再次找上門,擺出一幅居高臨下的樣子,好像我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稍后,又來找我,對我說:“先生,女兒只剩25公斤了,你能否幫點忙。”一個月后:“先生,只有24公斤了。事情很嚴重。”
我說:“24……公斤,等她只有19公斤時,再來吧!”
果然來了,聲稱14,其實有17公斤,據說,瘦到14公斤,女人的命就沒了,一著急,她提前來了。
“先生,她要死了。她對你就那么無足輕重?”
“太太,別怕。她不會消失的,我不能結束她的生命,即使只剩兩公斤,她還會活下去。”
《趨于寧靜》
拒不接受世界的人,不會在世界上建屋。冷而不知其冷,熱而不覺其熱。砍伐白樺,一無舉動,然而,樺樹一一倒下,他呢,領取相應的報酬,或者,遭到一頓痛打,有如一份無意義的饋贈,隨后,若無其事地離去。
喝水,并不因為渴,鉆進巖石而不感到疼痛。
腿讓卡車壓斷了,他神色依舊,仍然夢想和平、寧靜和平安,難以得到、更難保持的平安,想著平安。
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對海了如指掌。海就在他身下,無水的海,但并非無浪,一望無垠的浪。他熟悉河流,穿過他身體的河流,無水而寬廣,水面上,常常掀起猝不及防的巨浪。
無風的狂飆在他心中肆虐。屬于他的,惟有大地的寧靜,公路、車輛、羊群遍布全身。沒有纖維素卻堅硬挺拔的樹在他心中結出了一個碩大的苦果。
佇立一邊,赴約,每每只有他一人。從未握住別人的手,心咬誘餌,思念平安,纏人的混賬平安,他的平安,人常說的高于平安的平安。
《一個野蠻人在中國》(節選)
在北京我才認識了柳樹,不是垂柳,而是普通的柳樹,樹身略微傾側,典型的中國樹木。
柳樹總是有點像回避什么似的。它的枝葉捉摸無定,它的動作宛如駭浪進集。在它身上更多的是人們看不到的、它沒有顯示出來的東西。這是一種最不善于自我炫耀的樹。雖然它老在戰栗(可不像樺樹和白楊那樣生硬而惶惑不安的戰栗),但既不傲岸,也不阿附,它永遠劃行著,回蕩著,迎風獨立,仿佛游魚在湍急的河流中間翻騰、嬉戲。
柳樹一點一點陶冶你,每天早晨都在教育你。但是使你驚愕不止的是,經過一番巨大的搖撼之后,它歇息了,于是每當人們打開窗戶時,都不能不想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