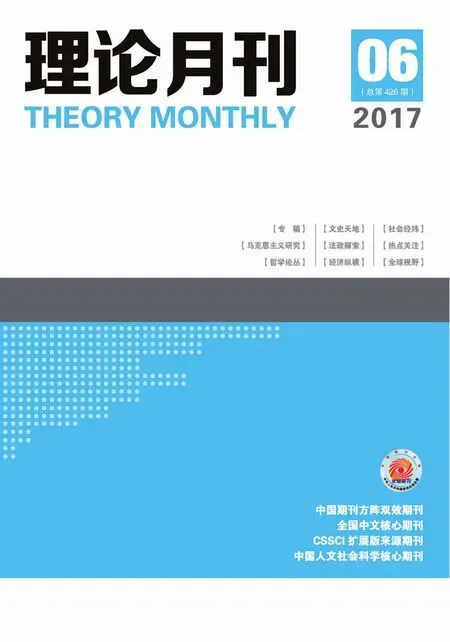海峽兩岸打擊電信詐騙司法協助研究
江勇
(臺灣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臺灣嘉義 62102)
海峽兩岸打擊電信詐騙司法協助研究
江勇
(臺灣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臺灣嘉義 62102)
海峽兩岸合作打擊電信詐騙犯罪始于2010年,剛開始收效明顯,然而近兩年來出現了反彈現象。面對海外電信詐騙日益猖獗、大陸受害人較多、被騙金額巨大等現實問題,從兩岸電信詐騙的發展脈絡及相關數據分析入手,合理研析了兩岸在處理電信詐騙犯罪方面的刑罰措施與既有的司法協助機制。針對兩岸在打擊電信方面存在的管轄權認定、刑責輕重、案件事實查證等方面的困境問題,本文試圖從尊重大陸地區的管轄權、實現證據收集和犯罪情資的溝通、加強罪贓的追繳與積極保障受害人的財產權益、落實大數據技術與體系的互動交流等方面提出司法協助層面的完善建議。
海峽兩岸;電信詐騙;司法協助
據統計,全國每年因網絡電信詐騙而蒙受的損失高達720億美金,且有逐年增長的趨勢,研究區域性的網絡電信詐騙成為熱點犯罪議題[1]。2016年4月,肯尼亞詐騙案完成臺灣詐騙嫌疑犯引渡至大陸的相關工作,同年12月,我國警方與西班牙警方又聯手破獲一起重大電信詐騙案。該案因其人數眾多,且嫌犯多為我國臺灣同胞、受害人多為我國大陸同胞而備受關注。雖然西班牙政府已經決定依據我國與西班牙簽署的司法協議將涉罪臺灣嫌疑犯引渡至大陸偵查、起訴,但這還是引起了兩岸司法機關的強烈關注,尤其是海峽兩岸合作打擊電信詐騙司法協助的議題。
1 兩岸電信詐騙的發展脈絡與相關數據分析
1.1 電信詐騙的發展脈絡
盡管世界范圍內打擊刑事犯罪的司法協作仍在加強,但這并未有效遏制近年來越演越烈的跨境電信詐騙,其發展勢頭迅猛。電信詐騙系指犯罪分子以網絡、電話及簡訊等方式,捏造虛假信息并以此設置騙局,從而實現對受害人的遠程式、非接觸式詐騙,其目的在于誘使受害人轉賬或打款。目前,海峽兩岸的電信詐騙主要還是以臺灣居民詐騙大陸居民為主,其具體詐騙地可能在臺灣亦可能在海外。電信詐騙最早發端于臺灣,早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前后,當時較為流行的方式就是“金光黨”,即詐騙犯將假黃金、假首飾置于路邊,等人撿拾后,提出只要現金不要黃金的分贓方案以實現詐騙財物的目的。隨著科技的發展,網絡電信詐騙開始逐步發展,假裝熟人、冒充親人、假冒檢警及設置釣魚網站等方式層出不窮[2]。隨著島內對詐騙的容忍程度越來越低,詐騙活動生存的土壤也越來越少,這種容忍包括民眾的容忍度與觀感和由此而來的警方打擊力度。于是乎,新的詐騙方式與模式也逐漸興起[3]。
首先,海外詐騙開始流行,為了規避島內警方的打擊,行騙者開始選擇將基站的建設放在海外,以降低犯罪的成本與風險。其次,團伙化、集團化詐騙越演越烈。隨著詐騙手段越來越復雜、內部分工越來越明確,團伙化、集團化的詐騙隨處可見。僅西班牙警方的一次行動就逮捕了200多人,而且詐騙集團多以包下整棟別墅的形式開始詐騙并偽裝自己的蹤跡。再次,打擊難度越來越高。打擊電信詐騙犯罪首先要弄清犯罪集團的組織結構,然后對“金主”等核心成員一網打盡。可是實踐操作中,“金主”往往隱身幕后,即便打掉一個窩點,“金主”還是可以很快地重新組建詐騙團隊。最后,手段越來越高明,從當初的接觸式詐騙逐漸演變成非接觸式的詐騙。常見的模式是:“金主”將基站建在海外,并雇傭一批人在海外從事詐騙大陸人的活動,“金主”同時還會收集大陸居民的信息以備詐騙和辦理“人頭卡”之用,等詐騙完成后,“金主”便會找一些“車手”(多為臺灣地區的國小、國中的學生)在臺灣各地自動取款機取現,整個詐騙過程與被害人無直接接觸且很難追蹤[4]。
1.2 兩岸電信詐騙的部分數據與分析
通過對臺灣法務部門每年發布的統計數據進行整合,制作了2011年至2015年的臺灣地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電信詐欺恐嚇案件統計表(表1),之所以談及恐嚇,是因為在電信詐騙過程中常會伴隨著恐嚇當事人的行為。

表1:臺灣地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電信詐欺恐嚇案件統計表(2011-2015年)
2010年1月1日起,臺灣警方與浙江警方聯合破獲數起電信詐騙案,簡稱“1011”專案[5];2010年8月10日,臺灣警方與福建警方又聯合破獲多起電信詐騙案,簡稱“0810”專案;2011年4月期間,大陸警方聯合臺灣警方在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國開啟聯合打擊詐騙行動,簡稱“0310”專案。據臺灣刑事警察局統計,2010年“1011”專案及“0810”專案實施后,次年臺灣地區新收詐騙案件數下降了45%,2011年“0310”專案實施后,次年案件量又下降了26%,與表一數據相呼應。2013年之后,兩岸聯合打擊詐騙活動的專案逐漸減少,于是2014年的詐騙案件數出現回升,2015年已達到1萬多件。從起訴率看,在詐騙事實基本存在的情況下,2011-2014年的起訴率不足五成,2015年較前幾年起訴率略有提高,約為五成一。從定罪率看,作出有罪判決的比例為九成五左右。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6起典型電信詐騙案件時指出:我國大陸地區2015年電信詐騙立案數為59萬件,損失金額達到220億人民幣,增長速度為20-30%。另據統計,2013年至今,全國千萬元以上的電信詐騙案件為94件,百萬元以上案件數為2085件,其犯罪模式呈現出集團化、專業化與跨區域化。此外,從詐騙類型看,主要有賬戶不安全、中獎、重金求子、包裹有毒、收到法院傳票、提供彩票中獎號碼及提供退稅與補貼等7種類型。從表1可見,2013年至2015年,臺灣地區新收案件數的年增長率也介于20%-30%,這與大陸地區電信詐騙案件的增長速度相吻合。
2 海峽兩岸打擊電信詐騙司法協助機制之探討
2.1 海峽兩岸處理電信詐騙的刑責比較
不可否認,兩岸在法律制度的理念、設計與實現領域仍存在一定的差異,厘清這些差異是開展兩岸司法協助的必要前提。從所涉罪名的角度看,電信詐騙可能因其行為較為復雜而涉及多項罪名。其很可能會因電信作案或者轉移賬款需要而觸犯《刑法》第177條所規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詐騙行為本身觸犯《刑法》第266條所規定的“詐騙罪”。從目前的釋法動向看,兩高將出臺關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以及擾亂無線電管理秩序犯罪的相關司法解釋。臺灣地區《刑法》第三十二章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了詐欺罪。從量刑角度看,大陸地區不管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還是“詐騙罪”,其刑期長短均與犯罪情節相關,最重可至無期徒刑。而臺灣地區的“詐欺罪”的刑罰相對較輕,其三百三十九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三百三十九(四)條規定,“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因特網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可見,在假冒政府官員詐騙、三人以上共同詐騙及利用網絡與媒體向公眾詐騙時所面臨的刑責可長達7年有期徒刑,其他情形的詐騙只會面臨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據統計,臺灣地區詐欺犯的實刑一般在6個月至2年不等。以此觀之,臺灣地區電信詐騙呈現周而復始、杜而不絕的情況便不難理解了。
2.2 海峽兩岸處理電信詐騙的司法協助機制
早在2009年,海協會會長陳云林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就共同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以下簡稱《互助協議》),該《互助協議》也成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完善司法互助機制的重要文件。從基本內容看,《互助協議》共計五章二十四條,內容涵蓋總則、共同打擊犯罪、司法互助、請求程序及附則。其中,總則就兩岸的合作事項、業務交流學習與聯系主體作出了規定。共同打擊犯罪篇章之第四節規定,“雙方同意著重打擊下列犯罪:(一)……;(二)侵占、背信、詐騙、洗錢、偽造或變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三)……;”[6]可見,電信詐騙屬于兩岸司法協助機制體系里的犯罪行為,亦昭示著兩岸就電信詐騙犯罪存在可以進行司法協助的基礎與可能[7]。
從臺灣法務部門的網站上還可以看到以下文件:《海峽兩岸重要咨詢通報及通知作業要點》《海峽兩岸犯罪情資交換作業要點》《海峽兩岸送達文書作業要點》《海峽兩岸緝捕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及《海峽兩岸調查取證作業要點》等。由此可見,兩岸在重要資訊互通、情資交換、文書送達、人員緝捕與遣返及調查取證領域存在著程式的運作規范。
3 海峽兩岸在打擊電信詐騙方面存在的問題
3.1 臺灣地區較輕的刑責“弱化”了大陸的司法權威
通過比較海峽兩岸的刑罰,不難發現,臺灣地區對電信詐騙犯的處罰較大陸地區要輕許多。以臺灣史上最大的詐騙案江永吉案為例(涉案資金約10億新臺幣),經過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合力打掉了這個流竄于兩地的電信詐騙犯罪團伙,其主犯江永吉在臺灣被抓、曾煥杰即“軍師”和其他人員在大陸被抓。經審理認定,主犯江永吉涉嫌詐騙案101件、恐嚇案2件,其在臺灣被判處6年4個月有期徒刑,目前處于假釋中;而曾煥杰在大陸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余幾名從犯均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刑罰。這樣的刑責差異顯然是對大陸司法權威的弱化。抓了放,放了抓,這種躲貓貓的游戲致使詐騙犯越抓越多。2016年4月,一則新聞轟動了兩岸,20名從馬來西亞遣返回臺灣的詐騙犯在桃園機場被無罪釋放,令人寒心。臺灣的減刑、假釋及易科罰金等制度使得原本就不是很長的刑期變得更短甚至不需要入監服刑。此外,臺灣地區法律還規定,“犯罪行為在海外的,最低本刑在3年以下的不追訴”。而大陸卻是另一番景象,2016年12月20日,最高法等三部門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再度明確,“利用電信網絡技術手段實施詐騙,詐騙公私財物價值3000元以上的可判刑,詐騙公私財物價值50萬元以上的,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3.2 臺灣地區辦案部門消極的心態為電信詐騙提供了土壤
詐騙犯越抓越多、手段越來越高明已經成為臺灣地區辦案警察對電信詐騙案件的普遍認識。在詐騙人在海外、受騙人在大陸、資金流回臺灣的情形下,辦案部門辦案的積極性也會大大降低。究其原因有三:首先,偵辦時間較長且空間跨度較大,這樣投入的人力、物力及財力較以往偵辦島內詐騙案件要多。其次,考慮到定罪量刑需要完整的證據鏈,受害人因在大陸且較為分散而很難確定,這樣定罪量刑之證據鏈可能不夠完整,從而起訴率不高。最后,跨境電信詐騙在臺灣地區一定程度上有穩定社會的作用。筆者一同學在臺灣刑事警察部門從事詐騙案件偵辦工作。據其口述,臺中地區以前是臺灣黑社會勢力較為猖獗的地區,社會治安環境不好,隨著跨境電信詐騙的興起,部分黑社會勢力從事了詐騙活動,所以社會治安快速轉好。其部門領導亦多次強調,打擊跨境電信詐騙不需要投入過多的精力,在經濟低迷的時期,這筆不義之財也算是一種收入。可見臺灣地區辦案部門的消極心態為電信詐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3.3 案件事實認定比較困難
大陸和臺灣同屬于大陸法系,但證據的證明標準還是存在些許差異。大陸地區《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并強調“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偏向于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臺灣地區刑事證據的證明則恪守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標準,即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于確信自由判斷。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規定。在實踐操作中,證明標準的些許不同并未改變證據應具有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及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從犯罪的構成要件看,不管是四要件還是三要件,入罪時均應當要求有明確的犯罪主體、被害人等基本要素,由于被害人在大陸且較為分散,實現案件的一一對應變得極為困難。不僅定罪存在困難,且量刑也存在障礙。一般認為犯罪數額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刑期的長短,詐騙行為因受害群體廣泛而無法一一確認,這樣總會有受害人無法得到賠償,反之,總有犯罪數額無法得到認定,上述原因也直接造成了2016年被馬來西亞遣送回臺的20名詐騙犯在機場直接被釋放的結果。
3.4 詐騙集團組織嚴密,難于“一網打盡”
組織機構嚴密、人員分工明確、“金主”幕后指揮已然成為目前電信詐騙集團的主要特征。組織機構嚴密指的是詐騙集團具有嚴密的組織網絡,往往會高薪誘導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加入,一旦進入詐騙集團,就會有較為嚴密的組織框架。人員分工明確是指在詐騙組織內部,每個人所從事的詐騙工作是固定的,收集個人資料與信息、話務、網絡偽裝、基站建設及車手等工作均有專人負責,崗位人員之間的流動性極少且人員之間亦相互陌生。“金主”往往不直接參與具體詐騙,事實上,“金主”在組建好詐騙集團后就會退居幕后,而在組建詐騙集團時,對該詐騙集團進行打擊是很困難的。一是因為發現的機制能力有限,二是因為沒有犯罪事實,即便抓獲也很難定罪量刑。對目前已經被打擊的電信詐騙案件進行合理分析后,我們發現,在詐騙集團被搗毀后,其會迅速“復活”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真正的“金主”沒有落網,這也是關系到贓款能否順利追回的重要因素。
4 海峽兩岸打擊電信詐騙司法協助的完善
4.1 尊重大陸地區對跨境電信詐騙案件的管轄權
以西班牙詐騙案為例,我國刑法的管轄權堅持屬地管轄為主,保護、屬人及普遍管轄為輔的原則。而屬地原則強調的是犯罪行為地與結果地,雖然臺灣同胞詐騙大陸同胞的行為發生在他國,但其行為的結果地在大陸,基于此,大陸地區對臺灣犯罪嫌疑人在海外詐騙大陸同胞的案件具有天然、正當且合理的管轄權,應當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大陸地區對此類跨境詐騙具有管轄權不僅有國內法的有力依據,也符合國際法的一般原則和中西之間相關司法文件的規定[8]。中國和西班牙可分別依據國際法的動機犯罪地原則(the subjective territorial principle)與目標犯罪地原則(the objective territorial principle)享有管轄權,一般實務上會先以犯罪結果發生地也就是目標犯罪地為優先,在國際法的慣例中,臺灣地區所主張的“屬人原則”不僅沒有法理上的支持論據,也是有違政治的偏頗想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2005年簽訂)第2條可引渡罪名及第4條可拒絕引渡理由的規定,此次詐騙案屬于可引渡范圍且西班牙可依據該案件已經或者準備進入刑事訴訟程序而拒絕引渡。值得慶幸的是,西班牙政府在充分考慮被害人的人權后作出了同意引渡的決定。事實上,此類臺灣犯罪嫌疑人在海外詐騙大陸同胞案件的管轄權爭議均類似于此案,可比照之,故大陸地區對此類詐騙案的管轄權理當得到肯定與尊重。
4.2 兩岸應在證據收集和犯罪情資的溝通上加強合作
面對破案壓力較大及證據收集難度艱巨的現實問題,為保障兩岸的人民的財產權益,應當加大證據收集及犯罪情資溝通的力度。首先,凈化政治文化,緩和溝通環境。兩岸人民的福祉是兩岸聯合打擊犯罪的最終目的,臺灣方面應當認識到合作是開啟兩岸未來的鑰匙,2010-2012年兩岸聯合打擊電信詐騙行動直接導致詐騙案件減少的事實就是明證。其次,加強證據的收集力度。根據《互助協議》第二章關于共同打擊犯罪之合作范圍的規定,詐騙、背信等經濟犯罪屬于兩岸共同打擊的范疇。《互助協議》第三章調查取證的規定則更為詳細,應當嚴格落實之,以實現對涉罪人員的有效打擊。最后,加強犯罪情資的溝通工作。面對分工日益明確的團伙化、集團化的詐騙模式,對犯罪信息的準確掌握是案件處理的關鍵;面對跨區域性的電信詐騙,僅依據片段化的信息即從受害人或者加害人一方的角度對詐騙行為予以打擊是遠遠不夠的,此時就需要加強犯罪情資的溝通。據臺灣地區法務部門的統計,2009年6月25日至2017年1月31日,兩岸共提請情資交換6281次,回應2667次。在利用情資的基礎之上,兩岸共同偵辦案件134件8476人,其中詐欺案件88起6904人,案件占比近七成,人數占比約八成。可見,充分的情資溝通有利于兩岸間共同打擊犯罪的實現。
4.3 加強罪贓的移交追繳、積極保障受害人的財產權益
《互助協議》第9條規定,“雙方同意在不違反已方規定的范圍內,就犯罪所得移交或變價移交事宜予以協助”。臺灣方面自從2014年4月首次向大陸被害人返還被查扣贓款以來,截至2015年8月,累計返還贓款僅為新臺幣102萬余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而同期大陸地區通過最高人民法院返還臺方的涉案資金為新臺幣1200萬余元。與每年數額巨大的詐騙損失相比,25萬元人民幣真是杯水車薪,可見臺灣方面在查扣犯罪所得方面的司法協作顯得無力。目前,兩岸之間的贓款依其被害款項比例返還查扣之詐騙所得,因此,筆者建議要進一步完善刑事沒收規則,加大懲處力度,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失[9]。此外,還有一種路徑值得探討,即民事司法沒收制度(judicial civil forfeiture)。2013年,臺灣檢方成功破獲了一起數額巨大的詐騙案,涉案資金約為80億新臺幣,其中有60億左右的新臺幣被轉移到香港匯豐銀行。據主辦此案的主任檢察官也是筆者的任課老師介紹,當時臺灣地區已經作出了正式的刑事判決并向香港政府申請凍結、轉移60億贓款。最終因港臺司法溝通不暢,香港政府依據臺灣的刑事判決作出了民事沒收判決,此案例對制度層面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4.4 加強大數據技術與體系的互動與交流
大數據監測已成為兩岸預防電信詐騙的有效手段。大數據(big data)系指對所有數據進行收集并運用新的模式進行處理,從而實現具有決策力、洞察力的海量信息資產,其具有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低價值密度)、Veracity(真實性)等5大特點,簡稱“5V”。2016年,中國工商銀行運用大數據技術對詐騙信息(風險客戶、賬號等)進行篩查、統計與整合,成功攔截了11萬筆電信詐騙匯款。北京市警方還將大數據技術與LBS定位技術相結合,成功實現對流動假基站的打擊并降低假基站詐騙案發案率八成。臺灣高雄左營警方也同樣利用大數據技術對車手取錢的超商進行統計分析,成功抓獲4名詐騙車手。此外,民眾宣導、媒體報道、防詐騙信息的定期發布等方式也成為兩岸應對電信詐騙之共通路徑。鑒于幕后“金主”的隱蔽性問題,兩岸之間的司法協助還應當側重于聯合辦案等多方面。事實上,加強大數據技術與體系的交流與互動不僅能在一定層面上促進辦案效率的提高,還能有效地降低電信詐騙的發案率,這種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應當是對被騙后無法求償問題的最有利的應對方式。
電信詐騙案件已經嚴重侵害了兩岸人民的合法權益與同胞感情,電信詐騙集團的“走向世界”也給兩岸合作打擊電信詐騙犯罪徒增了不少難度。不可否認,電信詐騙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這種不勞而獲的犯罪行為應當被堅決予以打擊。基于此,兩岸應當從預防和打擊兩個維度開展司法協助活動,前者強調的是對詐騙手段、犯罪情資及社會輿情等相關信息的溝通與交換;后者強調的內容更為廣泛,包括調查取證、聯合打擊、文書交換、判決執行及贓款追繳等諸多事項。此外,兩岸協助辦理電信詐騙案件的經驗還可以運用到兩岸毒品走私、偽劣藥品等犯罪領域的打擊中去。
[1]MAHUYA GHOSH.Telecoms Fraud[J].Computer Fraud&Security,2010(7).
[2]李修安.兩岸跨境犯罪之治理:以電信詐欺為例[J].犯罪學期刊,2016(2).
[3]林佳蓉.網絡詐欺案例類型,法律適用與犯罪防治之道[J].科技法律透析,2011(8).
[4]受騙百萬,半小時內就在臺灣被取現[N].新華社每日電訊,2013-01-27(3).
[5]章光明,從全球治理觀點論兩岸共同打擊電信詐欺犯罪[J].展望與探索,2010(10).
[6]宣炳昭,高珊琪.海峽兩岸刑事司法合作之現狀與發展[J].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011(5).
[7]薛少林.論兩岸刑事司法協助機制[J].社會科學,2011(11).
[8]DAVID HELD,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J].Global Governance,1999(5).
[9]陳澤憲,周維明.追逃追贓與刑事司法協助體系構建[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
責任編輯 伍靜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6.029
D914.35
A
1004-0544(2017)06-0160-05
江勇(1990-),男,江蘇鹽城人,臺灣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