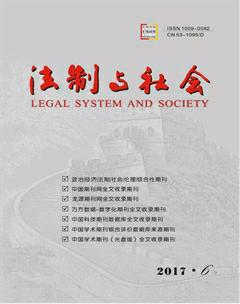論搶劫罪中暴力的程度
摘 要 本文闡述了對搶劫罪中的暴力進行限制的必要性,界定了搶劫罪中“暴力”的判斷標準,并對搶劫罪中“暴力”的上、下限作出探討。認為搶劫罪中的“暴力”上限僅包括故意殺人而把過失排除在外,提出搶劫罪中“暴力”的下限只要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即可,且并不要求事實上抑制住被害人的反抗。
關鍵詞 搶劫罪 暴力 程度
基金項目:此項目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2017年度院基本科研費項目,項目名稱:“暴力犯罪的司法治理與平安河南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7E16。
作者簡介:李浩東,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方向:中國刑法。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309
一、問題的提出
搶劫罪是刑法常見的一個罪名,而“暴力”是搶劫罪常用的手段,對于搶劫罪暴力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利于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本文就暴力的程度作出相應的梳理和探討,以求有益于司法實踐。
(一)搶劫罪中暴力的程度是否需要限制學說之梳理
關于搶劫罪“暴力”是否需要程度的限制,我國刑法學界至今仍存在較大爭議,目前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學者們各有各的見解。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類:
第一類:主張“暴力”須達到一定程度。但是對程度的要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可以依據“暴力”的程度對暴力進行細分:1.搶劫罪“暴力”的限度要達到“足以危及被害人身體健康或者生命安全且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2.搶劫罪“暴力”的限度要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但允許事實上并沒有壓制住被害人的反抗,同時不必須要求危及被害人的生命安全。3.要求達到“實際壓制住被害人反抗”的效果和程度。
第二類:不要求“暴力”必須達到一定程度。此種觀點認為,被害人存在著性別、體格、年齡、智力、性格等方面的差異,同樣的“力”施加給不同的對象,其作用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被害人個體上的差異化將會導致實際生活中對“暴力”認定上的困難。因此,沒有必要設置“暴力”的限度,因其沒有任何實踐意義。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們還有如下理由,其一,“暴力”的程度缺少法律依據和具體標準,實踐中,搶劫使用暴力與否還須憑法官的主觀判斷。其二,規定“暴力”的程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他們認為,行為人只要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圖,客觀實施了強取財物的行為,一般就能夠認為成立搶劫罪,在實踐中是否運用暴力、暴力的程度如何,可以在所不問。其三,行為人只要開始對被害人實施“暴力”無論“暴力”是否能在事實上抑制住被害人的反抗,只要其意圖通過實施“暴力”的方式壓制或排除被害人的反抗、非法占有財物,搶劫罪即宣告成立。
(二)搶劫罪中“暴力”程度是否需要限制之厘定
正如任何事物都是有界限的,搶劫罪中“暴力”的程度也理應有一定的限制。理由如下:其一,搶劫罪“暴力”的程度影響案件定性。如果不對搶劫罪“暴力”設定上限和下限的限制,那么就會造成搶劫罪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認定上的難題,因為此時暴力僅僅是一個名詞,任何方式的暴力都將具有同質性,這時罪與非罪全依賴于對暴力概念的理解,此罪與彼罪由于沒有程度的限制而變得難以區分。其二,搶劫罪“暴力”的程度影響案件量刑。我國刑法分則對各罪的處罰依據在于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搶劫罪中“暴力”的程度則能從客觀上反映出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暴力”有了程度的限制能更好的區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主觀惡性,通過其造成的危害結果可以判斷出其社會危害性,在司法實踐中可以做到罪行相適應。
基于以上兩方面的理由,我們認為應當對搶劫罪“暴力”的程度進行限制。那么,如果對其進行限制,具體的限定標準如何,筆者認為,如果把搶劫罪中的“暴力”程度的限定在:“足以(但不要求事實上)壓制被害人的反抗,但不要求危害被害人安全的限度”會比較科學。之所以這樣限定,是因為這樣一來易于司法人員對具體搶劫罪中“暴力”進行判斷和應用,二來有利于保護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打擊刑事犯罪。
二、搶劫罪中暴力程度判斷標準的界定
(一)搶劫罪中暴力程度判斷標準之爭
如上所述,我們了解到搶劫罪中的暴力需要限制,但對暴力進行限制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判斷搶劫罪中暴力的程度。當前刑法學界在搶劫罪“暴力”程度的判斷標準歷來是存在爭議的,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學說中:其一,主觀說。此說基于行為人的主觀狀態來判斷“暴力”的程度。只要行為人從其自身出發,主觀上認為已經壓制住了被害人的反抗,則宣告成立搶劫罪。其二,客觀說。持這種學說的學者們認為暴力程度的大小應以普通人按照其正常認知做出判斷為準。也就是以一般普通人在其正常狀態下認定達到“足以抑制其反抗”的程度作為客觀評判的標準。其三,折中說。該說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應當按照被害人所能抗拒的程度酌定。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確能使常人不能抗拒或不敢抗拒,但由于被害人的特殊體格、特殊身份(如武警、特警、拳擊教練)等而并不因此畏懼或喪失抵抗力,則該行為不能認定為“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反之,雖然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不足以使人不能抗拒,但被害人由于種種原因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則仍可認定為該當本罪的行為。
(二)搶劫罪中暴力程度判斷標準的界定
主觀說可能導致主客觀不相一致的結果,因此不可取,具體錯誤表現在以下兩種情況中:1.如果行為人認為其所采取的輕微“暴力”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根據主觀說的觀點,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在這種情形下被害人還有反抗的空間,不符合搶劫罪“暴力”取財的行為特征,這種行為其實并不能構成搶劫罪,被害人之所以給付財物并不是因為恐懼,多是因為憐憫或其他因素而主動交付財物,筆者認為,這種情形下將其定為“敲詐勒索”比較合理。2.行為人認為其所采取的“暴力”還未達到“抑制住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而實際上,被害人已經陷入了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境地,根據主觀說,這種情況并不能構成搶劫罪,但這個結論顯然是不合理的。客觀說是日本法院判例和刑法理論的通說,它以足以抑制普通人的反抗為標準,比較具有合理性。因為“暴力”行為不因行為人主觀意志的改變而改變,它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具有科學性;折中說還需要結合案件實際情況等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其中仍然摻雜主觀說的因素,因而還是有部分缺陷的,被害人個體的不同使本來就不統一的判斷標準變得更加復雜,在司法實踐中也難恰如其分的把握。
筆者基本贊同客觀說的觀點,但是筆者認為,“普通人”的概念還是太過抽象,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對其進行把握,所以筆者的看法是:對“暴力”程度判斷標準的認定,可以立足于客觀說,在此基礎上可以參照唐朝①和借鑒域外的法律②,綜合考慮如下幾個因素:1.暴力的表現形式。即是否使用刀斧棍棒等工具。2.被害人、行為人的客觀情況。如年齡、身高、人數、體格、性別等。3.作案環境。如在夜晚還是白天、是在城市還是荒郊,當時天氣溫度如何等。如果綜合考慮上述情況得出暴力行為達到足以抑制住社會“普通人”進行反抗的唯一結論,則構成搶劫罪中的“暴力”。
三 搶劫罪中“暴力”程度的限定
(一)搶劫罪中 “暴力”的上限
搶劫罪中“暴力”的上限達到何種程度?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只是規定了“搶劫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犯情形。關于“暴力”的上限,歷來理論爭議不斷,焦點在于故意殺人是否能夠納入搶劫罪“暴力”的范疇。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它明確指出,在搶劫過程中,行為人為排除被害人反抗而實施的故意殺人行為可以被納入搶劫罪“暴力”的范疇。此批復出臺后,引發了更多學者對搶劫罪中“暴力”上限的討論。
筆者認為,搶劫罪暴力的上限可以包括殺人行為,且這里的殺人行為僅指故意殺人。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個:
第一,搶劫罪侵害的客體為雙重客體,即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人身權利包括人身自由權、生命權、健康權等與人身密切相關的各種權利,其中生命是人最寶貴的財富,沒有了生命,一切將無從談起,殺人行為之所以作為最嚴重的犯罪行為被懲處,也是因為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搶劫罪的犯罪客體中既然包括人身權利,理應包括對生命的侵犯,況且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上來看,我國法律并沒有把殺人行為排除在“暴力”外,所以,搶劫罪的上限理應包括殺人行為,至于殺人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筆者認為,凡是“暴力”都是有意而為之,過失構不成刑法上的“暴力”,原因在于暴力的行使都受很強的犯意支配,只有故意為之才可能實行超限,刑法之所以規制“暴力”是因為實施它的罪犯主觀惡性極其嚴重,所以搶劫罪中使用暴力致人死亡僅限于故意而不包括過失;至于搶劫罪中的故意,有的學者明確指出,“搶劫罪中的致人死亡可以包含過失和間接故意致人死亡,但直接故意致人死亡不能包括在內”,筆者認為,這也是有誤的,因為至今還沒有發現哪一種犯罪只能由間接故意構成,而把明確排除直接故意。
第二,就犯罪構成要件而言,如果把“為劫財而殺人”的案件定性為故意殺人罪一罪,那么劫取財物的目的行為就沒有得到評價,案件性質也得不到正確的反映;而如果以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對其進行數罪并罰,就使方法行為和目的行為相分離,忽視了“暴力”行為在其中所起的連接作用,并且,在搶劫犯意持續期間殺人的情形下,如果把故意殺人作為單獨罪名獨立出來,則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而如果將之定性為搶劫罪一罪,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把殺人行為作為搶劫罪中的手段行為予以評價,把殺人行為蘊含于“暴力”的內涵之中,那么此時,殺人行為所反映的是“暴力”行為的內容和外在表現,這完全符合搶劫罪犯罪構成的要求。
第三,從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刑罰設置來看,搶劫罪中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故意殺人罪的法定最高刑也為死刑,在最高刑方面均設置了死刑,說明立法者對搶劫罪設定刑罰之時已經考慮到了為搶劫而故意殺人的情形,所以把搶劫罪的法定最高刑設置為死刑,此外,搶劫罪較故意殺人罪在刑罰設置上增加了罰金和沒收財產的兩種刑罰方式,目的在于矯正犯罪分子不勞而獲的心理,對行為人的處罰更加全面,不會出現放縱不法分子的情況。
(二)搶劫罪中 “暴力”的下限
搶劫罪“暴力”的下限同搶劫罪中“暴力”的上限一樣,也是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刑法也沒有給出明確的規定,所以在實際操作中也顯得非常困難和復雜,如:有人對“暴力”作了“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與健康”的限制,就把那些雖作用于他人人身,排除了其反抗但無危及其生命健康的行為,像未造成傷害的毆打、捆綁、禁足、摟抱等行為無所適從;又如:有人對其作出了“使人不能抗拒、不敢抗拒或無法抗拒”的標準限制,實際上等于承認若被害人對“暴力”侵害進行了抗拒,該“暴力”就不再屬于搶劫罪中的“暴力”手段了,本是犯罪未遂的情況也不復存在了,這無疑是放縱了犯罪,不利于當前打擊搶劫罪的實際需要。有學者認為,只要行為人基于搶劫的故意實施了“暴力”行為,搶劫罪即告成立。那么,是否應當對搶劫罪中“暴力”的下限進行設定呢?
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從搶劫罪的概念上講:搶劫是通過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的行為方式搶劫公私財物的行為。從中可以得知搶劫的過程實際上是通過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壓制被害人的反抗從而“劫取公私財物”犯罪意圖的過程,其中劫取財物是目的,暴力等僅僅只是手段,手段為目的而服務。研究搶劫罪中的“暴力”,關鍵之處就在于研究“暴力”的實施與劫取財物的內在機理。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求通過“暴力”或其他手段來取得財物,但要想達成“取得財物”這個目標,壓制或排除被害人反抗的“力”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對劫取財物的“力”沒有最低要求,那么它就有可能為脅迫所取代,因為脅迫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也常以“暴力脅迫”的形式出現;再者,設置“暴力”的下限是罪名區別的內在要求,搶劫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都涉及到“暴力”和取財,其重要區別就在于“暴力”程度的差異。如果“暴力”在程度上沒有最低限制,則上述罪名將很容易混淆,司法運用中也容易出現混亂和錯誤,此罪和彼罪將難以區分,從而有可能造成案件適用的不公。而且,如果“暴力”沒有下限,則會在心理上刺激犯罪人對被害人實施更加殘忍的“暴力”,因為更加殘忍的“暴力”只要不觸犯“致死”這一暴力程度的最高限度往往會使犯罪目的更好更快的實現,這將使刑法對被害人的保護流于空泛,不利于打擊搶劫犯罪,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所以,為了防止上述情況的發生,對搶劫罪“暴力”設定下限則顯得尤其重要。最低限度的設置應當是一個綜合考慮的結果,應給予人民財產和生命安全的最全面而科學地保護。由于搶劫罪中行使“暴力”是為了取財,那么壓制住被害人的反抗就顯得已足夠,但并不一定在事實上壓制住被害人的反抗,之所以這么設計,一是因為犯罪個體主客觀情況的復雜性,另一個原因在于,法律保護的不是純事實,而是對法益的保護。另外,暴力的下限,也不必要求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為如果要求了,則會使為了劫取財物而未對被害人生命健康安全的“摟抱”行為等變得無所適從。綜合專家學者的觀點,結合具體現實情況,筆者認為“足以(但不要求事實上)壓制被害人的反抗,但不要求危害被害人生命健康安全”,是一個相對合理的下限標準。
注釋:
①唐律《賊盜律》規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千,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又如《斗訟律》:“諸斗毆者,笞四十,傷及以它物毆人者,杖六十。”可見唐律中對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規定的十分詳細,一般按“暴力”的程度、作用的工具等具體情節來確定處罰方法。
②日本知名教授西田典之指出:“作為搶劫罪手段的暴力、脅迫,必須達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判斷是否達到了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必須綜合考慮行為人以及被害人的性別、年齡、犯罪行為狀況、有無兇器等具體情況。”
參考文獻:
[1]周道鸞、張軍.刑法罪名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2]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
[3]高銘喧、馬克昌.新編中國刑法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4]趙秉志.刑法新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
[5]高銘喧.刑法學專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