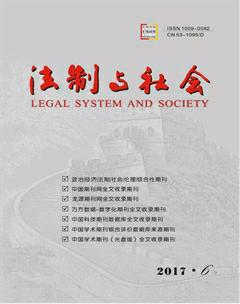評陳雁著《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
摘 要 陳雁教授的《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是一部資料詳實、論證嚴謹的著作,每章以具體的人物或事件作為切入點,探討事件背后的社會背景,并闡釋性別與戰爭之間的聯系與隱喻。在問題意識與創新之處上,該書沒有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女性戰爭史的寫作套路,而是從性別的角度對民族和民族主義展開新的分析。在理論方法上,運用了社會性別理論,展現上海女性在戰爭中記憶與體驗。在資料上,使用檔案、報刊、圖片、專著等多種資料,其中口述資料的運用是一亮點。戰爭并沒讓女性走開,女性也是戰爭中的一份子,從性別的角度出發去反思其行為,可以提供一個重新關照生命的契機。當今我們安寧生活來之不易,應當珍惜。
關鍵詞 戰爭 性別 女性
作者簡介:武小力,河北大學歷史學院2014級歷史學專業,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416
人們常說“戰爭讓女性走開”,但是戰爭真的讓女性走開嗎?古往今來,“烽火戲諸侯”、“特洛伊戰爭”、“沖冠一怒為紅顏”等等諸多歷史典故里,女性往往被視為戰爭的導火索,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在“他者”眼里并不受歡迎。但是,戰爭對于女性自己而言,提供了一個戰爭的體驗記憶、與“民族國家”對質關聯的平臺。復旦大學歷史系陳雁教授的著作《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上海女性為例,探究戰爭與婦女解放所包含的復雜歷史脈絡與多樣的社會面向,重新審視戰爭中的女性,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和典范意義。本文試圖從基本內容、問題意識與創新之處、理論方法、資料運用等方面對《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 1945》作一評述,最后闡述該書對自己的啟發與思考。
一、基本內容
《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一書,是陳雁教授在其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戰爭與性別”結項成果的基礎上修改而成,于2014年5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并被列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近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書系”之一。其作者現為復旦—密歇根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中方所長、國際婦女史學會(IFRWH)理事。
全書總共分為十一章節,分別是導論、“‘筑長城:從<孟姜女>到雀戰”、“<女聲>(1932)、<女聲>(1942)、<女聲>(1945)”、“職業女性的困境:由上海郵政局不招女性職員和拒用已婚女職員談起”、“‘灰鈿之爭:張愛玲與平襟亞的性別之戰”、“‘秋海棠與梅蘭芳:困守上海的男人”、“‘傾城之戀與‘抗戰夫人”、“姑侄的抗戰:養蔭榆與楊絳”、“女漢奸”、“口述、性別與上海抗戰史”、結語。每章都是以具體人物或事件作為切入點,以小見大,探討事件背后的上海乃至社會的大背景,并闡釋性別與戰爭之間的聯系與隱喻。
二、問題意識與創新之處
“學術研究首先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也就是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課題。但能否找到這樣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取決于學者對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判斷”。《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是關于上海的戰爭與性別的著作,作者通過對相關研究梳理表明,近些年來關于上海史的研究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的熱點之一,但是研究的上限往往到1937年戛然而止,而對上海抗日戰爭時的研究下限也常常到“八一三”淞滬戰爭結束而止。
作者在書中談到,抗戰時期婦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著重女性對抗日戰爭貢獻的探討,秉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宏大敘事。相關的研究有丁為平教授的《中國婦女抗戰史研究1937-1945》,還有一些各地、各級婦聯完成的成果有《抗日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概況》、《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婦女運動》、《魯中南婦女運動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婦女革命史》、《抗日烽火中的搖籃——紀念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文選》、《烽火巾幗》等。另一領域是關于戰爭中女性受害者的問題,尤其是慰安婦的問題。這些著作對戰爭中女性受害者進行了扎實嚴謹的研究,推動了抗戰時期婦女史研究的不斷深化,但是所得出的仍然是控訴式的結論,這難免給戰爭中的女性涂抹了單一的灰色面相,不利于讀者看到女性本身在戰爭中的所扮演的角色,這一類的研究有蘇智良教授的《慰安婦研究》、《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經盛鴻教授的《慰安婦血鑄的史實——對南京侵華日軍慰安所的調查》等。
以上列舉的著作豐富了戰爭與性別的研究成果。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之上,近些年來性別與戰爭的研究在不斷地拓展,而且在選題和視野上都有了一定的深化,對戰爭中的鄉村婦女、婚姻關系、性別關系、婦女形象、女性與大眾文化、民族國家與女性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現一批新的成果。比如:張志永教授的《邊緣到主流:抗戰時期華北農村婦女特殊亞群體的演化》、叢小平教授的《左潤訴王銀鎖:20世紀40年代陜甘寧邊區的婦女、婚姻與國家建構》、侯杰教授的《媒體·性別·抗戰動員——以20世紀30年代<世界日報>副刊<婦女界>為中心》、宋少鵬教授的《民族國家觀念的構建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系》等。
陳雁教授對于上述的研究成果予以了反思。傳統的戰爭史屬于政治史的范疇,聚焦于外交、軍事,但是將性別、娛樂、婚姻、消費、家庭等排除在戰爭領域之外,像鄭蘋如或王佳芝這一類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她們無法完全置入民族國家抗日戰爭英雄史敘事。陳雁教授重新審視了這種簡單化、臉譜化、標簽化的戰爭中的社會性別關系,力圖避免以往抗戰史寫作中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敘事套路,讓女性自己說話,努力展現上海女性在戰爭中記憶與體驗,同時關注抗戰時期上海普通女性的生活,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對民族和民族主義展開新的分析與理解,這是《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的問題意識與創新之處所在。
三、理論方法
貫穿《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全書的是社會性別的理論研究方法。作者稱,“筆者一直把本書的寫作看作一次女權主義史學研究的實踐……從性別視角出發,將性別關系與國家、民族等范疇緊密結合,對抗戰時期的中國社會重新解讀的過程,的確舉步維艱,但斯科特吹響的‘不僅僅是在撰寫新的婦女史,也是在撰寫全新的歷史的戰斗號角,卻又格外地鼓舞人心,激勵筆者不自量力地完成本書的寫作。”
關于社會性別的理論,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將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切入,亦不乏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羅久蓉先生的《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之下的忠奸之辨》也運用了社會性別理論。社會性別強調性別的社會性構建,與人的自然性別相區別。美國歷史學家瓊·W·斯科特(Joan W. Scott)給社會性別下的定義是:基于可見的社會性別差異之上的社會關系的構成要素,是表示權力關系的一種方式。一些社會性別理論著作指出,性別差異是由文化機制來構建的,而傳統價值觀念中的性別觀念、性別等級等因素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機制,深刻地形塑著人們對性別的認識。
由此,社會性別理論是評定男女社會地位、職業角色、行為規范的一重要指標。通常來說,女性在社會、歷史、文化中居于從屬地位。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婦女是被社會構建成的他者的人,婦女在男女性別權利中處于劣勢地位,這是父權制下的產物。以《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為例,陳雁教授對上海女性在戰爭中的位置與身份進行了探討,她們的身份變化而尷尬。《申報》的文章使用“英雌”一詞來形容那時上海的太太們,雖然沒有流傳至今,但是所表述的正是現代國家民族解放發展的訴求,也體現了當時女性解放訴求,同時隱喻了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張力。
斯科特在《社會性別:一種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里指出,國家政治本身便是一種社會性別化的概念,它的權力運行、擁有權威等都建立在排斥女性的前提上。在這一點上,《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第九章“女漢奸”可以看到戰爭對女性議題的影響。作者論述了戰后國家審判“女漢奸”的相關議題,這一章節主要涉及到的人物有紅色“漢奸”關露、“女漢奸”李青萍以及對陳公博的情人莫國康的審判。值得注意的是,關露背負著黨的使命“潛入76號魔窟”,但是在戰后受到社會的非議;李青萍追求藝術人生,在抗戰期間多次舉行畫展,如此表現與大眾抗戰的形勢不容,在戰后也遭到了審判與逮捕。但是換做男性,在戰爭年代他們這樣的做法也會受到審判與懷疑,不同的是,對女性的審判往往加上了道德倫理上的抨擊。“女性的容貌在這種時候最容易被拿來攻擊,容貌的敗壞似乎也象征著女人身體、貞節被玷污”,與之相關的桃色新聞被肆意地書寫,她們在審判過程中的一舉一動、表情容貌被無限地放大,群眾的評議也就更加苛刻。
“戰爭給女性對大限度的自由與解放,但在政治變動頻仍的中國,這種自由與解放可能隨時被收回,甚至轉眼化為鉗制與束縛,任何性別議題都有被泛政治化的可能。”這是羅久蓉先生在《戰爭與婦女:從李青萍漢奸案看抗戰前后的兩性關系》里強調的內容之一。性別議題政治化也許是戰爭年代的普遍現象,男性女性皆是如此。陳雁教授的《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并未限于考察戰爭中上海的女性,第六章“‘秋海棠與梅蘭芳:困守上海的男人”便是對淪陷在上海的男性進行了探討。“秋海棠”講述了中國男性追求陽剛氣質的艱難旅程,當時風靡上海;梅蘭芳“蓄須明志”,成為男性藝人抗戰的象征。這些都表現了戰爭年代社會性別議題的政治化現象,彰顯了時人對性別與國家的認同。
用社會性別的理論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社會上的性別現象。傳統的社會性別視角多集中于研究婚姻、家庭、纏足等與婦女相關的領域,當涉及戰爭、國族、忠奸問題等宏大議題時,它們被認為是屬于男性的歷史,往往較少提及女性,“戰爭讓女性走開”或許是一種不自覺的現象。但是,當我們以社會性別的視角重新審視譬如戰爭對社會的影響時,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發現,《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便是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視角,無疑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
四、資料運用
《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運用了多種資料,參考了多種文獻,它們大致可分為報刊資料、中文論著、外文論著。此外,書中還運用了口述資料,可以說,這是該書在資料運用上的一個亮點。
口述歷史的研究在近現代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們展示了生命的個體體驗,同時也在回憶與述說中勾勒出時代的背景脈絡。作為事件的親歷的個體,他們所口述的歷史具有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抗戰勝利如今已有七十二周年,當年抗戰的親歷者皆已非常年長,因此對戰爭口述資料的整理具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和意義上的重要性。可喜的是,近些年來無論是學術界、一般性的組織,還是教育性機構,對抗日戰爭口述歷史的資料整理與訪談越來越予以重視。遺憾的是,對于抗戰女性口述資料的整理研究仍然不多,有待進一步深入發展。在學術研究上,《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提到,有關女性與戰爭的成果引用最多的口述資料是李小江主編的《讓女性自己說話:親歷戰爭》,也有一些零散的口述成果見載于各地的文史資料中。
第十章“口述、性別與上海抗戰史”著重采用了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寫作的計劃設計中完成了對潘咸芳、刁作伊、黃新珍、張明江、翁保勛、楊獨青、程雨民、史玉泉這幾位上海人的深度訪談。在文章的最后,陳雁教授對訪談口述資料的運用和處理進行了反思:“在口述歷史實踐中,對于訪談者重構歷史的野心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我們必須承認,‘歷史記載中有太多的靜默無聲,有太多的無法解決的含糊和曖昧,因此我們對能動性事例的闡釋最終仍會受到根本的制約。”但是也因此,口述的實踐也就更有挑戰力和吸引力。這也是作者“嘗試構建普通人的上海抗戰史、社會性別化的上海抗戰史的努力之一”。
口述歷史夾雜著個人記憶,同時也在形塑著集體記憶、地方性的歷史記憶。運用口述資料,可以展現歷史中多采而鮮活的聲音,能夠打破單一面相的“官史”和精英史。因此,在近現代史的研究中應重視對這一資料的整理和運用。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年代的久遠,再加上口述具有主觀的能動性,口述者在述說過程中難免夾雜著個人情感、偏見喜好,也許記憶上會出現偏差,因此在具體運用中應當仔細甄別與考察。但是,口述的主觀性以及口述者著重提及也許時間上發生錯亂的事件這一現象,從側面也可以看出這一事件對當時人所產生的影響。從這點來看,陳雁教授在《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里針對口述者對抗戰的記憶出現“耐人尋味的時間分叉”問題,指出“這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口述者耄耋之年的記憶混亂,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抗日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集體記憶的營建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抗戰對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民族主義的激發總用至今仍然深刻。”
除上述的文本資料、口述資料之外,作者在有些頁面還插入了很多圖片資料,它們多選自上海抗戰時期的報紙,比如廣告、商標、人物、漫畫以及老照片。這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至于枯燥無味,圖片與文字相結合,相得益彰,知識性與畫面感并存。
五、啟發與思考
通過以上對《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基本內容、問題意識與創新之處、理論方法、資料運用的梳理,可以看出,陳雁教授不僅對1932-1945年抗戰時期的上海大眾女性的生活狀況進行了生動細致的描述,剖析當時女性生活的多元面相,而且也向我們展現了戰爭對男性的影響,對于研究戰爭對男性、女性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是一部資料翔實、論證嚴謹、富有創見的著作,讀后收獲頗豐。筆者依昔記得,買來《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后打開包裝,首先看到的是書背后的封面文字,第一句寫著“人們常說‘戰爭讓女性走開”,當時就記住了這句話。同時也帶著“戰爭讓女性走開?”這個疑問,對全書進行了閱讀。讀畢,深深吸了一口氣,對于這個疑問也有了答案:戰爭并沒有讓女性走開,女性也是戰爭中的一份子,她們不應該處于失語的地位。
之所以有這樣的閱讀體驗,一方面,筆者潛意識里并不贊同“戰爭讓女性走開”這句話;另一方面,陳雁教授將社會性別理論作為全書論述的理論框架,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戰爭并不僅僅關乎男性,在它的陰霾之下還有廣大的女性,她們不應成為失語的主體。從性別的角度出發來考察1932-1945年戰爭期間的上海女性,探究她們與周邊的關系,正視她們的處境,可以展現出多元的戰爭籠罩下的社會面相。
這樣的手法,在《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的前言里有所提及:“從女性書寫的敘事方式可以形成一個由邊緣向中心滲透的意義網絡,它們的各個細節對于整體的觀點呈現具有關鍵作用,有助于以更寬的角度掌握事情多元復雜的本質。面對錯綜的倫理問題、社會問題,站在個人的角度,將生命書寫置于更大的敘述脈絡,審視自我與社會、記憶與歷史、個體與群體的復雜關系,脫離主觀對立的敘事框架,故而可以容納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不同位置、不同立場發聲,從而提供一個重新關照生命的契機。”比如:戰爭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松動,給女性職業發展提供了契機,但是“戰時上海郵政局不招女職員和拒用已婚女職員事件”而引發的討論,展示出職業女性挑戰傳統性別角色引發男性世界的焦慮。
筆者不禁想象,在那戰爭動亂的年代,炮彈連綿,滿目是斷壁殘垣,不知在仲秋嚴冬時節,多少人會在落日余暉的那一刻,黯生悲涼,百般無奈?戰爭帶給人們的是痛苦的想象,對于經歷者來說更是悲慘的回憶。今日的幸福安寧生活與當時的動蕩不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應當愛之、惜之、敬之!
參考文獻:
[1]陳雁.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2013.
[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鄭克魯譯.第二性.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白玫.社會性別理論初探.內蒙古大學2006年5月碩士學位論文.
[5]李向平、魏揚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徐志民.《性別與戰爭:上海1932-1945》出版.抗日戰爭研究.2014(2).
[7]李金錚.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對話:王笛《茶館》之方法論.近代史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