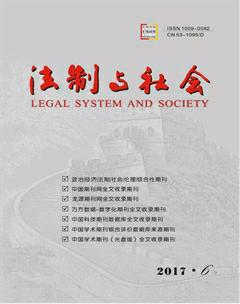環境刑法立法模式的探析
摘 要 本文從我國的環境刑法立法模式入手,分析我國目前在刑法典中專設一節規制環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存在的不足,并通過比較各國的立法模式,結合我國的現實國情,從而探析出新的適合我國的環境刑法立法模式。
關鍵詞 環境刑法 立法模式 法典化 附屬刑法 特別刑法
作者簡介:白蓓蓓,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418
一、概念
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是指規范環境犯罪條款在法律中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的立法模式受不同的立法目的、思想和技術的影響,并對懲治環境犯罪的法律效果產生影響。
二、我國環境刑事立法模式
我國環境刑事立法經歷了“行政法制裁-刑法典制裁”的立法沿革。在新中國成立初,對環保問題,僅規定在一些行政法規中,對環境犯罪并無明確規定,直到1979年刑法典的出臺,但這時刑法典也只規定了一些關于環境犯罪的條款,還分布在刑法典的各章節中,并無專門罪名規定。這一時期懲治環境犯罪的法律依據主要是環保法規中刑事處罰條款,在這些法規的法律責任條款中,通常在確定污染或破壞環境行為的民事和行政責任后,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是所謂的環境犯罪的“附屬刑法”。附屬刑法中對環境行為的刑事罰則條款規定的比較簡單籠統,缺乏獨立罪刑規定,只規定“依照”1979年刑法的條款定罪量刑,而1979年刑法本身就缺乏具體的環境犯罪規定,因而這些附屬刑法條款適用的效果很差。除此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88年還頒布一部單行刑法,專門規制野生動物的環境犯罪。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我國的環境刑法立法模式是:特別刑法規定環境犯罪的罪名、罪狀和法定刑,普通刑法和附屬刑法單純規定刑事處罰條款。
為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應對層出不窮的新環境犯罪問題及環保需要,我國于1997年對刑法典進行了全面修改,在新刑法典中設專節對環境犯罪問題進行規制,即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1997年刑法典對環境犯罪的規定,從體例上和內容上,都較之前的刑法典有很大進步。這突出了我國對環保的重視。與此同時,我國還陸續出臺一些環保法規,不斷完善我國環保法律體系,在這些法律中,繼續沿用附屬刑法的形式,追究環境犯罪的刑事責任。因此,我國當前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是:普通刑法典規定環境犯罪的罪名、罪狀和法定刑,附屬刑法單純規定刑事處罰條款。
目前,我國這種在刑法典中以專節規定環境犯罪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增強了刑法典的系統性和穩定性。但隨著新環境問題出現,環境犯罪也越加猖獗,所造成的環境損害也漸趨嚴重,也凸顯出現在這種設專節規定環境犯罪的立法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如:(1)未明確環境犯罪的客體是環境法益;(2)降低了環境刑法的位階,易造成人們對環保的不重視;(3)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理念未能受重視。鑒于這些弊端,當前這種立法模式已難以適應環境犯罪規制的現實需要,因此,有必要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獨立出來,在吸收和借鑒其他國家先進經驗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實踐,建立適合我國的立法模式。
三、世界主要的幾種立法模式
各國的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分為以下三種:
(一)法典化模式
法典化的立法模式是指主要將環境犯罪規定在刑法典中,再以其他立法形式為輔助。主要的代表國家是德國。
德國的環境刑事立法沿革和我國的大致相同,都經歷了從行政法的制裁演化成刑法典的制裁。1980年前,德國刑法典中對于環境犯罪的規定寥寥無幾,僅在極個別條款中規定了環保問題,這一時期德國對于環保主要依靠附屬刑法的規定,但即使行政法規中對于某些危害環境的行為予以定罪處罰,卻并未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隨著環境問題的加重以及環保意識的提高,1980年,德國對于刑法典進行了修改,其中對環境犯罪問題中的水、空氣、垃圾、噪音以及放射性物質等做了統一的專章規定,即刑法分則第28章“環境污染的犯罪 ”。自此德國從依靠附屬刑法懲治環境犯罪的時代進入到了刑法典懲治環境犯罪的法典化時代。1994年德國還修改了《基本法》,增加了對于自然環境的保護,并使環境法益在憲法層面上得到確立。
此外,因為新的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刑法典又具有穩定性,在處理新的問題時有所不足,德國還在附屬刑法中作出了補充性的規定。除德國之外,印度和前蘇聯等國家也采取這種模式。
(二)特別環境刑法模式
特別環境刑法模式是指在將主要的環境犯罪規定在一部特別刑法中,并輔以其他形式。主要代表國家是日本,日本環保問題始于公害。1950年,日本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與此伴隨的是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污染對人類造成的公害病影響范圍極其廣大。1960年后,日本開始注重對環境問題的治理,尤為注重對環境犯罪問題的立法。
首先,日本修正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典在此次修正之前并未有專門的環境犯罪的規定,此次修正也主要是針對日本已發生或正發生的環境問題做了規制,雖反映了環保的力度,但罪名規定具有針對性同時也具備了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日本采取了特別環境刑法這一世界先例性的措施。1970年日本頒布了《公害罪法》,這部法律開創了特別環境刑法的先河,雖僅有7個條文,但涵蓋實體和程序兩部分規定。這部法律可以說是日本懲治環境犯罪的首要的也是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但令人奇怪的是這部法律從頒布后所適用的案例僅有四個。這主要是因為通過對其司法適用的實踐考察,學者發現其適用效果遠不如其立法產生的價值和影響力,究其原因是:(1)立法觀念更新的不徹底,對破壞環境本身的犯罪行為并未規制;(2)日本最高法院對該法中的“排放”一詞進行了司法解釋,即“排放”必須是“作為業務活動的一環進行”,從而縮小了該法的適用范圍,這一限制性解釋遭到眾多批評。因此,特別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必須依靠令人信服的理論發展,才能在法理和實踐上獲得普遍接受。
最后,為了彌補刑法典和特別環境刑法在規制環境犯罪問題上的不足,日本還在環保行政法規中進行了補充規定。但日本顯然還需要對其立法模式進行新的修改。
(三)附屬刑法立法模式
附屬環境刑法模式是指將主要的環境犯罪規定各個環保行政法規中,并輔以其他形式。代表國家是我國臺灣地區和英美法系國家。
我國臺灣地區將環境犯罪主要規定在“行政法規”中,這主要是考慮到環境犯罪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且規定的較為詳盡,可直接引用。但這種分散式的規定,欠缺以“刑法”的強制威懾力來預防環境問題。同時,也未將環境法益作為客體保護,即未對污染和破壞環境本身的行為加以規定,而是等到這一行為損害了受法律保護的法益(人身或財產)時,才依據相關的法律規定加以規制。而且,這樣也破壞“刑法”的完整性。臺灣地區目前已意識到這一模式的弊端,因此正積極尋求新的模式對環境犯罪問題進行規制。1999年臺灣地區首次在“刑法修正案”規定了有關環境犯罪的專門性條款,則臺灣地區有希望在未來通過在“刑法”中設置專章的方式規定環境犯罪。
英美法系國家也采用這一模式,對于環境犯罪主要規制在各個環保行政法中,這主要是因為英美法系遵循判例法的傳統,沒有統一刑法典。以英國為例,英國對于環保問題起初只有法條的零散規定,后由于發生煙霧事件后,開始重視環保問題,主要體現在化零為整,將零散的規定組成環境行政法體系。英國是較早進行環境立法的國家之一,早在1821年,英國就有包含防治大氣污染的行政法規。自1950年倫敦煙霧事件發生后,英國又陸續頒布了一些環境立法,1982年還頒布了刑法,增加了環境犯罪的刑事制裁,但環境刑法還是附屬于環境行政法,功能較弱。1990年英國頒布了新的環保法,將零散的環保行政法規進行整合,涵蓋環境所有的要素,還對環境犯罪規制了相應的刑事制裁措施,是一部綜合性的法律,達到了保護環境法益的目的。
四、我國環境刑法立法模式的選擇
由上文可知,世界各國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法典化、特別刑法和附屬刑法三種。
特別刑法立法模式將環境犯罪的實體與程序規定在一部法律中,體現了對環保問題的重視,一部法律既能定罪量刑,又能提供訴訟依據,最主要是能突破刑法的約束,也能為更新理論觀念提供空間和機會。但一方面,我國已有《刑事訴訟法》,不需要依靠特別刑法提供程序規定;另一方面,我國在刑法典中已設專節規定環境犯罪,若再進行環境特別刑法的立法,不僅立法水平達不到,而且還會破壞我國刑法典的完整性。所以,我國目前還不適合特別刑法的立法模式。
附屬刑法立法模式是根據環境問題的實際情況進行規制,遇到新的問題可以及時應對,因此對比刑法典穩定而言,附屬刑法更靈活。但這卻不利于犯罪理論的系統性,也容易使環境犯罪問題泛化,之所以適合英美法系國家而不是很適合我國臺灣地區,主要就是英美法系國家是不成文法國家,沒有完整的刑法典,因此只能依靠行政法規加以規制。雖然我國也在環境行政法規中規定了一些刑事責任條款,但這些條款也只是籠統的規定了一些原則性條款,具體操作還是需要刑法典的規制,因此就我國目前立法現狀而言并不適合這種立法模式。
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對環境犯罪設專章進行統一規定,能夠明確使行為人感受到國家對環境的保護力度以及對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當前我國環境問題非常嚴峻,環境犯罪也層出不窮,并且,我國目前所采用的就是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因此相比較而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國現今的國情和立法現狀。不過,我國的立法模式還需要結合實踐作出相應修改,環境犯罪所侵犯的客體是環境法益,是單獨客體,我國目前將環境犯罪規定在第六章中,顯然是對環境犯罪客體不明確的結果,也降低了環境犯罪的位階,不符我國重視環保的國情,顯然不合適。因此需將環境犯罪脫離出來,進行專章規定,與其他犯罪客體并列,提高環境犯罪的位階,這樣不僅有利于刑事立法的成熟完善,也有利于刑法分則體系的精細度,與此同時,也會提升人們對環境犯罪的關注度,加強人們的環保意識,使環境刑法的威懾作用增強,更有利于保障環境法益。
環境犯罪所造成的損害是長期且嚴重,甚至是不可恢復的,當世界沒有干凈的水、沒有可呼吸的空氣、沒有無污染的土壤時,那人類的存在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環境問題造成的代價是昂貴的,并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也會有不同的特點,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盡管有利于統一環境犯罪,但在適應新問題時便有些滯后。因此,我國除采取以專章規定環境犯罪的法典化的立法形式外,還應采取一些分散立法。從法律的沿革史看,正是將零散的規定整合進刑法典的趨勢,只是環境問題有其特殊性,它會伴隨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問題,并且沒有一部法律可囊括所有規定,刑法典也如此,所以需要環境行政法和特別刑法來填補空白。因此,我國應在環保法規中相應的對“附屬刑法”條款加以具體規定來彌補刑法典的不足,條件成熟時,還可制定單行環境刑法。
綜上所述,我國的環境刑事立法模式應采取以“專章”規定的法典化模式,并由其他形式的立法彌補刑法典規制不足的地方。
參考文獻: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2]王明遠、趙明.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探討.中國環境法治.2008(1).
[3]趙秉志、王秀梅、杜澎.環境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
[4]徐平.環境刑法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5]徐久生,等譯.德國刑法典.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6][日]丸山雅夫.環境刑法.法律家.2004(1270).
[7][日]中山研一.公害犯罪:企業責任與刑事責任//中山研一,等編.現代刑法講座(第5卷).成文堂.1982.
[8][日]西原春夫.犯罪各論.成文堂.1991.
[9]邱聰智.公害法原理.輔仁大學法學叢書專論類.1984.
[10]葉俊榮.大量環境刑事立法.環境政策與法律.臺灣月旦出版公司.1993.
[11]鄭昆山.臺灣環境刑法立法之回顧與展望.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二).元照出版.2001.
[12]王秀梅.臺灣環境刑法與環境犯罪研究.境外刑事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39).
[13]王秀梅.英美法系國家環境刑法與環境犯罪探究.政法論壇.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