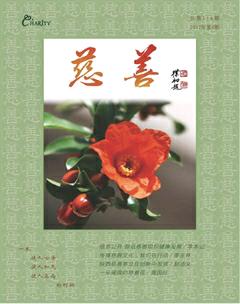慈心善語
2017-07-14 15:03:17
慈善
2017年4期
關鍵詞:節約
東晉時期的高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在《大智度論》中言簡意賅地闡明了慈悲之善,不僅僅給人快樂,還要把人從苦難中拔救出來。他說:
“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苦。”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出臺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李本公談及中華慈善總會在《慈善法》出臺后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時說:
“《慈善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慈善事業將進入法治時代,即依法運行、依法管理、依法監督,這是我們企盼已久的大事,會大大有利于慈善環境的改善和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對慈善組織來說,《慈善法》既是約束又是保護,更是督促。”
創作出版過《喬廠長上任記》《蛇神》《農民帝國》等著作的著名作家蔣子龍,一次在總結、分析國際上富豪慈善家的共同特點后說:
“節約是一種精神,一種態度。反過來,一個自信,一個奮發的民族,必然是勤儉節約的。奢侈是頹廢,今朝有酒今朝醉,原因和腐敗有關,跟社會的風氣有關,跟引導有關,跟媒體在追求豪華有關,現在再不談節約,就我們這點資源,我們這點錢,要是再這樣下去,實際上不是經濟損失多少,關鍵是我們丟了一種精神。看一個民族是不是奮發有為的,是不是有希望,有追求的,看他對物質的態度。”
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早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能、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經》哲學。他說,
中國的“立國之本在于比我們更寬厚、更慈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品牌研究(2023年6期)2023-03-01 06:51:18
品牌研究(2023年4期)2023-02-19 08:58:28
小學閱讀指南·低年級版(2020年11期)2020-11-16 07:00:53
作文評點報·低幼版(2019年42期)2019-12-30 01:40:57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8年10期)2018-10-27 05:46:08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8年17期)2018-09-10 02:39:46
小天使·二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5期)2018-06-29 08:47:04
資源節約與環保(2018年1期)2018-02-08 02:17:30
兒童繪本(2017年6期)2017-04-21 23:19:31
民生周刊(2015年9期)2015-05-06 02:2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