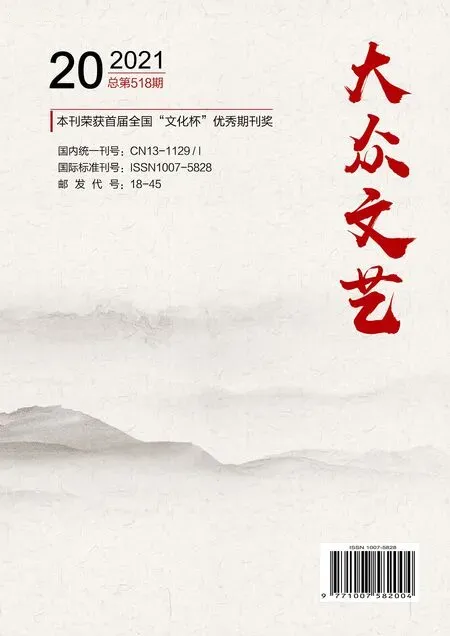當代北京朝鮮族畫家的現狀研究
——1990年代之后的美術
徐龍吉 (延邊大學美術學院 133002)
當代北京朝鮮族畫家的現狀研究
——1990年代之后的美術
徐龍吉 (延邊大學美術學院 133002)
從90年代初開始延邊與其它省市的朝鮮族畫家們陸續闖進北京。那些80年代興起的“人文”“理想”“新潮”等藝術潮流逐漸淡化,新的費解的當代藝術之變化,讓人既恍惚又驚喜。這種費解讓我們得到更多當代藝術的熏陶,也許這就是朝鮮族畫家在北京的生存環境。就執筆者而言,生存環境與藝術作品的關系形成他們作品的品味。因此,應該重視以下內容:1)從中心和邊緣的辯證關系分析當代朝鮮族畫家藝術作品;2)朝鮮族藝術家如何取得“自我認同”;3)如何理解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理解模式直接影響到詮釋藝術作品的方式;4)在當代語境之下,如何重構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作品。
民族傳統;非合理性;存在者
一、前言
隨著90年代市場經濟深化改革的熱潮,物質生活方式加速成長,北京的政治與文化環境對年輕人有極大的誘惑,許多朝鮮族年輕畫家闖進北京。他們大部分來自延邊以及東北三省,部分北京的大學畢業生留在北京、從外地進入中央美術學院進修直接留在北京、還有回國(韓國、日本)留學生。他們在這陌生的城市里為自己的藝術追求付出了代價。這使80年代以延邊為中心的中國朝鮮族畫家群逐漸轉到北京這個大城市。
1995年,以文成浩、崔憲基、金鳳石、樸哲奎(50、60年代出生)等年輕畫家組成的延邊畫院,首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畫展。 這對90年代中國朝鮮族畫家來說意義深遠,當時著名美術評論家水中天主持了開幕式,還有各種媒體的專訪。1994年崔憲基在中國美術館的個人展 、1993年樸春子的中國美術館的畫展都得到專家們的好評,確立了他們在北京的一席之地,并給予大批年輕朝鮮族畫家以極大的勇氣與鼓舞。這些畫家在北京這一競爭激烈的都市里拼搏掙扎,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夢想,艱苦卓絕而磨礪不止。
在當代美術大背景下,朝鮮族畫家從不同角度理解思考著繼承民族文化傳統,與此同時融合主流文化命脈,吸收國外先進的藝術思潮。在這種過程中他們逐漸確立著自己的藝術定位。今天反觀他們的作品有兩種傾向的創作模式,一是將民族傳統融入現代藝術形式,二是在當代藝術潮流之中不斷地更新自我觀念。
二、傳統與變異
李哲虎(1962吉林舒蘭)曾經堅持以朝鮮族民族傳統文化為創作源泉,后期他不斷擴展視野,在中西文化交匯中特別關注中國自身文化的價值,較深的研究“中國畫論”,將個人風格建立在中國文人畫精神之上。他的畫風精煉、簡潔、大方,有明確的構成,追求中國文人精神的內在深奧的境界。如“魂魄”“秋詞”等作品中尋找與中國文人精神氣質相符的新的創作形式。
樸春子(1963延吉)始終關注民族傳統,她擅長表現朝鮮族女性樸素、溫和、勤勞的生動形象。她在不斷探究本民族傳統的基礎上,表現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人物的生活狀態。她的作品以傳統工筆畫平面化的處理方法和統一而富于變化的色彩,達到畫面效果的簡單、極致,非常注重畫面的形式和材料的探索和運用。在《盛裝的新娘》中以對稱的構圖形式,統率畫面的紅色,亦莊亦諧,富有平面裝飾感,富于生命與活力,美感奇特。而這樣的色彩表達又特別適合表現少數民族人物樸素自然的人生觀,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總之這些畫家從不同角度擴展了他們的創作領域,就像德勒茲所描述的“塊莖”一樣在不同的“逃逸線”中實現自己的追求。他們從民族題材到現實生活、其它少數民族的文化生存狀態與歷史中研究中國畫論以及中國文人畫。在他們的心底里總有傳統民族整體性為根的文化情緒,在此基礎上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當代的文化命脈并擴展自己的藝術天地,形成了他們獨特的畫風。
三、觀念的膨脹
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有顯著的變化,一方面由于國內政治、文化傳統與現實的制約,加之當代國際前衛藝術的洗禮。“中國在社會轉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困惑與焦慮相互糾纏的異常豐富的資源,構成了中國前衛藝術的活躍與豐富多彩。”在不息藝術的左、右紛爭中,藝術家的精神和觀念真正產生出影響。這些前衛藝術的競爭中也有崔憲基、李松、劉鋒植等朝鮮族當代畫家。他們在以下領域中表現出各自對當代藝術的理解與思考。
(一)從架上到懸置
畫家崔憲基(1962延邊)從初期自由、單純、夢幻的《雪國》系列,到后來的《狂草》系列以及他的裝置藝術,表現出東方藝術哲學中最直接、最明確、深奧的精神內涵,在其中越來越強化了他對藝術的獨到見解。在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中,文本享有特權,它是開放的,具有含義的不確定性。崔憲基的創作中出現過的“6×9=96”等符號話語,是一種“反邏輯”的思維形式,且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當代與后現代主要特征之一。在崔憲基的“懸置”作品《肖像》中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攝影肖像與他自己和某位觀眾的肖像并列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我們的理論基礎”,“我與觀眾”曾經必須要對其頂禮膜拜,而崔憲基不無幽默地并置排列,不僅意味著一種民主意識的生成,也恰似反映出兩個時代之間的聯系,時序更迭的殘酷與荒誕,自我與歷史、社會與政治因素聯系起來把歷史與政治現實等問題給予文化上的評價。在西方有對神的否定,而中國則是對過去那些狂妄的政治迷信的質疑和否定。這一點上他是現時的一種行為美學。
(二)“反諷”的隱喻
在當代藝術中常出現“反邏輯”“反理性”“反諷”等主張與表現。李松(1965黑龍江穆棱市)與劉鋒植(1964哈爾濱)的作品中明顯的表露出這些精神內涵。李松的作品中那些超現實夢境般的“磚頭”“蠟燭”,馬、飛蛾、老虎不尋常、非合理性的組合,創造出意想不到的并置,表現藝術家自身心里的(宗教與神話)意思,發揮出自身的“力比多”的能量,接近“崇高”的一面。繪畫藝術這個概念的時候,它決定‘發生’的秘訣是靜態的那他本身。社會化是不可能的。繪畫作證,要做的就是那個事件或事件本身。”李松的藝術精準再現了對象極具體的細節,但沒有直接描寫什么的意義本身,可能標志著一種遠離意義,超越的尋求,而這種尋求正是同崇高相關,崇高已經在他的藝術創作中占有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呈現出來的那些虎,馬,石榴等形象體現了獸性的強力、暴力、戰爭、農業、人類流動中一位天然的同伴,是能量、力、美等中國古代文化的象征之一。也表明著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他所表現的奔馬在同燭光搏斗,不如說在同自我搏斗,更能激發出自我的崇高感;但也沒有哪種搏斗比自我搏斗更加荒誕不經,更能體現自我的虛無主義。
劉鋒植(1964哈爾濱)的理性、背離、毫無邏輯的那些表現主義特征,表現出一位隱藏的文化斗士,他那幽默可悲的形象中保持著他對當下清醒的文化使命與道義責任。他畫很多題材,其中對“天安門”的反復描寫引起人們的重視,關于《天安門系列》與其說“是一種對國家神話的蓄意顛覆,還不如說是一種典型的精神烏托邦的反面書寫;與其說這些畫是對某種不可貶損的族群意識的搗蛋式調侃,還不如說是一種唯美主義的詭謬表達,和藝術家心目中那種自我認定的自由理念的酣暢宣泄。……劉鋒植正是用他那種獨特的繪畫語言來從事這種破譯解讀的正是獲得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理性解讀。也只有通過這種理性的解讀,我們的民族才有可能恢復一種正常的心智與情態,使其生活的樣式走向一種真正的對稱和平衡,而不僅僅停留于一種表面上的‘光鮮’和口頭上的‘牛掰’。”作者用色極其大膽,對比也異常強烈。在那里攀爬各種內在的不可言傳的道不明的凄涼、蕭瑟、恐慌和沉寂之情,是一種還原主義的手法。顯然,作者想通過這種還原來呈示天安門一種更為隱蔽的本質;存在著消解權力空間與潛藏征服意識。帕克對崇高的含義是說 “因為無法捕捉到清晰的含義,產生了一種模糊感,繼而引發焦慮、恐懼或一種深奧的感覺。”在劉峰值的作品里體現的就是無法捕捉到的清晰。他絕對率性、絕對自由放開的表現痕跡且栩栩如生,神似形離的表現形式,表達了某種誠然是思想家也無法用語言來言說的深刻哲理。
(三)存在者的影子
德勒茲說〈同一身體給予感覺,有接受感覺,既是客體,又是主體。我作為觀眾只有進入畫中,到達感覺者和被感覺者的合一處,可以有所感覺。他主張感覺始終存在于意識本身存在之前。
金宇(1963內蒙)作品中那些被擠壓在玻璃的人群或者個體,樸光夑(1970延邊)作品中僅限制在一種圓圈里的個體的人也體現著像德勒茲的感覺邏輯的哲理。在金宇的作品中那些擠壓在玻璃層面上的人與人群,一種“存在”本身的話語,發掘了那種潛意識的夢幻般的超現實主義。按海德格的倫理來說它是通過現身、領會、言談等生存機制組建、構成或開展出來的。“它‘存在于世界’即世界給予我們得方式或者說之前我們存在于世界的存在方式那本身。”他的作品《觸點》系列在視覺上直接造成一種震撼的效果,表現消費文化背景下所呈現的一種失衡的精神狀態和對無可逃避的人性的理性思考。這種態度是在現代社會關系中所面臨的一種新的精神狀態,也是藝術家觸及到人的生存狀態的一種藝術化的自我寫照,也構成金宇特定的繪畫符號,也是一種“存在者”的角色與姿態,“存在”與這個世界。
做為70后的樸光夑從圓明園到宋莊畫家村同方力鈞等“玩世寫實主義”畫家們一起,創作出自己的游戲規則。對于“玩世現實主義”90年代初栗憲庭在《1989年后中國藝壇的后現代主義》中寫到“玩世現實主義的主題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末第三代藝術家群。因此在他們成長的社會和藝術的背景上,與前兩代藝術家發生了很大的差距。……無聊感不但是他們對自身生存狀態最真實的感覺,也是他們用以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徑。”樸光夑的作品大多采用圓形構圖,人物都在水中,或者是潛在水底,而且大量使用了粉紅色的色彩,很有視覺上的感染力。他所描繪的荷塘與以傳統文人畫作里的荷塘有著本質的不同。畫面人物表情各個怪誕不經,且不知何故還流著鼻血。所有這些更加促使畫面呈現出一種離奇、荒誕。樸光夑說“圓形構圖在我國傳統文人畫中是一個很常用的形式,……我想通過殘荷傳達的是一種像禪一樣空靈的境界與意境……我經常感覺我們這一代是一個比較多余、比較尷尬的一個群體,我們內心的體驗與當今社會的價值尺度是對不上號的,以至于我們時常會感到茫然和彷徨。”正是這種體會讓他通過那種常用的圓圈,一是借用傳統形式,二是預防外界思想的侵入,三是把水中的這個人物作為媒介去宣泄內心的不安。恰恰這就是傳達了他們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的生存體驗。
綜上所述,9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文化藝術大背景下的畫家采用各自的方式尋找與確立自己的藝術觀念。但有共同點是他們都相當于這個世界的直接的體驗者的角色,尊重自我體驗,不再停留在民族傳統的小圈子里,把自己放在世界當代藝術平臺與中國文化歷史、現實命脈來思考問題。感知到90年代之后文化認識過渡期的一個典型階段,是社會變化時文化失語的代表特征,是傳承脈絡的變異,做出了種種個人的心里表白。就是“它‘存在于世界’即世界給予我們的方式或者說之前我們存在于世界的存在方式那本身。”也就是朝鮮族畫家在北京生存狀態的具體體現。
四、結語
90年代之后北京的朝鮮族畫家們受過現代與后現代(當代)美術浪潮的洗禮、以及商品文化的沖擊,他們不再停留在那些80年代的狹義的民族情緒、傳統、地域文化的圈子內,并尋找自己的創作思路。他們的創作思維與形式,是多樣化、個人符號化的現代與后現代的理性思維接軌。于是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1.他們一直保持著民族整體性為根的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當代的文化命脈擴展自己的藝術天地。2.在當代藝術的思潮之下,從不同角度體現出這個世界的直接體驗者的角色,尊重自我體驗,脫離傳統的或者是反傳統思維形式的后現代理念。3.關注90年代之后文化認識過渡期的一個典型階段中的社會變化、文化失語的代表特征,是傳承脈絡的變異。折射出在當下這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和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社會時代背景中,民族、個人在某種強勢力量的擠壓下,做出的種種心理表白,他們重視本土當今的文化現實,盡力躲避傳統,更重視他們當下生存狀態下的文化情緒。
[1]韓版.李玄富譯.《知識分子的死亡》文藝出版社,1993.
[2]格雷厄姆.瓊斯.〈利奧塔眼中的藝術〉.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3.
[3]陳重權.韓國版(柱).《現代美學講義》.artbooks 2003.9.
[4]呂澎著.《中國當代美術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