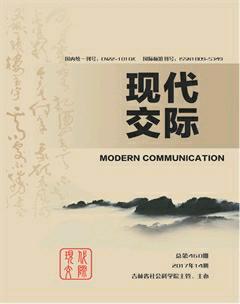從社會資本角度看玄學衰落的必然性
趙祉星+劉湘國??
摘要: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思潮,是在老莊思想基礎上建構的儒道兩家的極有意義的哲學嘗試,對后代影響深遠。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本文通過對魏晉時期典型人物是否擁有社會資本以及如何運用社會資本的分析來看玄學衰落的必然性。
關鍵詞:玄學衰落 社會資本 玄佛合流 魏晉名士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4-0178-03
一、玄學與玄學的發展
玄學①是魏晉時期流行的一種學問,意為“玄遠之學”,由漢末魏初的清議、清談轉化而來。湯用彤先生在《郭象與魏晉文學》中將玄學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即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時期(240-249)的玄學,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時期(255-262)的玄學,以裴頠、郭象為代表的元康時期(291年前后)的玄學,以張湛為代表的東晉時期(317年前后)的玄學。[1]
正始十年主要探討的是貴無論,當時的正始名士代表人物包括了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何晏是貴無派思想的創始人,王弼在當時影響最深。王弼所處時期為三國時期,身處曹魏。貴無論主張以無為本,以有為末,崇本息末。王弼注老莊時主要由用達體,在本體論層面探討哲學。
竹林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為竹林七賢,在本文中主要以嵇康為例。當時司馬昭以孝治天下,但是其選賢行為甚為荒唐,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從正始時期的玄學在政治層面的探索轉為精神層面,讓玄學生活化、審美化。竹林七賢率性純真、重養、蔑視禮法。玄學思想仍為貴無派,在思想上并無太大建樹。
元康時期,分為崇有和獨化兩派,《資治通鑒·崇有論》中說:“夫萬物之有生者,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為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名教”不過是根據社會正常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所以它是“合理”的,裴頠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風氣進行了批評。而郭象認為,事物之間的相互為因的功用,對于順應事物自身自己自足的生生化化沒有意義,所以只有每個事物“獨化”對其他事物才有意義。郭象通過獨化論說明了其對“貴無”思想的否定,同時提出了“內圣外王之道”。郭象強調游外以弘內。
東晉時期,《高僧傳》卷四《支遁傳》說道:“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于是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嘆服”。此事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佛學已經開始超越玄學。從張湛也可看出玄佛合流的趨勢,他為獲得更多的支持者,將神學納入其理論范疇,使理論具有某種神秘色彩。他沒有突破以“現世”逍遙為生命終極意義的玄學理論底線,他被作為最后一位有理論系統創建的玄學家載入史冊。在《天瑞篇注》中表明其觀點為冥內游外。
玄學興起于正始時期,竹林時期在思想上并無太大建樹,元康時期玄學發展再次興盛,東晉時期出現玄佛合流趨勢,玄學走向衰敗。從中也可看出各個時期代表人物其社會網絡在其玄學思想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社會資本對玄學發展的影響分析
本文采用邊燕杰教授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2]邊燕杰認為,社會資本基數主要由四個因素決定:網絡規模、網絡頂端、網差、網絡的構成。規模大的網絡比規模小的網絡擁有的關系、信息和人情橋梁較多;網頂高意味著網絡內擁有權力大、地位高、財富多、聲名顯赫的關系人多;網差大說明網絡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處于不同的職位,資源和影響是互補性的;網絡構成合理,則是指與資源豐富的社會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3]
表1 玄學各發展階段代表人物的社會資本測度
(一)正始時期
個人社會資本的多少決定思想擴展范圍的起點,玄學興盛之初,個人社會資本基數大,且網絡節點多,社會資本流動性強,所以通過個人社會資本的正確運用可以擴展到社會全體。
王弼的祖父是王粲②的弟弟王凱,母親是劉表的女兒。王弼家世顯赫。《王弼傳》記載了王弼與何晏的關于圣人有情無情的爭論③,記載說明王弼是有社會資本的,同時,他受何晏之邀,經常參加名士的清談④活動,在社會資本的運用層面,何晏及其他名士對其觀點的贊賞和傳播,網絡節點多,社會資本流動性強,使得“貴無論”從小網傳播到大網之中,發展興盛。此外,根據清談對象看出王弼的網絡規模大,網絡頂端為何晏⑤,同時,由于清談只涉及當時士人,所以網差較小,他與當時資源豐富的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社會資本構成合理,在以上社會資本的構成之中也可看到王弼的社會資本的基數大。從結果來看,王弼對社會資本的運用著實影響到了正始時期玄學的發展。
(二)竹林時期
竹林時期由于正、反兩種社會資本的沖撞造成了自以為正統思想者對逆反思想者的壓制和誅殺,強制統一口徑造成許多人避而不談思想,導致社會節點減少,社會資本流動中斷。而此時,不管社會資本基數如何龐大,也無法在全社會造成廣泛影響。
嵇康作為當時“逆反思潮”的代表,在被鐘會污蔑之后,為司馬昭所殺。可以看出持“正思潮”的統治者對“反思潮”鎮壓方式的極端,這也逼迫嵇康必須使用社會資本去防止受其牽連的人受到傷害。嵇康的網絡規模較小,主要集中在竹林七賢之中,網絡頂端為同是竹林七賢的山濤⑥,網差較小,網絡構成不合理。社會資本基數小,加之社會資本的流動性差,網絡節點少,嚴重限制了名士對玄學的理論構建。
(三)元康時期
元康時期,玄學思潮再次興起,部分權勢人物針對原有思想弊病進行攻擊,力證崇有,原有貴無思想的權勢人物保留原有意見進行反駁,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許多人避而不談思想的問題。在清談中,從高官到乞丐,從學術大師到少年學子,都有平等的發言權。思想包容性增大,社會節點增加,社會資本開始流動,思想繁盛,但好景不長,崇有思想隨著裴頠的死于非命而終結。隨后郭象發展玄學,在貴無和崇有正反兩題上提出了合題,即獨化。帶來新的理論方向,玄學較為興盛。
裴頠,玄學名士裴秀之子,其母與賈后母為親姊妹。他是賈后親戚中少有的治國干才,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官至侍中和尚書仆射,作為外戚賈氏的代表,對當時的政治決策影響極大,是元康時期的實權人物之一。[6]
《世說新語·文學》說道:“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
以上的材料說明,裴頠以反社會潮流的姿態活躍于思想舞臺,其也并非孤軍奮戰,歐陽建⑦曾著《言盡意論》反對貴無派的言不盡意思想,《崇有論》的問世,在學術界引起了大辯論。裴頠的網絡規模大,網頂涉及權力集團的中心人物,而且其自身就是實權人物,網差較小,網絡構成合理。社會資本起點較高,加之其合理的運用,社會資本流動快,網絡節點多,玄學發展興盛。
郭象并非名門出身,但郭象憑借其清談的實力,得到了王衍的青睞。之后進入司馬越集團,官職、權力均超越王衍。
郭象通過清談獲得賞識,同時也在被賞識中不斷發展自己的學問,有人說《莊子注》是郭象竊取了向秀的成果,但不可否認,郭象運用其社會資本為玄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高度。郭象的網絡規模較大,網頂為當時權力的中心人物司馬越,自身也為實權人物。其出身看,他網差較大,網絡構成合理。社會資本基數大,網絡節點多,社會資本流動快,玄學發展興盛。
從裴頠和郭象可以看出兩人對社會資本的運用,再用社會資本發展玄學的同時也用玄學提高了自身的聲譽。在郭象身上尤能看出社會資本的運用和玄學發展的互進關系。
(四)東晉時期
東晉時期,戰爭分散了人們對理論的注意力,社會資本基數雖大,但其大致被分為保身立命和發展玄學兩部分,所以用于發展玄學的基數減少。加之佛教“借力打力”,網絡節點多,佛學社會資本流動快。在玄佛兩方力量對比下,玄學處于弱勢地位,之后玄學走向衰敗。
張湛約生于370年前后,卒年不祥。是東晉人。其生存年代戰爭頻繁,政局動蕩,并于383年發生了淝水之戰,399年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晉斗爭,在這之后的21年里,戰爭不斷,東晉于420年亡,取而代之的是南朝。
張湛在孝武帝太元時期官至中書侍郎、光祿勛。[7]其職位很高,但在戰亂頻發的時期,民眾對佛學更加認同,尋求心靈的解脫,使得其社會資本失靈。根據其官職判斷,其網絡規模較大,網頂較高,網差較小,網絡構成合理。社會資本基數較大,但動亂使得張湛的社會資本分散,也使得離他較近的網絡節點的社會資本分散。在中心與節點社會資本均分散的情況下,社會資本流動速度慢,玄學走向衰敗。
從以上分析來看,王弼、裴頠、張湛的社會資本測量標準類似,但玄學的興盛程度卻不同,原因在于在運用社會資本發展玄學時,張湛的社會資本未產生像王弼和裴頠的社會資本所產生的玄學的廣泛傳播,而未廣泛傳播的原因是社會動亂造成民眾對玄學的認同度降低,所以在玄學傳播的網絡之中出現了“節點缺失”的情況,而節點缺失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社會資本流動速度慢,效率低,玄學走向衰落。
三、對現代社會的啟示
(1)思想的發展需要社會資本根基,同時也要不斷“找節點”“織網絡”。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知識分子的交流促進了學說的發展,在其中會促進社會資本的增加,而之后又會進一步促進學說發展,所以學說發展繁榮,社會資本在此如同一張不斷擴張的網絡,從“小網”不斷創造新的聯系而織成“大網”。每個人均屬網絡節點。
(2)制度建設不合理,可能會帶來與現世不合時宜的逆反潮流的不斷擴張。在社會擁有一批“行為解放”的人并且其行為引起社會關注時,擁有逆反潮流的思想的人會聚集、相互促進,在造成一定影響之后,就會增加和其他社會群體高層人物的相識幾率,從而獲得更多社會資本,保證其行為不受過分苛責,逆反思潮興起。兩種社會網絡的沖撞必會導致兩方不相容的成分更加明顯,在這種暗示之下,網絡中的人會出現折中、趨同、逆反強化的情況,竹林時期的阮籍屬于折中,向秀、山濤屬于趨同,而嵇康屬于逆反強化。這對思想的發展并無太大好處,因為雙方已并非思想領域的交戰,而是從思想對外進行了延伸,如鏟除異己、株連九族等。
(3)個人社會資本的運用是“利滾利”的。在某思想層面社會資本運用得好,思想發展的同時也會促進個人聲望、地位的提高,而在社會地位提高之后又會獲得新的社會資本,而這又會促進思想的發展,螺旋上升。當然,如果社會資本在某一環節出現了中斷,就無法與其他思想相抗衡,所以必然導致思想的衰敗,而這衰敗可能是暫時的,如儒家,也可能是永久的,如崇有論。
(4)思想的興盛需要流動的社會資本。張湛官居高位,其學說影響力較大,但實際情況與理想情況相悖。其接觸的人群有限,雖在學說系統建立過程中有將軍韓康伯等人的協作互進,但其社會資本是非流動的。與此同時,支道林、僧肇憑借自己清談的功力以及對佛學的正確解讀,使佛學逐漸取代了玄學的地位。從此可見,思想的發展需要把握時代的脈搏,思想的發展只有使人“果腹”即感到滿足,才可成為主流。
而主流思想的社會資本是流動的,而并非僵化的。
思想的發展須對社會資本進行良好的利用,首先要有眾多的社會節點,其次要有快速的社會資本流動,否則思想的傳播范圍有限,最后只會由于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而被合并、衰落。
注釋:
①玄學:本文采用湯一介先生的定義,即魏晉玄學指魏晉時期以老莊(或三玄)思想為骨架,從兩漢繁瑣的經學中解放出來,企圖調和“自然”和“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它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本末有無”問題,即用思辨的方法討論關于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遠離“事物”與“事務”的本體論形而上學的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企圖使中國哲學在老莊思想基礎上把儒道兩大家結合起來的極有意義的哲學嘗試。
②王粲:在文學上,王粲與孔融、徐干、陳琳、阮瑀、應玚、劉楨并稱“建安七子”。王粲不僅名列七子,且是其中成就較大的一個,與曹植并稱“曹王”。
③何(晏)以為圣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鐘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圣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④清談:魏晉知識分子的學術辯論會,雖由玄學家發
起,但不局限于玄學家,亦不局限于玄學論題,各種學術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人,均可參加。
⑤何晏:字平叔,仕魏,曾在曹爽集團中任吏部尚書,推行改制,正始十年被處死。
⑥山濤:字巨源,河內懷縣人也,官居吏部尚書。
⑦歐陽建:當時賈謐“二十四友”的核心人物。裴頠是賈謐的表叔。
參考文獻:
[1]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12-113.
[2]邊燕杰丘海雄.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J].中國社會學,2000(2):87-88.
[3]張文宏.中國的社會資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測量和經驗研究[J].江蘇社會科學,2007(3):143-144.
[4]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
[5]劉世明.竹林玄學與山濤[N].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5(8):30.
[6]王曉毅.郭象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111-112.
[7]王曉毅.張湛家世生平與所著《列子注》考[J].東岳論叢,2004(6):166-170.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