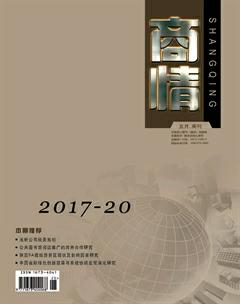表見代理制度構成要件的分析與構建
惠強
(陜西省咸陽市三原縣人民法院審判員 陜西 三原 713800)
【摘要】表見代理作為一種特殊民事法律行為,學術上長期以來一直對它的構成要件存在爭論。本文通過對不同學說及我國合同法立法現狀的分析,提出將本人關聯性內置于相對人“合理信賴”的新單一要件說。
【關鍵詞】表見代理 構成要件 可規責性 本人關聯性
一、表見代理構成要件爭論
表見代理是一種特殊的民事法律行為,它具有無權代理的特點,但因本人與無權代理人之間的關系,具有授予代理權的外觀即所謂的外表授權,致相對人信其有代理權而與其為法律行為,進而產生與有權代理同樣的法律效果。
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問題一直是民法學上爭論激烈的議題。在表見代理構成要件的爭論中,學說上已經形成“單一要件說”和“雙重要件說”兩種不同的觀點,持單一要件說的學者認為,構成表見代理的條件只有一個,只要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這一特征,即可構成表見代理,本人有無過錯都不影響其構成。該說認為,相對人“善意無過失地相信無權代理人有代理權,是表見代理的唯一構成要件”,認定表見代理“必須將被代理人于無權代理發生之主觀心態排斥在外”。持雙重要件說的學者認為,構成表見代理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本人存在過失; 二是相對人不知行為人無代理權。可見,雙重要件說強調本人存在主觀過錯這一要件,增加本人的責任。對這兩種觀點比較可知,在判斷是否成立表見代理時,單一要件說適應交易便捷和保護交易安全的角度出發,更易于操作,只要審查是否存在“有理由相信”的表象即可,而雙重要件說除了具備有代理權的表象外,還得認定本人是否存在主觀過失,只有二者都具備了,才能構成表見代理,否則不構成表見代理。在實踐中,大陸法系的很多國家采用單一要件構成說,比如日本和德國民法制度就是采用單一要件構成說。根據我國《合同法》第49條規定,在發生無權代理時,如“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則代理行為有效。通過該條規定可見,構成表見代理,我國《合同法》并沒有強調本人的過錯問題,只強調了“有理由相信”這一條件,表明我國在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中,也采取了單一要件構成說。
二、《合同法》第49條中本人歸責性的分析
我國《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從該條的文義看,表見代理需要無權代理人具有代理權的外觀與相對人有正當理由信賴該無權代理人有代理權。雖然在學說上對于表見代理的理論基礎,存在著交易安全說與權利表見責任的分歧。但是依據立法資料的解釋,設立表見代理制度的目的是保護交易的安全性,因此相對人只要證明自己和無權代理人訂立合同時沒有過失即可,至于本人在無權代理人訂立合同問題上是否有過失,相對人有時難以證明,并不以此為構成要件。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我國表見代理制度大體沿襲了法國法的做法,其最大的特點就在于,表見代理的成立,不以被代理人的“過錯”或者某種“可歸責性”為要件,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并非通過民事責任方式以保護第三人合理信賴。2009 年頒布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 號)認為,應當從構成要件方面穩妥地認定表見代理,但也未涉及本人的歸責性。該解釋第 13 條規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依據上述分析可知,我國現行《合同法》第49條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表見代理的判斷上,僅限于代理權外觀與第三人的合理信賴,不以被代理人的可歸責性為獨立的構成要件。
三、新單一要件說的構建
歸責屬于侵權法或民事責任制度中的概念,,被代理人承擔的是債務而非責任,以民事責任尤其是侵權法上的歸責原理適用于表見代理,并不妥當。同時,本人可歸責性的認定標準復雜,會極大的影響司法實務對表見代理的判斷。而且,將本人歸責性作為表見代理的獨立構成要件使本人利益與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同等對待,有悖于我國表見代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立法宗旨。但是,盡管表見代理系以犧牲被代理人的追認自由為代價,也不能過分忽略對被代理人利益的保護,單純地、絕對地強調保護代理活動中第三人的利益,對本人的利益全然不顧。應堅持非所有具代理之法律外觀者均構成表見代理。因此,筆者主張將本人關聯性內置于相對人“合理信賴”,以此闡釋我國《合同法》第49條及其司法解釋,更具有說服力及妥當性。本人的關聯性與歸責性不同,較之“可歸責性”,“關聯性”的要求顯然更低,關聯僅僅是構成第三人合理信賴的客觀環境要素之一;或者認為,對于法官和第三人而言,某人放任代理權表象的發生,往往是證明合理信賴成立的證據,并由此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實義務。在將本人關聯性視為相對人合理信賴因素的具體構造上,應當結合代理權外觀進行判斷,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1)對于行為人是否具有代理權存有疑問。如果行為人用于證明身份印鑒、印鑒證明書、委托書、權利證明等存在令人懷疑的情事,相對人應當向本人調查確認。如果相對人怠于調查確認,則其具有過失。
(2)代理人本身具有可疑性。如果行為人雖持有用于證明身份的印鑒,是其本人的親屬等,處于容易取得用于證明身份的印鑒并且濫用地位的情形。
(3)本人的不利益。若實施的代理行為使本人將蒙受重大不利益,在此情形,就本人是否真的有負擔那般不利益的意思,需要調查確認。相反,在某些客觀環境,例如長期代理關系的存在、特定身份關系的存在等,相對人不用去核實行為人的代理權狀況,這種客觀環境,構成了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賴”。
參考文獻:
[1]崔北軍.試論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類型及效力[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
[2]冉克平.表見代理本人歸責性要件的反思與重構[J].法律科學,2016,(1).
[3]朱虎.表見代理中的對代理人可歸責性[J].法學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