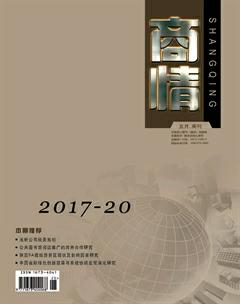淺析違約金數量調整規則
李連同
(陜西省咸陽市三原縣人民法院審判員 陜西 三原 713800)
【摘要】合同法第114條對違約金調整進行了規定,合同法解釋二也對此進行了解釋,但是二者對如何判定違約金性質的差異、如何適用違約金調整的具體規則,均未進行具體規定,導致違約金調整制度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實踐中裁判結果往往差別較大,本文從法理學以及實務操作的角度對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的規定進行分析,進而探討違約金調整中的范圍以及規制等問題。
【關鍵詞】合同法 違約金調整 懲罰性違約金 賠償行違約金
私法自治是合同法的根基,而違約金調整制度是對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這一制度是為兼顧實質公平和個案正義而設,其正確適用涉及到如何合理平衡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調和意思自治和個案正義,筆者通過分析違約金分類和成立條件,提出合理適用違約金調整的規則。
一、違約金的功能與分類
(一)違約金的功能
違約金在歷史上一直作為債務履行的擔保工具,在傳統民法上,定金和違約金往往被一并規定在“債務確保”的名意之下。德國民法典、荷蘭民法典、俄羅斯民法典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均將違約金作為債務履行之確保或擔保加以規定。而法國民法典設立了損害賠償制度,規定了損害賠償額預定,即合同當事人事先約定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作為損害賠償,其目的在于填補損害,在債務人違反合同約定時債權人免于損害證明責任,具有簡化損害賠償制度的作用。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推知違約金集債之擔保和損害賠償之功能于一身。
(二)違約金的分類
當賦予違約金擔保功能時,違約金便具有了懲罰性質。懲罰性違約金體現的是一種私的制裁,擔保債務履行的功能非常明顯,因為其可以與損害賠償或繼續履行并用,已經超出損害賠償制度固有的范疇,而對債務人施予較大壓力。作為損害賠償總額一種民事預定的違約金,是責任的承擔方式時,此種違約金相當于履行之替代,因此請求此種違約金之后,便不能再請求債務履行或者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二、違約金責任的成立
違約金作為一種從債務,其成立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如果主債務不成立、無效、不被追認或者被撤銷,違約金債務也就不得成立或無效。同時,應注意,如因違約而解除合同,作為“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違約金條款仍然成立,并不因為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而被影響。
違約金責任的成立以嚴格責任為原則,以過錯責任為例外,如果當事人約定違約金的成立以一方當事人的過錯為要件的,則依其約定;在合同法分則以及單行法規特別規定違約責任為過錯責任的場合,違約責任的成立需要以過錯為要件。在懲罰性違約金場合,由于其設立的目的在于給債務人心理上造成履行壓力,同時,在債務不履行的場合,表現為對過錯的懲罰,因此,應以債務人的過錯作為承擔懲罰性違約金的要件。而在賠償性違約金場合,除上述原因外,不要求以當事人過錯為要件。
三、違約金數額調整規則
按照合同嚴守原則,當事人通過合意達成的違約金無論是何種性質,都應該被嚴格遵守,但是,為了防止過度的合同自由,使違約金條款異化成為一方壓榨另一方的工具,合同法114條規定了違約金的司法調整。
(一)違約金性質辨明
如當事人在合同中為違約金條款明確約定了 “懲罰性”或有旨在擔保合同履行的意思表示,則應將其視為懲罰性違約金。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對違約金性質約定不明或者沒有約定時,應認定其為賠償性違約金。不能因為私的制裁而對民事活動中的等價有償原則進行沖擊。
(二)因違約金性質不同而產生的調整差異
(1)在賠償性違約金中,由于一般情況下非違約方必定會因違約方的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遭受損失,當事人形成合意的目的是對非違約方整體損失的填補。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的比較標準是因違約“造成的損失”,這一損失應以違約方締約時所能預見到的合理損失作為參考。當然,對違約金是否適當作判決時,應考慮債權人的一切合法利益,綜合考慮多種因素,而不僅僅是財產上的利益。債權人請求就賠償性違約金進行增額時,盡管合同法字面上只是限定于“低于”,但作為法官應將這一差異定義為“明顯”的,而不僅僅是“看得出的”,否則只要有差額就予以增額,必然使違約金的規范目的落空。而當約定的違約金高于造成的損失,當事人請求予以司法調整時,應當由請求減額的債務人負擔舉證責任。司法機關在進行裁量時,可以將違約金與實際損失之間的差額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但絕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還應考慮債權人其他的合法權益,如債權人尋求替代交易的難易程度,是否因信賴該合同的履行而與他人簽定連環合同,以及債務人是否有主觀上的惡意等。合同法對減額幅度的用語是“適當減少”,筆者認為,法院應能動性的有所節制。綜合考慮雙方的交涉能力是否平等,是否使用格式合同等因素。
(2)在我國,懲罰性違約金原則上可由當事人自由約定。在懲罰性違約金中,當債務不被履行時,債務人除需支付違約金外,其他一切因債之關系所應付的責任,均不受影響。此類條款,屬于私人之間的制裁,我國法律雖未禁止,但是并不意味著放任。就我國法律而言,可以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54條的規定,通過無效或者可撤銷等制度規范此類條款的效力。懲罰性違約金條款如是以格式條款的面目出現的,還可以依據合同法第39條、第40條等條款加以規制。另外,盡管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對懲罰性違約金進行明文規定,更沒有對其數額進行限制,但是鑒于擔保法第91條規定的定金,同樣屬于私的制裁,其數額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的百分之二十。考慮二者相似的利益狀況,擔保法該條的立法精神也因該體現在懲罰性違約金上,故筆者認為,對于懲罰性違約金的數額,法以類推適用擔保法第91條的規定,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百分之二十。
參考文獻:
[1]韓世遠.違約金的理論問題—以合同法第114條為中心的解釋論[J].法學研究,2003,(4).
[2]違約金調整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對《合同法》第114條的分析[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2).
[3]違約金數額調整研究[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