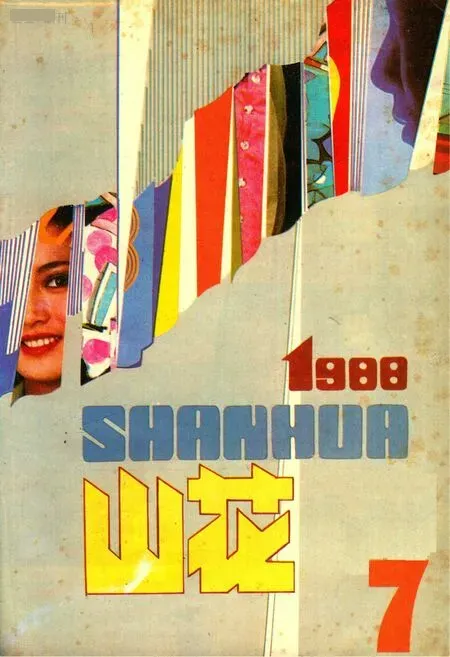那些頑固的陰影已不復存在(七首)
蘆葦岸
埋首塵世
不要裝,真理已經(jīng)死掉
忍冬花的枯葉下,一場薄霜剛剛收起
注腳。它們顧不得霧霾深重
潮水一樣退去,像失去了對現(xiàn)世的耐心
在散開的草木中,安頓一顆心
對斷頭臺說不,對活著多點耐心
與每一天的茍且都像是赴死
在更低處,抱守日腳
埋首塵世,一腔熱血,足夠
本雅明之歌
單行道上空的落日仿佛柏拉圖的精斑
意象的血液源源流向夢的蹤跡
如果談論:每一首詩寫出來就好像
第一首,或是最后一首。我羞愧
詞語的命運,在洞穴世界被荒謬替代
用減法置換偷生,也只是耽于空想
從未放棄盆栽的棕櫚,希望借此獲得
向上的力量,而時間已拉開身體的拉鏈
人類的好日子不多了﹡,卻像剛剛開始
昨天埋下的罪孽,開滿罌粟
隱喻始終是個財主,端坐于晚宴前
賓客們動手和動嘴,注定都會載入史冊
﹡出自莫言142
《哪些人是有罪的》。
描 述
架在一條活魚的身上的刀
才像刀,或刀法:嫻熟、精妙、銳進
魚先于刀,卸下外套
而刀遲遲沒有入鞘
其實,它根本不需要隱藏
它以時間的庇護為恥
它讓死不瞑目的魚眼留下證據(jù)
它只讓銹跡,完成對自己的否定
在刀下,魚完結了茍且
掙扎也只是作為活過一場的象征
那么奮力擺動
是在表明弱者不乏危險的一面
也不好惹。或者,作為一種暗示
并非甘心交出生命的權利
因此,放血不多;腥氣
隱于水,喬裝成一條河流的樣子
相對于刀的精明,魚不笨
它知道除了刀制造分割皮肉的厄運
還有手這個難纏的幫兇
與其無謂抵抗,不如順勢就義
刮鱗不要緊,只要有尊嚴
甚至把最后一口氣留到油鍋里
在筷箸和高談里,碎骨
不取悅個人,只為向集體示范壯烈
于觥籌的喧嘩與快慰中
魚慶幸自己比刀更完整,更像魚
出世與入世,都鮮美
刀,除了殺得興起時的快活
多數(shù)時間,在角落和寂寞對抗
它不稀罕熱鍋的熱鬧
它執(zhí)著于用冷冰冰,模糊生死的界限
妥協(xié)與撫慰
它的前爪在墻根下
閃著歲月之光……一切的瑣碎
隨時針慢慢走向正點
當那一聲“喀嗒”讓旁邊的柳葉
微微顫動,然后停在一束
晌午的強光下
它反復回味在未來的位置上
獲得引以為傲的確認
或者,作為一次短暫的休憩
它試著調(diào)整了一下哲學的睡姿
鼻息、胡須、黑眼圈
和偶爾扇動的兩只小耳朵
在時間的寂靜里,妥協(xié)
讓一個夢倒在追趕另一個夢的路上
光陰的灰燼覆蓋全身
它沒有撲進人類的懷里
是因為,喧囂不屬于它的專利
溫暖,也不僅僅是
一種合身的撫慰。這個正午
默許了它的決定
它的尾巴沒有縮回去
啞劇般的空曠里,下著一場雪
賞月的另一種方式
看月亮的人都去天上了
我獨留人間
吃晚飯時,夜色在筷子里破碎
而我其實是想用它們夾住
當空的明月
但是一場倒霉的雨
摸進了碗里,讓我吃相狼狽
我在冰冷的夜里睡去
我在寂寥的時辰醒來
月亮,已被眾生瓜分
唯有我的孤獨還很完整
像這個渾圓的世界,明亮而寂靜
黑暗如此閃光
令我猝不及防
田野調(diào)查
把全世界的陽光趕到這里
讓它們和滲漏的地表水
滲入深厚的大地
更深的黑暗在土壤深處
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蓄滿溫暖
春天,催生萬物
輕易占領人類肅然的生活
在黃昏,俊鳥落窩,水回流
草開始打點葉尖上的細軟
清洗露水里的塵雜
這夜色下最安閑的時間
接納從寬闊河道進入溝渠的水
接納越來越窄小的光陰
自然的竊喜,蠱惑暗中的動物
率性的它們,不按章法入世
亦如我蹲伏的腳下,泥濘濕滑
每挪移一步,都像是一次布道
隆重且透露出活著的甜蜜
給西蒙娜·薇依
陽光滿城。此刻的紙上
你比廓外混沌天底下的西湖更神秘
西蒙娜·薇依,我從窗外的喧囂中
拯救了自己。獨坐于木桌前
分解身體里多余的脂水。俯瞰
那些陰影雜亂的枝條切割街道的走向
如你偏頭痛發(fā)作時服下的鎮(zhèn)定劑
人間恍惚,無比虛弱
所有的哲學都得回歸生活
農(nóng)田里,莊稼和葡萄交替?zhèn)魉徒?jīng)驗
那些經(jīng)過你的事物,滿懷重負與神恩
“苦行是一種必須”,你的笑
無人可以模仿;精神的自傳
在遙遠的東方,對峙著早春的寒苦
不得不再次打開冊頁,唯其如此
亂世的呻吟才會減輕一些
在更久長的時間里,我撫摸書本
享受成為黑暗的一部分
也享受著身外浩蕩的光明
——那些頑固的陰影已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