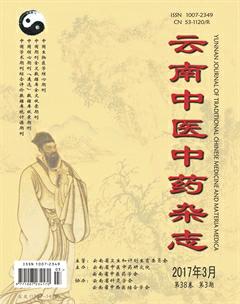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彝族醫藥研究綜述
韓艷麗 鄭文 那霄雯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彝族醫藥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本文以國內公開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為線索,兼顧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公布的數據,從彝族醫藥概念研究、彝族醫藥“非遺”特質研究、彝族醫藥傳承人研究、彝族醫藥傳承路徑研究、彝族醫藥申遺研究5個方面展開述評,以展示研究成果,并為今后的研究明確方向。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彝族醫藥;綜述
中圖分類號:R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7)03-0093-03
彝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人民長期生活在藥物資源極為豐富的涼山、金沙江、烏蒙山、哀牢山和無量山一帶,在與疾病作斗爭的實踐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彝族醫藥。彝族醫藥底蘊深厚、內容豐富,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后,我國學者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角度出發對彝族醫藥展開研究,形成了一定研究成果。
本文以國內公開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為線索,兼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管、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云南省文化廳主管、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辦的“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等官方網站進行資料收集、整理。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展開的彝族醫藥研究,可以歸結為以下5個方面。
1彝族醫藥概念研究
彝族醫藥概念在我國相關學者的研究、闡述下日臻完善。王敏從民間傳說、古籍文獻記載、考古出土文物和民間民俗流傳4方面論述了中國彝族醫藥歷史源流,認為彝族醫藥源遠流長,其伴隨著彝族先民的生存斗爭與生產實踐,發端于神話傳說時代,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步形成與成長,并發展成為內容豐富而獨特的彝族醫藥學。錢韻旭等從地理環境的視野探究了彝族傳統醫藥,認為“彝族醫藥基礎理論受到地理位置臨近的漢文化的深刻影響;彝族醫藥與所處地區的氣候條件、生態環境,尤其所分布的動植物種類密切相關;彝族醫藥擅治生活環境的多發疾病或者采用一些適應當地環境的治療方法;由于地理的隔絕,彝醫多用單方或者簡方”,說明彝族醫藥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羅艷秋、徐士奎通過對彝漢文史資料和田野資料的系統研究,認為彝族醫藥是根據彝族先民所創制的先天八卦太陽周天歷法測度日月運行規律,結合氣候時節推算生物的首萌長遍退藏,在此基礎上形成以陰陽療疾理論為核心的醫學理論體系,保留著中華上古醫藥理論的源頭,對中國傳統醫藥的發展與傳承具有重要價值。
通過對彝族醫藥概念的闡述,有助于我們理解彝族醫藥的歷史源流、地域特色、理論基礎等,明白其醫療保健作用及文化內涵。
2彝族醫藥“非遺”特質研究
國內學界撰文闡述彝族醫藥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揭示其人員銳減等的瀕危狀態。秦國政認為彝族醫藥至今在我國云南、四川、貴州及廣西等地區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服務于當地人民群眾的重要衛生資源,是具有中國特色衛生事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顏曉燕、童志遠認為彝族醫藥同其他少數民族醫藥一樣是我國傳統醫藥、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少數民族醫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國本從民族醫藥的醫學范疇、人文因素;衛生事業、經濟產業;自然文化、人文文化;民族文化瑰寶、文化交流口岸;地方、中央共同規劃,全面協調保護五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關系出發分析了民族醫藥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趙富偉等通過大量實地調查,以第一手數據從民族醫藥傳承人“非法行醫”、女性在傳承人中所占比例偏低、傳承人隊伍老齡化問題突出、潛在傳承人數量銳減、傳承人受教育程度低5個方面,揭示民族醫藥傳承危機。崔箭等認為由于受到全球化、現代化的沖擊,目前民族醫療機構治療的病種日益減少,許多知名的老民族醫生由于年齡偏大相繼離開了工作崗位,現存的民族醫療服務陣地越來越小,盲目的用西醫和中醫填補不足的現象十分普遍,特別是在民族醫藥的人才隊伍方面。
無論在學界還是在普通民眾中,人們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彝族醫藥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其加以保護、傳承和發展不僅是開發其醫療藥用價值的需要,也是傳承中華民族物質與精神財富的需要。面對彝族醫藥的傳承危機,如不加緊采取措施給予有利幫助扶持,彝族醫藥的傳承將面臨急劇的流變和消失的風險。
3彝族醫藥傳承人研究
面對當前彝族醫者中出現的年齡斷層問題和“技在人身,技隨人走,人亡技亡”的特點,對彝族醫藥傳承人的認定與培養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中,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具備的條件,這對彝族醫藥傳承人的認定,特別是申報國家、省、地、市級別的項目傳承人具有指導意義。秦阿娜等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論述“從廣義上講,凡是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彝醫知識治病并將其告知于他人的人,都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著彝醫文化的傳承。而從狹義上講,只有掌握豐富的彝醫知識,直接參與診治活動并樂于將其傳授于他人的彝醫從業者,才能稱得上是彝族醫藥的傳承人。民族醫藥傳承人培養模式,包括3方面的內容:申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鼓勵民間傳承;以學校教育為基礎的傳承。”諸國本認為對于傳統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培養至關重要,在培養目標及教育方法上應考慮“在現有的中醫藥院校或專業內開設‘非遺課程,加強‘非遺教育;對省、地、市級非遺項目中已經確定的傳承人,利用舉辦培訓班、專題學習班的形式,加強培訓,進一步提高社會責任感和專業水平;對可能入選的‘非遺項目,特別是民間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醫藥人員,通過集中辦班、分散實踐觀察等辦法,提高他們的文化、專業水平。”有學者從“活態傳承”角度闡釋民族醫藥傳承人的重要性,認為活態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特征,區別于文物的定點保護、博物館式的實物收藏、古籍整理等的“靜態”保存,強調傳承過程中人的重要作用,傳承人集中體現了活態傳承的內容、形式與手段。胡芳梅等認為彝族醫藥傳承與發展離不開彝族醫藥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研究,以應對當前彝族醫藥面臨空前的“斷檔”危機。李佳川等認為需要建立民族醫藥人才培養體系,從民族地區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民族醫藥教育體系多形式多層次發展等方面,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助力民族醫藥的發展。
對彝族醫藥傳承人概念的闡釋還不多,然而彝族醫藥傳承人作為彝族醫藥傳承的重要載體,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已有的對彝族醫藥傳承人的培養探討有理有據,為具體彝族醫藥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工作提供了思路。
4彝族醫藥傳承路徑研究
學者們主要從兩種不同的思路出發探尋彝族醫藥的傳承路徑。思路一,通過尋找民族醫藥傳承的渠道或方式,描述民族醫藥在傳統或當下的社會環境中的內在傳承機制。王志紅、向芯慰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指出,民族醫學醫技的傳承基本上都是以“口傳身授”為主,強調個體經驗的積累和體驗型的學習方式,其“秘方”和醫技大多也只有記憶相傳,沒有文字記錄;有些專家“保密”意識較強,有“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的傾向,傳習人基本上是在子女親屬之中選擇。梁正海等在對湘西蘇竹村個案研究基礎上,總結出地方性醫藥知識的傳承機制和特點,認為縱向承繼(祖傳、師傳),橫向交換(自由式交換和當地政府干預下的交換)都是其內在機制。沙學忠認為畢摩是彝族文化的傳承者,也是診療疾病的實施者。畢摩經書上有部分彝醫藥方面的記載,彝族醫藥理論基礎來源于畢摩的部分理論,畢摩對彝族傳統文化(包括彝族彝藥)的繼承與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吳道顯等將云南民族醫藥文化的歷史傳承模式總結為文獻傳承、言傳身教傳承、學校教育傳承和產業化發展傳承。思路二,學者們在總結區域彝族醫藥發展現狀的基礎上,為保護、傳承、弘揚彝族醫藥非物質文化獻計獻策。徐士奎等在總結云南省彝醫藥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提出發展彝族醫藥的對策:梳理彝族傳統醫藥基礎理論、建立彝藥臨床研究基地、開辦彝醫藥專科服務窗口;組建彝醫藥知識傳承的主線型團隊、彝醫藥產業發展的多元化團隊;集中打造“彝族醫藥”品牌,用品牌統攝與培育各品種品牌和各產業鏈;對彝族藥實施分類管理,對面臨枯竭的部分藥材盡快開展馴養種植,提升其資源儲量和質量;重視技術創新,使彝藥質量工作有效促進彝族醫藥產業的發展。許嘉鵬等在調研楚雄州彝族醫藥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提出,創造條件開展彝醫藥執業資格考試。在開考之前,依據一定的辦法認定部分彝醫藥系列專業人員、鄉村彝醫,解決其合法行醫的身份問題。楊祝慶認為收集、整理和挖掘第一手資料建立檔案,是云南民族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手段。
彝族醫藥的傳承路徑是彝族醫藥研究的核心議題,學者們從不同思路出發,指出彝族醫藥的內在傳承機制及就當前彝族醫藥發展現狀指出保護、傳承、弘揚彝族醫藥的可行性辦法,已涉及傳統理論梳理、醫療研究與運用、藥品研發與種植、彝族醫藥品牌打造、合法行醫身份認定、建檔保護等,思路開闊、具有啟發意義。
5彝族醫藥申遺研究
由政府主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四級名錄的申報對彝族醫藥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早在2010年秦阿娜等就在《文化遺產視野下的彝族醫藥——探索動態保護的可能》一文中指出“彝族醫藥尚無國家或省級名錄項目,這種狀況是與彝族醫藥豐富的內在價值和亟待保護的現狀不相符合的”,并提出彝族醫藥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的具體努力方法。以云南省為代表,由于各級政府的重視、相關人士的共同努力,彝族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實踐工作近年來取得了一些成績。目前,被各級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中,彝族醫藥代表性傳承人有7人,其中國家級1人,省級2人,州級4人;7人中除省級1人的申報地區或單位在四川外,其余6人都在云南。截止國務院公布的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入選其中的彝族醫藥代表性項目共有2項,分別是國家級1項——彝醫水膏藥療法,國家級擴展項目1項—一撥云錠制作技藝,申報地區或單位都在云南省楚雄州。同時,也有學者指出當前我國傳統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管理工作存在重申報輕保護、缺乏行業特色評審標準、申報主體模糊等問題,應從政策制度、資金保障、傳承人隊伍建設等方面完善傳統醫藥非遺保護措施。
對政府主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四級名錄的研究,有助于確有代表性的彝族醫藥傳承項目、傳承人盡早達到申報條件,盡早成功申報。同時,學者指出當前我國傳統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管理工作存在的不足,這些研究都是圍繞彝族醫藥的保護、傳承與發展進行的。
6結語
綜上所述,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角度出發對彝族醫藥展開研究,已經形成了新的研究熱點與研究方向。就研究方法而言,已從早期的文獻收集、整理發展到現在的文獻梳理與實地調研相結合;從區域、個案、專題研究切入,總結彝族醫藥傳承現狀、傳承機制,探討傳承辦法,使得彝族醫藥傳承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討論。就研究學術領域而言,已經涉及醫學、藥學、化學、圖書情報、歷史學、教育學等。不同研究方法的運用、不同學術領域的關照,使當前彝族醫藥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也反映了當前彝族醫藥保護、傳承與發展的緊迫性和意義所在。
筆者通過文獻綜述,認為此研究方向還存在繼續跟進的空間,如未來還可以結合實地調研,進一步加強對彝族醫藥傳承人的研究,提供傳承人的認定標準;開展彝族醫藥的當代傳承與變遷研究;引入人類學、社會、哲學等學科領域對彝族醫藥展開研究;不同領域、不同地域的彝族醫藥研究還需要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推進我國彝族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
(收稿日期:201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