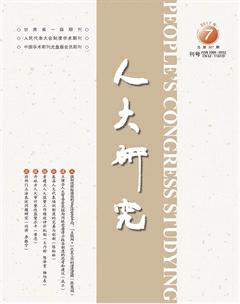論“一國兩制”的制度建構(gòu)與制度認同
周長鮮
時值香港回歸20周年(1997~2017),對“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總結(jié),引起國際國內(nèi)學界的較廣泛關(guān)注。概而言之,近20年以來,中外許多學者的相關(guān)研究廣泛涉及“一國兩制”的起源、歷史演進、現(xiàn)代內(nèi)涵、價值路徑以及體制建構(gòu)等諸多維度。從制度建構(gòu)和制度認同的視角來看,學界和實踐界對特別行政區(qū)立法會的研究也逐漸興起,作為制度建構(gòu)中的回應(yīng),也有許多學者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所面臨的挑戰(zhàn)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基礎(chǔ)性理論研究成果。本文現(xiàn)將有關(guān)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一、“一國兩制”的理論框架已初步形成,但尚需實現(xiàn)由法理到制度的全方位建構(gòu)
自1997年7月1日至今,由于“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和不斷深化,這對我國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對香港及大陸政治體制的發(fā)展形成了重要的影響。盡管,許多學者對于“一國兩制”的歷史起源、現(xiàn)狀和前瞻都已有較深入的研究[1],大大拓深了其價值內(nèi)涵,但仍存在若干可探討空間:(1)從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而言,針對我國目前的三種政治實踐模式:即中央與普通行政區(qū)、民族自治區(qū)和特別行政區(qū)的關(guān)系模式,學界的很多討論聚焦于“一國兩制”下中央與港澳的關(guān)系是否就是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呢?特別是對其中憲法適用性的問題,以及對國家主權(quán)和國家整合能力的影響,尚需在制度層面進行切實的探討(王振民,2000;張琳, 2008)。(2)從政體建設(shè)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的挑戰(zhàn)依然嚴峻。受近百年來的歷史發(fā)展軌跡影響,香港已與大陸在法制、文化和習俗等方面產(chǎn)生了較大的差異。對此,近年來的天星碼頭、保留政府山以及“占中運動”等事件,都反映出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若干民眾在政體建設(shè)上的強烈訴求,三權(quán)分立抑或行政主導制?仍需實現(xiàn)制度層面的進一步研究和完善(胡錦光,朱世海,2010)。(3)從制度的價值構(gòu)建而言,如何將“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進一步應(yīng)用到臺灣的和平統(tǒng)一?如何解決臺灣同胞對“為什么要統(tǒng)一”的路徑困惑,還需要通過“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鋪平從人心到法理到制度化的道路[2]。特別是如何通過香港、澳門的實踐而探索出對臺灣的結(jié)構(gòu)統(tǒng)一形式,還尚需加強“一國兩制”框架下對政治整合的機制、過程、模式、條件等問題的研究[3]。
二、對特別行政區(qū)立法會的研究漸進興起,但仍需拓深對其體制和工作機制方面的全方位研究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已從多個方面對香港立法會和澳門立法會進行了廣泛研究。許多學者不僅從歷史發(fā)展的視野探討了香港立法機關(guān)的組成、演變和運作實踐(周建華,2002;朱世海,2007);而且已深入到對基本法之下立法、 司法與行政(主導)方面的制衡關(guān)系的探討(梁美芬,2007;郝建臻,2011)。更重要的是,已有較多研究深入到對立法會的職權(quán)行使方面的探討,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1)對香港立法會行使預算審查批準權(quán)方面的關(guān)注。如,南方周末曾報道過香港立法會否決申辦亞運撥款一案,并認為是戳痛了政府的脊背(趙蕾,2011)。(2)關(guān)于香港立法會調(diào)查權(quán)的研究和分析,這已形成一個理論熱點。有些學者對香港立法會的調(diào)查權(quán)進行了法理和權(quán)限解析 (朱孔武,2009;王書成,顧敏康,2010;); 還有些學者則是通過案例研究而對立法會的調(diào)查權(quán)進行較深入的剖析,如,對“鄭家純、梁志堅訴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立法會”一案的研究(王鍇,2010)。(3)關(guān)于香港立法會的質(zhì)詢權(quán)方面的研究。對此,有學者認為,質(zhì)詢權(quán)在執(zhí)行過程中發(fā)生了異化,導致補充質(zhì)詢過多過濫,嚴重影響了行政主導體制的運作,導致行政主導體制有滑向立法主導體制的趨勢(徐加喜,姚魏,2000)。(4)關(guān)于立法會的制度建構(gòu)方面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對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guī)則的研究(朱宏濤,2001),對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完善方面的研究(陳家琪,2011);以及對香港立法會擴權(quán)及其制度與限度方面的研究 (周帆,2011)。除此之外,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研究動向就是關(guān)于對香港立法會的選舉政治與政黨制度方面的研究(周建,2009;梁玉英,2004)。有的學者對2012年立法會的選舉給其政治生態(tài)方面的影響進行了分析(陳麗君,2013),且越來越受關(guān)注的熱點話題則是關(guān)于“雙普選”對香港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分析(陳紹方、李厚強,2010)。當然,關(guān)于制度運行中的一些負面問題也引起了一定的關(guān)注,如,香港立法會的惡質(zhì)“拉布”及其治理問題(田飛龍,2014)[4]。
可見,盡管學界對立法會制度運行中的許多問題已有涉獵,但對其體制和工作機制方面的深入研究仍是欠缺。尚需從完善“一國兩制”的體制機制的角度出發(fā),深入分析香港特區(qū)立法會制度的理論基礎(chǔ)、歷史沿革和實踐運作,并結(jié)合香港、澳門等特別行政區(qū)社會運行的現(xiàn)實情況,尤其是對立法會實行普選等現(xiàn)實重大問題及時跟進研究,進而提出建設(shè)性的意見和建議。
三、對“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人大制度研究不足,還有待于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及時跟進
基于歷史原因,內(nèi)地和香港之間的法治不僅在語言載體上存在差異,而且在法律體系方面也存在著重要差異:祖國內(nèi)地現(xiàn)行的法律體系是大陸法系,而香港和澳門特區(qū)采用的是普通法模式。這些差異,在現(xiàn)實中難免形成表述差異、概念差異與效力差異的疊加。因此,隨著“一國兩制”的全面深入,如何實現(xiàn)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特別行政區(qū)立法會的融合與對接,已成為非常迫切的重大現(xiàn)實需要。
首先,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quán)的行使。在“一國兩制”體制下,內(nèi)地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的法律語言和法律體系存在明顯差異。有學者認為,法律語言差異是澳門、香港與內(nèi)地法律差異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祝捷,2013)。此外,對香港特區(qū)的立法,還需反思行政主導與立法的沖突問題(朱維究,2007),尚需對有關(guān)法律障礙進行切實的研究,進而建立起相應(yīng)的解決機制。尤其是中國內(nèi)地現(xiàn)行的法律解釋體制是立法解釋,而香港原來采用的是普通法模式,實行的是“司法解釋之上”的原則,這無疑對憲法解釋技術(shù)的發(fā)展提出了非常現(xiàn)實的要求。這不僅需要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及其基本特征進行研究(王振民,2007;鄒平學,2009),還需對人大釋法與香港司法釋法的關(guān)系進行進一步的明確(王磊,2007;秦前紅,黃明濤,2012;),進而探討搭建起港澳基本法的解釋模式。如,居留權(quán)等案件不僅涉及對兩地解釋體制的沖突,也涉及對香港終審法院的判詞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協(xié)調(diào)問題。有學者強調(diào)指出,法律解釋問題涉及香港的司法獨立,并最終與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產(chǎn)生聯(lián)系,內(nèi)地與香港兩種解釋體制的融合是“一國兩制”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5]。此外,在人大立法中,也需探討建立香港與內(nèi)地相互執(zhí)行仲裁裁決、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商事判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等制度的協(xié)調(diào)機制 (朱雪忠,1995;張憲初,2002;于志宏,2007) 。
其次,人大及其常委會監(jiān)督職權(quán)的行使。“依法監(jiān)督”作為人大監(jiān)督的首要原則,不得不首先解決“法”規(guī)范的差異問題。如,根據(jù)《澳門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guī)定,全國性法律除附列于《澳門基本法》者外,均不在澳門實施。即便是附件三所列的全國性法律,也需要經(jīng)過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公布或者立法實施等法律形式予以接受。據(jù)此,澳門具有相對獨立于內(nèi)地的法律體系。由于法律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對同一事項的規(guī)范內(nèi)容和規(guī)范程序也是存在差異的。對此,不僅需要進一步理順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性質(zhì)及其與憲法的關(guān)系(肖蔚云,1990;李琦,2002;劉茂林,2007),而且也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內(nèi)地憲法對特別行政區(qū)的法律效力(丁煥春,1991)。 另外,如何順利實施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quán)的保障與監(jiān)督問題(肖蔚云, 曾忠恕,1997),特別是如何協(xié)調(diào)“違憲審查”、司法審查制度的落實等問題,都還需要從制度上進行良好的設(shè)計和建構(gòu)。
再次,人大及其常委會對人事任免權(quán)的行使。20世紀8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行“代議政制”,使香港的選舉政治從無到有。選舉催生了香港政黨,政黨的產(chǎn)生及對選舉的介入又推動了選舉的發(fā)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后,在“一國兩制”下,根據(jù)香港《基本法》的規(guī)定,特區(qū)政府舉行了行政長官、立法會、區(qū)議會等一系列選舉。在每一次選舉中,政黨對香港政治發(fā)展的舉足輕重作用越來越得以凸顯[6]。對此,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香港特別行政區(qū)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chǎn)生辦法及有關(guān)普選問題的決定進行了說明,為推進新時期的政治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香港“雙普”選舉呼聲的不斷推高,對相應(yīng)有關(guān)人員的選舉、任命和罷免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尚需進一步的引導和規(guī)范。
四、學界對“一國兩制”在國家認同方面的研究比較集中,尚需從制度建構(gòu)和制度認同方面進行引導和保障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中文語境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還極少使用,但近年來發(fā)展十分迅速。據(jù)統(tǒng)計,自2006年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中,標題中含“認同”一詞的課題也在逐年成倍增長,研究選題十分廣泛。有的學者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視角進行闡述,指出民族問題的核心是國家認同問題,并從“一國兩制”與祖國和平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提出了構(gòu)建國家認同的可選路徑(費孝通,1999;許紀霖,2005;朱志勇,2006;馮穎紅,2009;沈桂萍,2010;王家英,1996) 。概而言之,理論界對“一國兩制”的國家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其在價值路徑上的構(gòu)建可歸納為三個維度。一是,從民族認同維度的價值構(gòu)建。需要重視的是,港、澳、臺人民對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的認同并不會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青年大學生所表現(xiàn)出來代際差異效應(yīng),已成為非常突出的現(xiàn)實問題。二是,經(jīng)濟利益維度的價值構(gòu)建。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qū)的大量經(jīng)濟投入與援助,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就業(yè)、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等方面的需求,但也面臨著如何平衡不同社會群體的差異化利益訴求的挑戰(zhàn)。三是,從法治維度的價值構(gòu)建,這方面仍是任重道遠。目前雖已通過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內(nèi)涵與外延都有所拓深,但還面臨著對“雙普”選舉的正確引導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法治路徑選擇問題,還有待于從國家制度建構(gòu)方面予以深化研究。
此外,從國外的有關(guān)研究成果來看,對“一國兩制”的政治認同方面的研究已形成了相對領(lǐng)先的國際話語主導權(quán)。尤其是有關(guān)研究對于認同框架 (地方/大中華)的問題以及對認同方式 (文化—族裔認同/公民認同)的思考[7],都能對相關(guān)的后續(xù)研究提供不同的視角和啟發(fā)。但是,也應(yīng)該看到,缺少了制度建構(gòu)的制度認同研究,很容易停滯于對現(xiàn)實短期效應(yīng)方面的評價,甚至是急于在制度成敗上草率立論。因此,在未來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實踐中,還有待于搭建起制度認同與制度建構(gòu)的協(xié)同機制,努力在制度建構(gòu)的長效機制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和建樹。
小結(jié)
“一國兩制”,顧名思義,不僅需要在“一個國家”的層面上進一步拓深政治制度建設(shè)的理論體系,而且還需要在“兩種制度”的不同語境中進行切實的制度建構(gòu)。為了促成從制度建構(gòu)到制度認同的協(xié)同演進,尚需在“一國兩制”的體制框架內(nèi),基于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安排而構(gòu)建起切實的政治整合機制。特別是要通過制度化的協(xié)商對話機制的搭建,使特別行政區(qū)人民的意愿能通過組織化和制度化的表達而得到妥善解決,逐步有序推進“兩種制度”在“一個國家”框架內(nèi)的有機融合,進而使“一國兩制”充分發(fā)揮出其應(yīng)有的制度績效。
注釋:
[1]孫翠萍:《“一國兩制”史研究的歷史、現(xiàn)狀與前瞻》,載《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2]吳陳舒:《“一國兩制”的價值路徑探討》,載《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3]王英津:《20年來的“一國兩制”研究:回顧與展望》,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4]注:拉布即冗長辯論(香港稱為阻撓議事,英語:filibuster)是西方議會政治的專業(yè)術(shù)語,狹義是議會中居于劣勢的一小部分甚至單獨一位議員,無力否決特定法案、人事,或為達到特定政治目的時,在取得發(fā)言權(quán)后以馬拉松式演說,達到癱瘓議事、阻撓投票,逼使人數(shù)占優(yōu)的一方作出讓步的議事策略。
[5]張小羅:《論“一國兩制”下兩地法律解釋體制之融合》,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09年第1期。
[6]周建:《香港政黨與選舉政治 (1997~2008)》,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Veg, Sebastian.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
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 1-25.
(作者系北京聯(lián)合大學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