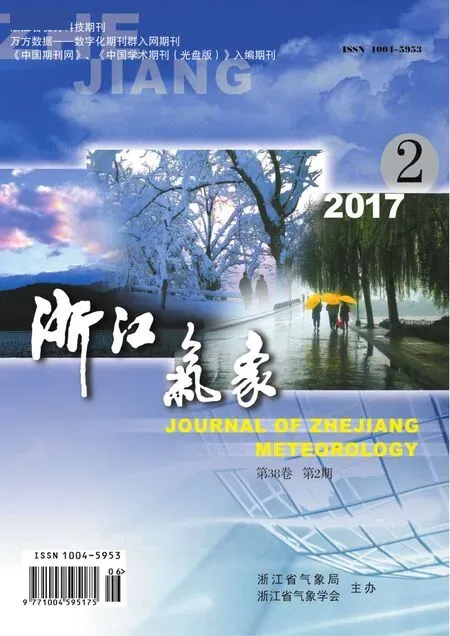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特征分析
周功鋌 李懷川
(1.臺州市氣象局,浙江 臺州 318000;2.溫州市氣象局,浙江 溫州 325027)
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特征分析
周功鋌1李懷川2
(1.臺州市氣象局,浙江 臺州 318000;2.溫州市氣象局,浙江 溫州 325027)
利用2014—2016年浙江及其周邊省市部分站點的PM2.5和浙江11個地市2012—2015年逐日、逐時AQI監測資料,結合1000 hPa風場資料,分析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污染源和污染過程特征。通過14個浙北重污染伴隨偏北大風過程發生時,在浙南發生或不發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環境場對比分析,探討浙南輸入型重污染的發生條件。結果表明: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是在浙北先發重污染且浙北到浙南風速明顯增強的同時,浙東南地區建立一個穩定層結、弱輻散或弱輻合、無明顯的垂直運動的污染物輸送通道條件下發生的,這一結果可為浙南輸入型重污染的短時預警模式提供依據。
輸入型重污染;污染源;污染輸送過程;污染輸送通道
0 引 言
區域周邊對區域污染物的平流輸送,是區域大氣污染預報、預警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徐祥德等[1]通過統計分析北京及周邊地區TOMS與MODIS衛星遙感氣溶膠區域性特征,發現北京城市重污染過程與南部周邊城市群落排放源影響相關顯著,綜合分析北京地區重污染過程軌跡特征并采用軌跡模式進行模擬試驗,進一步證實了北京城市重污染過程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南部周邊城市污染物外源的輸入。
對于區域之外空氣污染物的輸送,陳朝暉[2]等統計2003年9—12月7次大氣污染過程發現,當華北地區為大尺度高氣壓控制時,河北為弱的低氣壓區(地形槽)時,將導致西南風氣流盛行該區域。受地形和天氣型控制,西南方向的輸送通道是引起北京大氣污染過程的主要通道。
王艷等[3]對代表城市前向軌跡進行計算以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污染物對外地的中尺度輸送,結果表明,東亞季風的活動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污染物的中尺度傳輸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其中冬季季風是長三角污染物向華南和西太平洋地區傳輸的一個主要機制。
李懷川等[4]取重度污染持續6 h以上為一個重污染過程,通過2012年10月至2015年5月在浙南地區發生的31次重度污染過程AQI時間變化曲線圖分析,發現有12次明顯的從浙北輸送污染物致使浙南地區發生重污染的過程,占浙南地區發生重度污染過程總數的39%。
本文采用浙江及其周邊地區的大氣污染監測資料對各地的污染日數進行統計,分析浙南地區發生輸入型污染時的主要污染源;通過12次在浙南發生的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環境場變化特征分析及2次未發生污染輸送的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環境場對比分析,探討浙南地區(臺州、溫州、麗水三地)受周邊地域污染物平流輸送發生大氣重污染的機制,為浙南地區的輸入重污染過程的預警模式建立提供依據。
1 浙南及其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分布的統計特征
1.1 資料的選取
研究表明,大氣污染危害人體健康的主要污染物是PM2.5,浙江省發生重度大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也是PM2.5[4];因此,我們取PM2.5濃度的日平均值進行統計分析。采用環保部門提供的浙江省2014年12月—2016年12月2年浙江省11個地市和滬、蘇、皖、贛、閩地區部分站點的PM2.5日平均資料,作為分析浙南地區和周邊地區的有關大氣污染物的環境場分布特征的依據。
據有關資料統計,浙南地區發生的重污染過程的維持時間多數在12 h以內,考慮到采用日平均監測資料可能會使部分重污染過程遺漏,且浙南區域周邊300~500 km內的大氣污染物輸送過程一般僅持續12~24 h,;因此,在研究外部污染物平流輸送對浙南大氣污染的影響變化過程特征時,采用浙江省11個地市的逐日逐時AQI監測資料。
1.2 浙南及其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分布的特征分析
據我國以PM2.5的24 h平均值劃分大氣污染等級的標準,將115~150、150~250(μg/m3)的PM2.5值分別定為中度、重度大氣污染;圖1a給出浙江省11個地市和滬、蘇、皖、贛、閩地區部分站點的2014年12月—2016年12月PM2.5日平均值≥115 μg/m3即中度以上污染的總天數分布圖;該分布圖說明,華東東南部地區的污染高發區有兩個,分別在上海及其南部的杭、嘉、湖、紹一帶以及皖東南的馬鞍山附近;其中上海、湖州、馬鞍山為高值中心,贛、閩地區為低值區;浙江省呈西北高東南低的分布特征,浙南各地的PM2.5≥115 μg/m3的總天數僅為浙北1/4~1/5,浙南和浙北差異顯著。這和文[4]給出的浙江省2012年10月至2015年5月AQI≥200的重污染總時數空間分布特征相一致(圖1b)。

圖1a 華東東南部地區2014年11月—2016年12月日平均PM2.5≥115 μg/m3日數分布圖

圖1b 浙江省2012年—2015年重污染總時數分布圖
2 浙南輸入型大氣重污染過程分析
2.1 浙南輸入型大氣重污染過程的分型
有關研究表明[5-7],區域性重度污染過程與有利的氣象條件下本區域污染物的累積或上游地區重度污染地區的水平輸送有關,或為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據此可以把區域發生的重污染過程分為累積型和輸入型。累積型重污染一般發生在該區域持續較長時間的(一般48 h以上)低層弱風場(風速≤4 m/s)、弱輻合或弱輻散、穩定層結的環境場中,當風速增強時(風速≥6 m/s),重污染過程即結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則發生在上游重污染先發地區低層出現有利于向區域輸送污染物的較強氣流時,即風速明顯增強時(風速≥6 m/s),致使當地AQI值快速升高,發生重污染;一般這種輸入型重污染過程污染程度變化較快、重污染維持時間也相對較短。
據圖1a、圖1b可以認定,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的污染源在上海、浙北地區(杭、嘉、湖、紹)及皖東南地區;由于上述污染源向浙南輸送污染物都經過浙北,所以,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可以把浙北先發生重污染伴隨偏北大風作為起始條件,為浙南建立輸入型重污染預警模式提供依據。
李懷川等[4]通過2012年10月至2015年5月12次浙南地區輸入型重污染的過程的特征分析,將輸送過程分為兩類,即移動型和擴散型,移動型又表現為局域(指二個以下地市的區域)移動和片區(指3個以上地市的區域)移動兩種方式。
1)移動型
浙北先發生重度污染的局部區域污染氣團在一定條件下隨氣流向偏南方向移動,當區域風速增強時,污染物向下風方向輸送,本地AQI同時下降;其后,隨著污染氣團的快速南移,沿下風方向各地依次發生重度污染,在AQI時間曲線圖上則表現為下游各地依次出現AQI峰值,將此類向下游輸送污染物的空氣污染過程定義為移動型。

圖2 移動輸送型各地AQI和風速風向變化
圖2a為2014年1月25—26日AQI和1000 hPa杭州與溫州地區風速風向的變化,由圖可見,1月25日08時嘉興和湖州地區最早出現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25日17時湖州地區AQI達峰值,為451,浙北地區偏北風增強至6~8 m·s-1,在污染物向南輸送的同時,嘉興和湖州地區AQI隨之快速下降;此次局域污染物移動輸送過程的軌跡為從浙西北地區向浙東南地區,即嘉興和湖州—杭州和紹興(寧波)—金華(衢州)—臺州和麗水—樂清和溫州地區,依次發生重度污染。
圖2b為2013年12月25—27日浙北片區向浙南片區的污染輸送過程,由圖可見,26日14—20時浙北的湖州、嘉興、紹興、杭州和寧波AQI同步達峰值,發展為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26日14時至27日08時全省偏北風風速增強至8~10 m·s-1,污染物向浙南地區輸送;浙北各地AQI迅速同步下降至中度或輕度污染;此次
污染過程為浙北片區同步累積達重度污染后,污染物向南輸送的過程。
2)擴散型
與移動型輸送不同,當先發生重度污染的區域風速加強,向下風方向輸送污染物使下游地區重度污染發生時,本地污染程度仍維持或繼續發展,將此類污染物的輸送過程定義為擴散型。以2014年1月17—19日重度污染過程為例說明,由圖3可見,1月17日14時至18日02時浙北4個地區和寧波地區先發生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18日02—20時全省1000 hPa偏北風速增強并維持6~12 m·s-1,浙北地區向浙南地區輸送污染物;同時,浙南的臺州、樂清、麗水和溫州4個地區AQI依次快速上升(自NE向SW輸送);18日06—22時臺州、樂清、麗水和溫州地區先后發生重度污染;而浙北和寧波地區18日02時后AQI仍繼續維持重度污染,并于18日20時至19日02時均發展為嚴重污染。

圖3 2014年1月17—19日擴散輸送型各地AQI和風速風向變化
圖4給出的華東地區1月17—19日925 hPa流場圖,可以看到17日江、浙處于河套西南部高壓南伸脊SE側的弱偏北風場(圖4a)、1000 hPa弱輻合場(圖略)中,不利于空氣污染物的擴散,浙北發生大氣重污染;18日08時高壓東移南壓,伴隨冷空氣南下,江蘇、浙江兩省均為偏北風急流(圖4b),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18日20時到19日08時浙南地區處于減弱的冷高壓SE側弱風場中(地面E—NE風2~4 m/s),低層925 hPa為散度(0~0.5)×10-4·s-1的弱輻散區(圖略),有利于重污染的維持;但與此同時,北方高壓中心已經移到江蘇北部,其SE側的江蘇西南部到浙江西北部仍維持一支偏北風急流(圖8c);據江蘇省2014年1月18日和19日的AQI日平均值記錄反映,南京為349、327,持續兩天嚴重污染,蘇州為272、255,屬重污染,且1000 hPa江蘇西南部兩天偏北風風速維持8~10 m/s、杭州風速6~8 m/s;由此可以推斷,18—19日浙江北部有來自江蘇西南部的外源污染物輸入,使得浙北地區在向南輸送污染物的同時,AQI值繼續維持并發展為嚴重污染。

圖4 2014年1月17—19日925 hPa流場圖
2.2 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
我們把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定義為在一定環境場條件下,在偏北大風(浙北和浙南1000 hPa風速大于6 m/s)引導下,浙北上風方向的重污染先發地區向南輸送污染物,導致浙南地區至少兩地同時發生重污染的過程。
但分析浙北的44個重污染過程還發現,在浙北同時發生偏北大風和重污染的條件下,有二次過程并沒有發生污染物向浙南輸送,為此,我們把所有浙北發生重污染并伴隨偏北大風的過程統稱為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通過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發生時浙南發生或不發生輸入型重污染的兩類個例對比分析,進一步探討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的環境場條件。
3 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的個例統計
表1給出14個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的統計表,其中,12個為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另2個過程浙南未發生重污染;表中“輸送時段”以浙北最早出現AQI峰值及偏北大風為起始時間,浙南出現最后一個AQI峰值的時間為終止時間(若浙南在“輸送時段”未發生重污染為空,僅標明起始時間),“輸送時間”為起始時間到終止時間的間隔時數(若浙南在“輸送時段”未發生重污染為空);浙北、浙南AQI最大值分別為在重污染大風過程中浙北起始時間的最高值及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的最高值。輸送風速為浙北到浙南在“輸送時段”的最大風速。

表1 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統計表
據表1可見,發生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時,浙北到浙中南的偏北風6~12 m/s,風速越大,從浙北輸送污染物到浙南的“輸送時間”也越短,其中最短的“輸送時間”為16 h,一般情況為18~24 h;擴散型的“輸送時間”相對較長。浙南的AQI值和浙北重污染源的AQI值正相關,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時,上游的AQI值越高,浙南發生污染的AQI值也較高。
4 兩類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對比分析
圖5a、5b分別給出2013年1月11—14日(無輸送)和2015年2月4—5日(無輸送)二個未發生污染物輸送的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AQI時間變化曲線及1000 hPa杭州、溫州風向、風速圖。據圖可以看到,2013年1月13日08—20時及2015年2月5日02—08時在浙北發生重污染伴隨偏北大風過程,浙南隨后也發生偏北大風(風速8 m/s),但浙南并沒有發生污染物的輸入,AQI呈下降趨勢或少變。為了分析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發生的環境場條件,對圖2b和圖5a所示的二個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的環境場為例進行對比分析。

(a)2013年1月11—14日 (b)2015年2月4—5日圖5 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AQI變化和風記錄圖
4.1 物理理量場對比分析
1)溫度平流
圖6a、6b分別給出2013年12月25—27日和2013年1月11—14日兩個過程“輸送起始”時刻的1000、850 hPa溫度平流分布圖;據圖6,1000、850 hPa浙中南地區的溫度平流值2013年12月26日的輸送過程分別為-10×10-4℃·s-1、(-6~-4)×10-4℃·s-1,有利低層逆溫層維持;而1月13日的無輸送過程分別為(-8~-6)×10-4℃·s-1、(-10~-8)×10-4°C·s-1,低層無明顯逆溫層。

圖6a 2013年12月26日20時溫度平流分布 圖6b 2013年1月13日08時溫度平流分布
2)散度、上升氣流、θse925-700
圖7a、7b、7c和圖8a、8b、8c為分別給出2013年12月26日20時和2013年1月13日08時兩個過程“輸送起始”時刻的1000 hPa散度場、θse925-700、850 hPa垂直速度分布圖;據圖分析,2013年12月26日的輸送過程浙中南地區處于1000 hPa散度為(0~0.5)×10-4s-1的弱輻散或無輻散區、θse925-700為-15°的逆溫層、
垂直速度為(0~0.1)×10-3s-1的弱下沉氣流區;而1月13日的無輸送過程浙中南地區低層處于1000 hPa散度為(1~1.5)×10-4s-1的較強輻散區、無明顯的逆溫層(θse1000-850≥0°)、垂直速度為(0.2~0.3)×10-3s-1的較強下沉氣流區;因此,前者已經建立了有利于浙中北的污染物在偏北大風引導下向南輸送的通道;而后者的環境場不利于污染物的聚集和輸送。

圖7 2013年12月26日20時物理量場分布圖

圖8 2013年1月13日08時物理量場分布圖
4.2 浙南輸入型重污染個例的物理量統計 計算結果
據上述分析,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都是在北方高壓東移南壓伴隨冷空氣南下的天氣過程中發生的;表2給出了14個個例的850、1000 hPa溫度平流值,可以看到,所有輸送過程中浙中南地區1000 hPa的冷平流都明顯比850 hPa強,θse925-700≤0°(圖略),這說明,冷空氣主要是從近地層南下或近地層先于中低層南下,使得低層維持較穩定的層結;有利于浙中北重污染區的污染物向南輸送。而兩個無輸送過程850 hPa的冷平流都強于1000 hPa,θse925-700≥0°(圖略),低層無明顯的逆溫層。
據散度D和垂直氣流ω的計算,12個輸送個例的“輸送時段”D值為(-0.5~0.5)×10-4s-1,ω值為(-0.1~0.1)×10-3s-1,低層都處于弱輻散或弱輻合、無明顯的垂直運動;2例無輸送的浙北重污染大風過程“輸送起始”階段浙中南地區的ω和D值計算結果,ω值為(0.2~0.3)×10-3s-1,D值為(1.0~2.0)×10-4s-1,浙中南地區近地層處于較強的下沉氣流和輻散流場中,不利于污染物的聚集和輸送。
據上所述,在浙北同時發生重污染和偏北大風時,還必須具備浙北到浙南地區的污染物“輸送通道”,這個“輸送通道”為穩定層結、弱輻散或弱輻合,無明顯的垂直運動。
5 結 語
1)華東東南部地區(滬、浙、閩、贛東、蘇南、皖東南)的大氣污染高發區有兩個,分別在上海及其南部的杭、嘉、湖、紹一帶以及皖東南的馬鞍山附近;其中上海、湖州、馬鞍山為PM2.5的高值中心;贛、閩地區為低值區;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污染物都是經浙北地區在偏北大風下輸入浙南。
2)浙北向浙南的污染物輸送過程可分為兩類,即移動型和擴散型,移動型又表現為局域移動和片區移動兩種方式。
3)發生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時,浙北到浙中南的偏北風6~12 m/s,風速越大,從浙北重污染區輸送到浙南的輸送時間也越短,輸送時間為16~24 h,擴散型的輸送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上游的AQI值越高,浙南發生污染的AQI值也較高。
4)浙南輸入型重污染過程是在浙北先發重污染伴隨浙北到浙南風速增強(風速≥6 m/s)、同時在浙中南地區建立了層結穩定、弱輻散或弱輻合、無明顯垂直運動的污染物輸送通道時發生的;據此,可以把浙北發生重污染后同時發生偏北大風作為浙南發生輸入型重污染過程的起始條件,通過浙北到浙南地區低層的散度、穩定度、上升氣流及偏北風風速的分析,建立浙南輸入型重污染發生的短時預警判別模式。
[1] 徐祥德,周麗,周秀驥,等.城市環境大氣重污染過程周邊源影響域[J].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4,34(10):958-966.
[2] 陳朝暉,程水源,蘇福慶.華北區域大氣污染過程中天氣型和輸送路徑分析[J].環境科學研究,2008(1):17-21.
[3] 王艷,柴發合,劉厚風,等.長江三角洲地區大氣污染物水平輸送場特征分析[J].環境科學研究,2008,21(1):22-29.
[4] 李懷川,陳宣淼,葉子祥,等.浙江省重度空氣污染過程時空變化特征[J].氣象與環境學報,2017,32.
[5] 任陣海,蘇福慶,高慶先等.邊界層內大氣排放形成重污染背景解析[J].大氣科學,2005,29(1):57-63.
[6] 李德平,程興宏,于永濤等.北京地區三級以上污染的氣象影響因子的初步分析[J].氣象與環境學報,2010,26(3):7-13.
[7] 張睿,蔡旭暉,宋宇.北京地區大氣污染物時空分布及累積效應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40(6):930-938.
201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