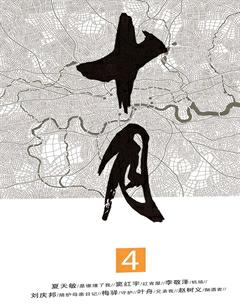卷首語
2017-07-27 19:05:13
十月 2017年4期
關鍵詞:文本
“糾結”無所不在,既在生活中,也在靈魂里,更在歷史中。本期夏天敏的中篇小說《是誰埋了我》就很糾結,主人公活著的時候就被埋葬了,那是個衣冠冢卻享受著英烈的殊榮。但在圍殲山匪的那次戰斗中,他卻不幸成了遺留戰場的唯一幸存者。被虜獲的屈辱、與匪首女兒的糾葛,成了他的心病;即便帶領部隊剿滅匪徒,也無法令他釋懷。但更難以直面的,是那座墳冢。受之有愧的榮耀,比不正當的感情,更加讓人飽受折磨。
短篇小說《兄弟我》,則牽涉一座高塔的拆除與遷延。已丟失其功能屬性、矗立五十余年的高塔,如今破舊多余,甚至與周圍環境顯得格格不入。但是一群老人奮起抵抗。高塔不僅是他們青春年華綻放的見證,也是他們心存感念的某位無名者的一座紀念碑。
劉慶邦的散文《陪護母親日記》,有明顯的文本開拓,而且顯然很成熟。它既沒有被日記規范,也沒有被母親養病局限。陪護的人在改變,治病的空余被交談和回憶充滿。時間在當下與過去之間自由穿梭,空間在病房與家鄉之間輕松轉換。各色人等在講述中紛紛登場,然后從容或倉促謝幕。文本因此具備一種似乎無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種復雜多變的開放性。
猜你喜歡
云南教育·小學教師(2022年4期)2022-05-17 14:46:24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藝術評論(2020年3期)2020-02-06 06:29:2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18年11期)2018-12-29 12:30:5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語文知識(2015年11期)2015-02-28 2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