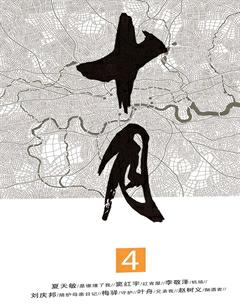秀姑
鐵揚
一
秀姑有個綽號叫張小勇,因為先前她演過一出叫《張小勇參軍》的戲,她演張小勇,我姐姐演她的家屬,那時她們都是十四歲,都是當地抗日小學的學生。那年八路軍打了大勝仗,拿下附近一個碉堡,晚上慶祝演戲,抗日小學的學生對抗日軍民的活動一向積極。
這天晚上,在敵人破敗的碉堡前,掛起幔帳,點起汽燈,秀姑和我姐姐在汽燈下出場,她們演的就是張小勇參軍。她們自編自演,由一首《丈夫去當兵》的歌曲改編而成,劇情是張小勇出發前妻子送行的情景。秀姑個子矮,春天還穿著家做的棉褲棉襖,像個棉球,她頭包一塊羊肚手巾,胸前戴朵大紅花。我姐姐個子也不高,穿件花棉襖頭包一塊三角頭巾,懷里抱個小枕頭,那是她們的孩子。
秀姑先出場,站在臺上念開場白:“我叫張小勇,家住在村東,政府號召參軍去,我小勇提早報了名,今天出發上前線,孩子娘非要送一程。”
我姐姐懷里抱個小枕頭出場,邊走邊喊:“當家的等等我啊。”她追上了丈夫張小勇,然后夫妻二人就在臺上轉圈,邊轉邊唱邊說。
我姐姐唱:“丈夫去當兵,老婆叫一聲,貓兒爹你等等我,為妻的將你送一程。”
秀姑說:“不用送了,恁娘倆別叫風吹著。快回去吧。”
姐姐唱:“丈夫去打仗,女子守家庭,你在前方打得好,我在家中把地耕。”
秀姑說:“從今以后咱家是抗屬,有人給咱代耕,有困難政府給解決。”
姐姐唱:“可惜我非男子漢,不能隨你投大營。”
秀姑說:“哪有帶著家屬打仗的,打完仗我就回來了。”
姐姐唱:“幸喜你今扛槍走,一鄉之中留美名。”
秀姑說:“你這是娘們觀點,咱不為落個好名聲,就為打敗日本。”
……
那天秀姑演戲,以她女扮男裝的打扮,和她那出口成章的鄉音,給鄉親帶來了無盡的歡笑,自己也落下了一個張小勇的綽號。
二
“張小勇”第二年真的參了軍,在軍區后方醫院做了一名衛生兵,后來仗打完了,她沒有回鄉,開始在解放區隨軍隊四處轉移,每到一處就有信寄回來。她的信要寄到我家,讓我父親念給她的家人。秀姑的家人不識字,都是勤勞度日的莊稼人。秀姑參軍前也跟家人一起勞作,她小時就會紡線,坐在紡車前還不及紡車高,晚上她和母親在炕上守著兩架紡車,只紡到雞叫。她們把紡成的棉線拿到集上賣,換成小米,買回棉絮再紡。后來秀姑上學也要兩星期回一趟家,背小米交伙食。我姐姐和秀姑常背著小米偷過敵人的封鎖線,有一次敵人的子彈還打穿了她們的口袋,小米撒了一地。
我父親接過秀姑的信看看說:“這張小勇現時在鄚州,這地方還屬冀中,離河間府不遠。”有時就說:“這張小勇又到了石門橋。”一次我父親拆開信封發現信封中還有另外的物件,那是一個扣子大的小紙包,里邊有一點兒白色的顆粒。原來秀姑在信中有說明,她說紙包里的東西叫糖精,這一小包能頂二斤白糖。我父親對我娘說:“這可珍貴,糖精這東西只聽說過,還沒見過。明天蒸餅子取兩粒試試吧。”我娘取了兩粒,用水化開拌在面里,蒸出的餅子家人都搶著吃,我從來沒有吃過這么甜的東西,現在想來還覺得再甜的東西也甜不過糖精。
三
一年之后,秀姑由八路軍變成了解放軍,她穿當時的制式裙裝,戴一頂大沿帽,進駐保定。此時我也是一位穿灰制服的文藝界學生,星期天我們約好在保定蓮池見面。現在的秀姑和當時的張小勇相比,好像沒有長多少,制式裙裝穿在她身上像個半截水缸,大沿帽在頭上也哐當著,看到我像見到親人,問我吃飯能吃飽嗎,被子夠不夠蓋,夏天有沒有蚊帳,津貼夠不夠花。說時從一個軍挎包里摸出一管黑人牌牙膏,交到我手中,我推辭說有,秀姑還是把牙膏狠狠摁在我手中。她說她在軍區醫院當司藥,住在西關的斯羅醫院,部隊比地方供應充足,有困難就找她。中午,她領我去天華市場吃炸糕,我便想起她寄糖精的事。我說炸糕可趕不上用糖精蒸的餅子甜。秀姑告訴我說,糖精可不是糖,是瀝青的提取物。當時根據地困難,有時發一包糖精當糖吃。可別多吃,還有副作用呢。
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考入北京一所藝術大學,秀姑也去了北京,她上的是工農速成中學,校址就在沙灘北大紅樓。那時她已結婚,在學校是一位挺著大肚子的學生。星期天我到她家中看她,她挺著肚子朝著我說:“見過這樣的中學生嗎,準沒見過吧。挺著肚子也得上,憑老家那點兒文化可不夠用,光會給你姐姐編個張小勇參軍,詞不達意的。在紅樓上中學,跟不上也得跟,建設新中國得提高文化。”她強調著建設新中國五個字,說得刻板但認真。
我站在秀姑對面,卻又想起張小勇的樣子,那時張小勇在臺上像個棉球,現在看到肚子圓圓的秀姑又想起張小勇。
五
秀姑完成了在紅樓的學業,也生了女兒,再見她時,她是某醫學院的本科生,那天她剛燙了一頭卷發,看到我,她雙手捂著頭發說:“后悔死了,后悔死了,我可不適合改模樣。”
對秀姑的改模樣,我也覺得不改也罷,我拿張小勇的形象和燙成彎彎頭的秀姑做比較,覺得彎彎頭的秀姑失去了張小勇式的自然。
六
秀姑又變成了一頭直發,那時這種發式叫青年頭。她在北京一個研究所做機關醫生,憑著她的好人緣,身邊常聚集著有病和沒病的同志姐妹,說著疾病以內和疾病以外的話。
好脾氣的人,性格中往往會表現出處事時猶豫不定。我去看秀姑,她端著一個碗正在攪拌著碗中的一點兒肉餡,見我來了,高興地說:“有肉餡,咱們包餃子吧。”我說:“好吧,咱們一塊兒包。”肉餡在她手下繼續攪拌著,她想了想又說,“肉餡不多,咱們包餛飩吧。”我說,“好吧,餛飩也行。”秀姑遲疑片刻又說:“包餃子吧,也許夠。”我說:“還是包餃子吧。”秀姑又說:“還是包餛飩吧。”……
秀姑對于餃子和餛飩的換算給我留下了終生的印象,現在想想,我們到底是吃了餃子還是吃了餛飩。我也總在換算。
秀姑離別我們那個冀中平原的村落,參軍、進城、中學、大學都經歷過之后,但鄉音未改,還是操著一口地道的方言,把“告訴”說成“遞說”,把你說“恁”,把我說“俺”,她對我說改掉方言好像就不是她自己了。
遞說恁吧,包餃子也許夠。
七
秀姑以她的好脾氣、好人緣走遍天下都暢通無阻。
又過了些年,我已是一位畫家,常背著畫具四處游走,路過北京時總要去看望秀姑,秀姑看到我,若是一位饑餓的我,她就會領我去食堂吃飯,食堂若已關門,她就砰砰敲門,喊著:“老劉老劉,吃飯吃飯,開門開門。”食堂師傅一看是秀姑,就會把門打開,不久或菜或飯就會端上來。我若是風塵仆仆,她就會領我去樓下公共浴室,浴室關門,她就會砰砰敲門:“老宋老宋,洗澡兒,洗澡兒。”老宋開門一看是秀姑,就會把門打開,把熱水放出來。
八
鄉人還是把秀姑看成當年的張小勇,同齡人叫她勇姐、勇妹,隔輩人叫她勇姑,也有喊她勇奶奶的孩子。
張小勇回了村,背個軍挎,提個提包進了家門,村人涌進來,都知道張小勇現時已是一位北京“名醫”,他們涌進院子,不顧秀姑路途的勞頓,爭先恐后開始述說自己的病情。
“勇姐,疼得直不起來。”一位大媽拍著自己的腰。
“勇姑,咳嗽不止,一黑介一黑介睡不著。”一位大嫂說。
“他勇奶奶,這孩子的痄腮生是回不去。”一位老奶奶領著一位男孩。
發燒的、發熱的、看不清的、聽不準的……
秀姑不顧自己的勞頓,顧不得進屋,拉開提包拽出一個出診包,操著鄉音開始給患者施治。
“來,褪下袖子,扎個針兒。”她說。
“來,這兩包小藥,先吃這包,后吃這包。”
“老風寒,給你一貼膏藥,烤熱了再貼。”
“痄腮不能光吃藥,要忌響器,遇到敲鑼的打鼓的,趕快讓孩子躲開。”
……
秀姑在醫學院學西醫,但她也準備下中醫乃至民間許多診病方式。針灸、拔罐、推拿她都會。也因此更加得到鄉人的尊重。
九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十多年沒見秀姑,由于在美國定居的子女需要,她去了美國。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她喊著我的小名說:“回老家看看吧,回老家見個面兒吧。”我按著她的要求,回老家和她見了面,她拉住我的手說:“看你姑姑吧,越來越矬了,還不如當年的張小勇高。”秀姑的腰向一側彎著,表情中明顯地在忍受著什么,顯然是腰疾正在折磨著她。
秀姑回老家是來求醫的。她說老家有“能人”用偏方能治腰疾。一個對于生理病理都精通的專業醫生,竟然不遠萬里來鄉村僻野求醫,這本身就很引人思索,難道鄉間真有這樣的能人?這時我突然想起那年秀姑面對一點兒肉餡,做出的對于吃餃子還是吃餛飩的不停換算,這就是秀姑的性格吧。這是一個好人式的、質樸的、一時缺少主意的換算。
秀姑扶著我坐下來,說了些域外域內的瑣碎,當然她也科學地表示了對這次求醫的看法,有病亂投醫吧,她說。她說她愿意回來,愿意用鄉音自然而然地和鄉親說說話,這才是她回鄉的初衷。
十
當然,鄉間僻野的能人終沒有讓秀姑的腰直起來。
又過了十年,我來到美國看秀姑,她住在美國西海岸一個宜人的養老院里,對于子女對她的安排,不時向我表示著滿足,她說:“孩子們忙,照顧不了我,你看,”她指著房內房外的一切,“可好哩,從二樓下去出一個門還有一個院子,有草坪。屋里還有冰箱,里面什么都有,這里晚飯吃得早,晚上餓了,拉開冰箱吃點兒水果、面包……”秀姑還是操著鄉音向我介紹著這里的一切,表示對眼前的滿足,我想,就她的年紀和狀態,這確是一個好去處。論年紀,她已是一位八十大幾歲的老人,而她的腰更加彎,胸也向一側偏著,在屋內扶住可扶的東西,才能移動自己,出門時要靠一輛輪椅或推或坐。但她要努力證明自己還是一位健康老人。
這天,家中的熱心晚輩開車要帶我出去走走,秀姑堅持要同去,我們幫她走出門,扶上車,一路上她向我介紹這里的一切。她指著一個公交車站說,從前她常在這里乘車,或去超市或送晚輩上學。走過一座建筑,她說這是圖書館,先前她常乘公交車在此看書。她說他們有個老年華人群體,常在一起聚會唱歌……說時臉上流露出對車窗外生活的無限眷戀。
秀姑喜歡照相,在她居住的房間里就擺滿各種大小照片,家人的,友人的,自己的。她把自己最滿意的放大照放在房間最重要的位置。那時的秀姑容光煥發,披著五彩披肩,笑得燦爛。現在秀姑不斷讓晚輩停車照相,在她認為可做留念的景致里。她扭過身子對我說:“來,照張相。”我們從車上走下,再把她扶下,擺個合影的姿勢。果然,這是秀姑最愉快的時刻,她努力站直,面對鏡頭每次還會發出咯咯的笑聲。在美國,這只能是一位熱愛生活,對生命還有著無限眷戀的中國老人發出的聲音。秀姑咯咯笑一陣,還會提醒我們:“都笑,都笑,要真笑。”秀姑的笑是真笑,不加帶任何表演,真實得還會使你想到家鄉,只有在中國、在冀中平原一個村子里,才能聽到這樣的笑聲,它真實、清澈、悠遠,也是純中國式的。
離開西海岸時,我去和秀姑告別,我把我的一本散文集送給她,還告訴她從中國帶來的小米放在了家中(這是秀姑要求我帶給她的),秀姑顧不得翻書,迫不及待拉開她的冰箱,搬出些水果、點心,掰下幾根香蕉讓我吃,她說,我住飯店準吃不好。又囑咐我一些旅行常識……分別時,她一定要推車出門送我,她彎腰扶車通過一個長長的走廊,每走過一個窗子,就把她的院子指給我看,還為我沒時間參觀院子而遺憾。
上午十一點,正是老人們用午餐的時間,走廊里排列起許多坐在輪椅上的域外老人。老人們都很在意自己的衣著容貌,極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這倒顯出秀姑在衣著上的隨意,她不在意這些。當她扶車從他們身邊經過時,不忘把我介紹給她的美國同伴,每走到一個人前,她就會把我介紹出來說:“這是我個侄子,從‘柴納來。”她說得鄭重豪爽,極力強調這兩點,“侄子”和“柴納”。
“柴納”,這是我在美國聽秀姑所說的唯一英文單詞。“柴納”,這當是“CHINA”。而她說“柴納”像家鄉人說柴火。
大約一個月后,我從美國東海岸回到中國,撥通了秀姑的電話,告訴她我已平安回家。秀姑在電話里告訴我,我送她的小米只能在周末回到親人家中時才能熬一次粥,說她住的地方沒有粥鍋。還告訴我她正在看我送給她的散文集,說了幾個她感興趣的章節,然后問我,書里為什么找不到她,她還演過張小勇參軍呢。說著咯咯笑著,還哼唱起:丈夫去當兵,老婆叫一聲……
201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