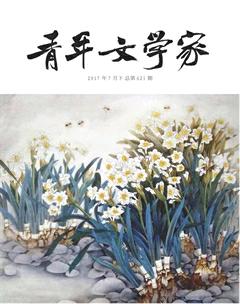家書與家風
王德生
書信是人們學習、工作、生活,以及社會交往中廣泛使用的交際、交流思想的工具,在人們的社會交往和思想感情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古人稱書信為尺牘、尺素、書札、書牘等。家書又稱家信,鄉書。在電報出現之前,家書是維系身在異地的家人情感的主要溝通方式,一封家書飽含著濃濃的親情。家書可以給遠方的親人報平安、送去問候、送去祝福、傳遞消息。家書對親人來講是十分珍貴的,杜甫的《春望》中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充分說明了在古代,特別是動亂的戰爭年代,一封報平安的家書對遠方親人的思念、牽掛的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傳遞家書大都通過托付私人捎帶,民間通信極不方便。直到明代才出現專門辦理民間信件傳遞的民信局,第一家民信局出現于當時商業最發達的浙江寧波,后來逐漸出現在各大商業城市。清代家書發展到了高峰。最有名的莫過于《曾國藩家書》,曾國藩在寫給兒子紀澤、紀鴻以及諸弟的家書中,涉及內容極為廣泛,小至人際瑣事和家庭生計的陳述指點,如交友和旅游等內容,大到進德修業、治國安邦之道的闡述,如用人、修身、學習、理財等內容。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從《曾國藩家書》中汲取工作、學習、生活的知識經驗。
老一代革命者的家書中透著家風,既有普通人普通生活的生活情感,更透革命者以身許國的家國天下情懷。“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在培養良好家風方面,老一輩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其中家書是他們和家人的情感紐帶,更是傳承家風的重要載體。翻閱他們的家書,那泛黃的信紙上既有對革命事業的激情和信仰,亦有對愛人的叮嚀囑咐,對子女的諄諄教導。透過歲月的洪流里永不褪色的先輩的家書,感受他們的敦厚家風,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追溯信箋背后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遷。周恩來于1942年9月寫給鄧穎超的家書中寫道,“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黃昏,月已東升,坐在一排石窯洞中的我,正好修寫家書寄遠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澇,直至前天還是陰雨連綿,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望收到二成左右。河東來電,亦說是淫雨不止,不知你們那里的情形怎樣?山居過節,居然也吃到兩塊月餅,幾串葡萄。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做農村訪問,那你一定是忙著和農家姑娘姊妹談心拉話;假使你正在準備下鄉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與工委一起過一個農村中秋節。不管怎樣,一切話題總離不開土地改革和前線勝利。九個年頭了,似乎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中秋的,這次分開,反顯得比抗戰頭兩年的分開大有不同。不僅因為我們都大了十歲,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為人民服務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你來電提議在東邊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贊成。再多在農民中鍛煉半年,我想,不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會起更大的變化,就連你的身體想也會更結實而年輕。農民的健美,不僅是外形,而且還有那純樸的內心,這是一面。另一面,便是堅強,堅定的意志,勇敢的行為,這在被壓迫的群眾中,更是數見不鮮。你從他們中間自會學習很多,只要不太勞累。我想半年的熏陶,當準備刮目相看……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著余興送我入夢。愿你安好。”從周總理的家書中,我們讀到了丈夫對妻子的思念牽掛,讀到了老一輩革命家深沉的人民情懷,讀到了偉大革命者的家國天下的胸襟。家書中傳承著崇高的家風。
爸爸說,我們家的家風是“忠厚傳家遠,詩書濟世長”。我知道,爸爸從小和爺爺奶奶生活在農村,養成了勤儉、忠厚的家風和生活習慣,也渴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承載著要好好讀書學習本領、長大改變貧窮落后的農村面貌、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老一輩人寄托的樸素愿望。爸爸當年離開家上高中和大學讀書時,那時還沒有手機,除了緊急時可以通過郵局發電報外,基本上也是每月要互通家信的。爸爸堅持每月給家里寫一封信,寫自己身體很好勿念,寫學習情況,寫學校生活,寫對家的思念,寫對父母的牽掛。奶奶識字不多,每次來信就讓爺爺念,然后聽了一遍又一遍,自己看了又看,然后每一封信都小心地收好。每次爺爺給爸爸寫信,奶奶都在一旁又是叮嚀又是囑咐。如果哪個月沒有按時收到兒子的來信,就輸的日子盼著,念叨不停。一封封家書承載著對家人的濃濃思念,一封封家書承載著醇厚質樸的家風家訓,一封封家書承載的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一封封家書架起了兩代人之間的情感橋梁。
隨著現代手機、電腦、e-mail等科技產品的出現,親人、朋友之間的書信聯系越來越少,大多通過短信、微信等發送接收消息,但仍有一部分人情愿使用書信來互通信息。前一段時間讀了一本書,臺灣作家龍應臺和他的兒子安德烈合著的《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寫的是母親工作在香港,兒子在德國長大,由于母親與兒子安德烈年齡的差距、生活經歷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兩代人、兩個文化的人之間的鴻溝無法通過面對面的語言溝通,通過互相寫信來溝通思想、感情的故事。“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臺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棱角分明,眼神深沉寧靜,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里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的看著你。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里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發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我走進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聊天,他說,談什么?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說什么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它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歡什么討厭什么,他為什么這樣做那樣做,什么使他尷尬什么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假期會面時,他愿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于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母子之間語言溝通幾乎沒有什么用武之地了,于是母親和兒子共同決定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一寫就寫了三年,三年的家書如同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額懷。“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漂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信息化電子化時代,家書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他們使人們慢下來、靜下來,傾聽內心深處的聲音,他能使我們在字里行間讀著彼此的精神世界,他能使我們互相安靜下來互相凝望對方的思想、了解對方的情感。家書架起了兩代人之間溝通的橋梁。
到了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幾乎普及到每個家庭生活中了,人們工作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們越來越忙碌奔波,人們通過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微信等相互進行實時溝通,更加快捷方便,很少有人能靜下來寫封信了,如果有一天能夠讀到一封手寫的家信似乎更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情了。伴隨著人們生活了幾千年的家書會漸漸地消失嗎?我們還能夠細細地品味到家書中的溫暖的情感嗎?忽然想起前不久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話,讓我們放慢腳步,等一等我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