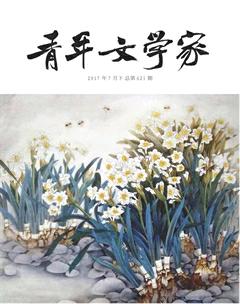戰火烽煙中的清新俊逸之花
摘 要:主要從風景和風俗畫的描寫、人性溫度的自然回歸、別具一格的審美取向,三個方面來分析的《百合花》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與成功。挖掘出作者對當時“規范化”創作的成功與突破,以及對后來者思考和借鑒的價值。
關鍵詞:《百合花》;文學史地位;突破與成功
作者簡介:楊程(1993.2-),女,漢族,遼寧省鐵嶺市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1-0-02
引言:
1953年,第二屆全國文代會正式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樹立為當時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最高的價值準則。同時,和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原則互文伴生的是對于現實主義創作的幾近于束縛式的規約。作為當時文壇占據主導地位的革命歷史小說尚且囿于既定的創作范式的束縛,更遑論詩歌、戲劇等其他文學體裁的作品了。但是正是在上述各種條件和范式的約束和限制之下,茹志娟的小說《百合花》卻能夠通過人物形象的自然回歸,對朦朧隱現的情感線索的細致勾勒,以及對于清新淳樸的鄉土風景的開掘,從而在十七年革命歷史文學的百花園中占據了它獨具一格的地位。
一、風景畫與風俗畫的摹寫
雨后的殘露、行將成熟的莊稼、混雜著泥土清香的百味迎面撲來,使讀者轉瞬之間仿佛置身于這鄉間小路,在視覺、聽覺和觸覺的交互作用下,與陶淵明“夕露沾衣,帶月荷鋤”的意境頗有同工異曲之妙。在短暫的風景描畫之中,使讀者也暫時忘記了主人公所處的是戰爭環境,小戰士所要奔赴的是可能生離死別的戰場。這副田園風光圖既是作者為讀者營構的畫卷,但何嘗不是為即將為革命獻出年輕而寶貴生命的小戰士的所發出的深刻的惋惜與喟嘆呢。如果說風景畫讓讀者得以獲得戰爭間隙的寬余,那么,風俗畫的植入則可以看出作者的深層次寓意。
中國現代文學自誕生以來鄉土小說就呈現出蓬勃的生命力,經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壇巨擘在鄉土小說的創作與理論規范層面的不懈努力,鄉土小說得到了長足發展。但是在十七年文學期間,鄉土小說的發展逐漸被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文學規范所限定。縱覽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丁帆所歸納的鄉土小說所賴以存在的根基即風景畫和風俗畫幾乎趨近消失。鮮明的革命話語取代了鄉場酒館中農民的談天交際,曾經作為被啟蒙者的農民成為了革命的積極參與者,絢爛多彩的鄉風民俗徹底淪為了革命戰爭的背景。推而廣之,這一現象在建國以后及至文革結束期間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為在突出文學的宣傳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教化的特殊時代,無論風景畫抑或是風俗畫都是脫離了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與英雄塑造的中心任務的。所以在同時其作品中,我們所熟知的是對于風景畫與風俗畫的徹底拋棄。但是,試問如果當文學作品徹底脫離了風景畫與風俗畫的范疇而徹底滑向單一的敘事模式以及人物塑造,則小說還能夠繼續煥發出足夠的生命張力嗎?答案不言自明。而茅盾在《百合花》發表后不久即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對其進行高度的肯定的評論文章,并將《百合花》的風格歸納為清新俊逸。而通過閱讀作品,作者對于當時同類作品中所稀缺的風景畫的書寫無疑是其打開清新俊逸之門的關鍵鎖鑰。
二、人性溫度的自然回歸
在《百合花》中我們首先關注到的是兩位女性,即“我”和新媳婦。在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中,為了使人物形象的塑造配合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恢宏壯闊的歷史化畫面,所以形成了女性形象逐漸趨向于中性化的結果。作為《紅色娘子軍》中的隊長,吳瓊花的名字就曾在60年代強調英雄的時代里被更改為“吳清華”,當時改名的理由竟然是瓊花過于女性化,會影響到英雄形象的塑造。所以在十七年文學中我們會看到漸趨與模糊了性別特征的女性形象,同時也逐漸向著“高大全”的方向邁進,進而造成了對人物本應具有的喜怒哀樂的有意識忽略和遮蔽。但是當我們把視線聚焦到小說中對于我的刻畫,則首先會驚喜于“我”的女性特征的回歸。“我”作為新加入革命隊伍的戰士,在和小戰士的接觸中由于自己的年紀大于小戰士,所以我們看到了“我”并沒有普通女性的羞澀,相反卻能夠展露自己的老練和細心來面對小戰士的好奇和羞澀。同時,當時“我”曾“索性不走了”,而且還詢問小戰士“娶沒娶媳婦”,在這轉瞬即逝的動作和語言中,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女性身份下,“我”的微笑,我的撒嬌甚至于是對小戰士的革命戰友間特有的玩笑方式都讓讀者可以確定作為革命者之上的“我”是一個具有了普通人所有情感的女性,從而讓革命者由遙不可及的高大上回歸到觸手可及、親切可感的平實溫暖。
作為肩負著實現歷史經典化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以對歷史本質的規范化敘述,為新的社會真理性作出證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動對歷史的既定敘述的合法化,也為處于社會轉折時期的民眾,提供生活準則和思想依據。”從洪子誠的論述中,我們不難尋覓到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在創作中所受到的題材、主題以及情感基調的先入為主的束縛。基于這一系列的創作要求的要求,所以在作品的人物塑造中盡管為文學史銘刻了眾多可歌可泣、高大偉岸的英雄形象,但是不可否認,當一種文學范式成為一類作品的創作模式,一類人物成為可以“克隆”的文學符號后,文本的同質化以及人物的臉譜化就會成為必然的趨向。故而當我們回顧十七年文學中經典文學人物時,就會得到一個早已形成的共識:這一時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文革中所形成的“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是有著密不可分的呼應關系的。因此我們在品讀《百合花》時,首先看到的是從人物的塑造中人性化的回歸,在前沿包扎所得兩位女性和一個小戰士的言行中,讓讀者找尋到了同時期同類作品中難得一見的真實的人性和人情。
三、別具一格的審美向度
自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開始,面對著日益加深的民族國家危機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愛國熱情所展現的時代風貌,眾多作家們也緊隨時代的脈搏,用自己的筆為國家民族和人民鼓與呼。所以我們看到了以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在文學作品中對于時代的介入,對于革命的參與。可以說這種文學為現實服務,換言之,就是為革命服務的傳統直接被建國以后的十七年文學所繼承,甚至逐漸向“高大全”的方向傾斜。不可否認,文學對于革命的深度介入對于當時的革命進程和社會建設起到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物極必反,當革命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發展到十七年文學時期時,文學的已經逐漸失去了自身的審美作用與維度,完全從屬于政治,甚至成為了政治的傳聲筒。故而當我們在回顧十七年文學的革命題材類作品時會發現作品中審美趨向的高度的同質化,而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到“文革”時期的文學會徹底走入極端化的死胡同。但是茹志娟的《百合花》在當時單一化的文學審美規范之下對于清新俊逸的語言的運用和對人物情感的內斂的表達卻從審美上實現了突破。
茅盾曾經在評論《百合花》的文章中稱贊其風格為清新俊逸,筆者認為這種清新俊逸如果從單一的維度界定,那么其語言的俊秀清麗則首當其沖。在《百合花》中,故事的背景設置在一個鄉間村落,而且正值前線激戰正酣,如果按照當時的常規文學的描寫方式,那么《紅旗譜》和《林海雪原》式的戰斗描寫語言無疑是最佳范本。但是當我們品味作者的用筆時,卻體悟到了作者的匠心獨運。如果說語言的清新俊逸是形而上的可觸可感的有形的媒介,那么對于人物情感的恰到好處的“含而不露”則在情感意義上為小說的審美提升了檔次。在同時期的革命英雄主義題材作品中,存在著一個普遍的特性,那就是對于人物情感的平鋪直敘式的描寫。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英雄形象的樹立,但是這不可避免地要傷害到人物形象深度的開掘。而《百合花》在創作中顯然是有意識地回避了讓人物的情感過分外露,而是“壓著寫”,在內斂的情感交流中實現了審美的升華。
作為主人公,小戰士似乎有別于傳統的革命英雄的義正詞嚴和慷慨激昂,甚至有羞澀和靦腆的特點,但是通過仔細梳理線索,我們可以看到,小戰士的靦腆是建立在和異性的談話中,同時他的年齡也十分符合作者對于他的性格設定,這就保證了人物形象的真實。同時,雖然小戰士在借被子的過程中羞澀靦腆,但是最終犧牲在前線陣地的結果已經充分說明了他在戰斗中的英勇和果敢,這與平時的性格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未點破而效果鮮明,達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而這一切都來自于對人物情感的內斂式描摹。綜上所述,《百合花》真正實現了在同時期作品中的審美向度。
參考文獻:
[1]李云霞.宏大敘事下的抒情詩從百合花看茹志鵑小說創作風格,河北建筑科技學院學報(社科版)。
[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