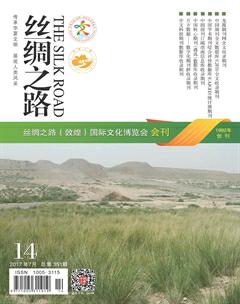從主人公五龍的形象看蘇童《米》的新歷史主義特質
王丹藝
[摘要]大約從1987年到1992年,中國新歷史主義小說發展到了全盛時期。這一階段的作品,歷史縱向的流程被碎片化、空間化,顯現出“超越歷史”“寓言化”的特征。蘇童小說《米》是新歷史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本文將從小說的主人公五龍的人物形象分析入手,簡單解讀《米》這部小說所體現出的新歷史主義特質。
[關鍵詞]蘇童;《米》;人物形象;新歷史主義
[中圖分類號] 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7)14-0050-02
《米》的創作完成于1991年,作為中國新歷史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鮮明的新歷史主義風格。新歷史主義是對傳統歷史觀念的顛覆和解構,認為歷史只不過是某種話語的呈現、文學的敘述,不存在所謂的“歷史真實”。新歷史主義小說拋棄了舊的“主流歷史小說”常用的意識形態視角、政治化話語、簡單二元對立的立場,試圖用民間化、個人化的眼光審視和探尋歷史,展現歷史的細節和被忽視的角落,敘述可能與主流話語相悖的個人的經歷;甚至虛構某種歷史的背景,進行寓言式的陳述,表達某種隱喻的意味。
蘇童在《急就的講稿》中寫道:“《米》。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1990年冬天寫到1991年春天。朋友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遠離作者本人的故事。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對人及人的命運中黑暗的一面。這是一個關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毀滅的故事,我寫了一個人具有輪回意義的一生,一個逃離饑荒的農民通過火車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過火車回歸故里,五十年異鄉飄泊是這個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歸鄉途中又是整個故事的高潮。我想我在這部小說中醉心營造了某種歷史,某種歸宿,某種結論。”這段自述精確地概括了《米》故事的內核。作者并非只是簡單地講述某個歷史背景下一個人的經歷,主人公的故事是超越了時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作者通過對五龍的生活經歷的描寫,展現的是永恒的、根植于人性的問題。
一、漂泊:精神的孤兒
五龍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鄉村和城市都無法給他的心靈以歸屬感。他從鄉村中來,卻無法再重返鄉村;他想要融入城市,卻始終沒有被城市真正接納。看似獲得了權勢地位、財富和女人,卻始終是一個漂泊的靈魂,找不到心靈的歸宿。長久以來鄉村和城市常常以二元對立的姿態出現,二選一似乎是必須的,而五龍的形象卻揭示了兩者之間還存在漫長的過渡部分。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迷失于路途上的人并不在少數。
五龍對于鄉村的背離,是被動的、被迫的,一場席卷家鄉楓楊樹鄉村的洪水,將他驅趕到陌生的、令他驚惶的城市。初入城市,他所遇見的那個凍死在碼頭的逃難者,似乎已經暗示了他的命運和結局。城市給他的當頭棒喝,便是精神上的壓迫和屈辱,他為了滿足生存最基本的對食物的需求,叫了碼頭伙計阿保一聲“爹”。此時他已經被迫放棄了鄉村的精神之父,轉而被城市的威權所壓制,但城市又無法成為他的心靈依靠,他的精神從此開始無盡的流浪。不管他如何努力占領城市,奪得話語權,城市都無法容納他,他也無法與城市和解。
已然在城市立足的五龍仍舊有著揮之不去的漂泊感,從鄉村到城市的旅程在他腦海中反復重現。強行占有綺云是他對征服欲和性欲的滿足,但“他覺得身下的米以及整個米店都在有節律地晃動,夢幻的火車汽笛在遙遠的地方拉響,他仍然在火車上,他仍然在火車上緩緩地運行”。此后多次在獲得某種證明之時,他總會感到自己仍在火車上顛簸,聽到鐵軌的碰撞聲、汽笛的轟鳴。即使取得了成果而想要求得認同,對于城市,他永遠都是一個游客,一直在路上而無法真正到達。
五龍在城市打拼,一步步向上爬,占據財富、地位和女人,這個過程中他始終是割裂的。他的肉體駐扎在城市,靈魂卻沒有離開鄉村。征服城市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終極追求是回到鄉村,帶著他征服城市的戰利品——米,作為最初因為食物需求而被迫離開鄉村的補償。但最終的回歸沒能真正完成,他腐敗的肉身被拋棄在半途中,財富地位散盡成空,終其一生對故鄉的眷戀和執著,也未能隨著米被帶回鄉村。
二、欲望:食、性、財與權力
在蘇童的新歷史主義小說中,欲望常常被描述為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欲望也是五龍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詞,他的行為受欲望的驅使,不同程度的欲望劃分了他生命的不同階段,最終也因欲望而墜入深淵、自我毀滅。
五龍走出鄉村,帶在身上的只有一把家鄉的米;被大鴻米店收留,自此開始占領和報復城市的行動;染病生命奄奄之際,最后的愿望是拉一車皮的米回到故鄉,一生都與米糾纏不休。“米”的象征意義有很多層次,在五龍的欲望一步步膨脹、升級的過程中,“米”始終與之相聯系。
米從鄉村的大地中生長出來,純白而干凈,未被城市污染,它是五龍與鄉村維系的紐帶,是關于家鄉的原始記憶。在五龍最初進入城市時,它代表著食欲,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五龍被迫走出鄉村的原因是它,留在米店開始城市生活的原因也是它。所謂“飽暖思淫欲”,在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之后,五龍的欲望開始向更高級別發展。食欲被滿足,米又與性欲聯系在了一起。五龍開始有了一種怪癖,在看到米時會產生更強烈的性沖動,與女人做愛時要拿米塞進她們的下體。他以米來宣告對女人的征服和占有,同時也是對城市的占領和示威,潛意識中,更是想以鄉村反撥城市,凈化城市的污濁,留下純潔的種子。在獲得了財富和權力之后,米也成為了五龍欲望的戰果的代表,寄托著他對鄉村持久的追憶和回歸的渴望,帶著一火車皮的米榮歸故里,成為了他人生的究極目標。
五龍將自己的牙敲掉換成金牙,象征著他征服城市、追慕財富和權力的過程中對自我的舍棄。他在欲望中沉浮,輕易就丟失了自己,他利用欲望,也被欲望反噬,以至于最后在泛濫的性欲和征服欲中染上性病,導致了自己生命的終結。財富和權力是實打實地存在的,但對它的占有卻是暫時的、虛假的,五龍在生命消逝、身體腐爛之時,自然地脫離了與它的聯系,被兒子全部奪走。這樣的結局,頗為諷刺也十分悲涼。人的欲望無窮無盡,生命終結之時,曾經的擁有就成了一場虛空,欲望的滿足究竟有什么意義,又代表著什么,是人類面臨的永恒的問題。
三、仇恨:“惡”的純粹展現
《米》的故事里充斥著仇恨和惡意,整個行文籠罩在陰冷而黯淡的氛圍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仿佛總是冰冷而淡漠,親善與溫情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利益關系和權力壓制,在這樣一種極端的狀態下,人性的丑惡與變態被凸顯出來,構成了一個“惡”主導的世界。
驅使五龍在城市里從一個米店伙計最終成為一方惡霸的一個直接動力就是仇恨。在最初進入城市之時受到阿保的羞辱,使他始終對城市抱有敵意和惡意。五龍對權力和地位的追求、對城市的占領和征服,其實是一種兇惡的報復和毀壞。在已經成為碼頭幫主之后,他對被他羞辱的年輕搬運工說:“現在我從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仇恨,這就對了。我從前比你還賤,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這是我們做人的最好的資本。你可以真的忘記爹娘,但你不要忘記仇恨。”這個年輕搬運工實際上是五龍自己的投射,這番話,其實是說給曾經的自己。仇恨是他征服城市、占領權力高位的原始動力之一。
五龍借呂六爺之手除掉阿保,不僅是為了報復阿保對他的羞辱,還因為阿保做了他想做而不敢做或者做不了的事。可以說阿保是五龍潛意識中欲望的反映,他對阿保不僅僅是恨,還有隱含的羨慕和嫉妒。后來五龍在城市中步步上位,加入碼頭會、成為地方霸主,可以說是在模仿阿保,或者說是沿著他想象中阿保將會走的道路而行動。
呂六爺則是五龍追求的權力和財富的具象化,雖然兩人沒有直接沖突,但呂六爺是五龍潛在的敵人,是他上升道路上的阻礙。于是他設計炸了呂家公館,使六爺遠走他鄉,自己才有機會將其取而代之。
五龍強占綺云的身體,是對她最初對自己漠視和反感的報復,和綺云結婚,也只是為了打擊和壓制綺云。充斥著惡意和冷漠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培育出了畸形的下一代:大兒子米生親手悶死了自己的妹妹小碗,二兒子柴生只顧賭錢玩樂,對親人全然不關心,最后還親手將金牙從父親的身體中搶走。人性中惡的一面永恒存在,相似的人性的悲劇,在下一代將繼續上演,循環往復。
五龍是一個面對歷史發展洪流的逆行者。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是城市向鄉村的擴展和滲透,正如滔滔洪水淹沒了許多像五龍一樣的鄉村的人們,他們被拋到城市當中,緊張而無措。生存困境將他們逼到一種極端的狀態,人性中惡的一面被激發和放大。不論他們在城市的命運如何,都無法真正地融入城市,想要回歸鄉村,鄉村也已沒有了容身之處。這些角落,主流的歷史敘述并不會記錄。歷史的發展并無對錯可言,犧牲者往往是角落里不被關注的普通人們。
五龍是一個個體生命在歷史發展洪流中無措無助的縮影。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對某一個人來說,歷史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給自己的人生帶來的東西是好的還是壞的?我們習慣了看到集體性的、政治正確的歷史發展描述,那些個別的無法跟上時代大節奏的人往往被忽略,就此被淹沒在歷史當中,不為人知。蘇童通過五龍這個形象,把歷史的另一面翻開,將這些人們擺在讀者面前,把我們時常刻意忽略、避而不談的問題明白地揭露出來,呈現出了一種非主流的、時代共名的聲音之外的“歷史的真實”。
[參考文獻]
[1]蘇童.米[M].北京:臺海出版社,2000.
[2]段斌,胡紅梅.艱難的救贖——《米》的新歷史主義意蘊[J].重慶社會科學,2007,(10).
[3]劉進軍.還原歷史的語境———論新歷史主義小說《米》[J].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1).
[4]趙雙雙.火車、米與楓楊樹大水——淺談蘇童《米》中物象的運用[J].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7).
[5]徐汀汀.新歷史小說特點在蘇童小說《米》中的呈現[J].文學教育(下),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