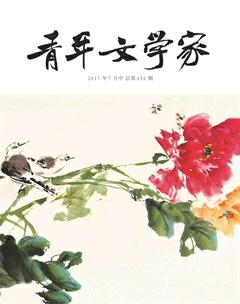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解讀《喧嘩與騷動》
摘 要:威廉·福克納,著名的美國南方作家,一生中創作了眾多著作,小說《喧嘩與騷動》是他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在這部小說中,女性人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讀這部小說,探討父權制對女性的摧殘與壓迫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
關鍵詞:威廉·福克納;《喧嘩與騷動》;女性主義;父權制;女性意識
作者簡介:汪曉霞(1990-),女,山東煙臺人,碩士生,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0--02
一、引言
威廉·福克納,20世紀美國南方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喧嘩與騷動》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說中女性人物的生活不僅反映了傳統南方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與迫害,也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過程。因此,本文旨在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讀這部小說,探討父權制對女性的摧殘與壓迫以及在壓迫中女性意識的覺醒。
二、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女性主義起源于女權主義,是由女權主義的不斷發展衍變而來。女性主義注重性別意識和文化建構,是從文化批判的立場出發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掀起的第二次女權運動,主要是對兩性生存境況的反思、批判揭露男性文化對女性形象的扭曲,抨擊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以及援用女權的視角解讀經典作品,進行語言文學批評。
三、父權制下男性對女性的態度
在父權制盛行的美國南方社會,女性無疑是父權制的受害者,男性主導的社會影響著她們的思維方式,使她們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父權制對待女性的毀滅性影響首先體現在男性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在小說《喧嘩與騷動》中,女性人物凱蒂可以說是小說的中心,然而她從來沒有正面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是通過三個男性人物的內心獨白呈現了她從天真無邪走向墮落的故事。事實上,三位男性人物的內心獨白恰恰反映了他們對待女性的態度。
小說的第一位男性敘述者是班吉。作為一個只有三歲孩童智商的癡兒,班吉得不到母親的關愛,康普生夫人將其視作是對自己的懲罰,對其漠不關心。只有凱蒂一直關心照顧班吉,因此班吉將其視作是自己的保護者,就像是善良、充滿愛心的母親一般。在班吉的內心,凱蒂是一個純潔的、充滿愛心的姐姐形象。他害怕凱蒂長大,因為長大意味著要結婚,與丈夫一同生活。在凱蒂失去貞操后,班吉嚎啕大哭,他不再接受凱蒂,將其推進浴室。班吉抗拒凱蒂的態度反映了傳統的南方男性拒絕女性長大,要求她們保持圣女形象。
小說的第二個男性敘述者是凱蒂的哥哥昆丁。作為一個正常人,昆丁卻和班吉一樣想永遠地占有凱蒂。他十分嫉妒凱蒂對其他男人的愛。作為南方父權制社會的繼承者,昆丁身受傳統教義和清教思想的影響,認為女性的貞操象征著家庭的社會地位和榮譽,屬于她的丈夫和家庭。因此,凱蒂失去貞操使得昆丁感到極其恥辱,也給整個家族帶來了恥辱。他對失去童貞的凱蒂反應十分激烈,他甚至說:“我希望你死了”(福克納,1929:157)。在昆丁的內心世界,他將凱蒂視作是自己“純潔的愛人”,并自私地想帶著她逃離這個家庭,但是在現實中他又無法真的愛凱蒂,因為那樣就違反了南方社會的傳統道德原則。他內心的矛盾以及在得知凱蒂失去貞操后的絕望最終使他走向自我毀滅。昆丁對待凱蒂的態度同樣表明父權制下女性被當作是私有物品,女性的貞操被看作是無比重要的東西。
小說的第三個敘述者是杰生。杰生是一個冷血、自私殘酷的人。在杰生眼中,凱蒂和凱蒂的女兒都是賤人。正是杰生將凱蒂失貞的事報告給了母親,導致凱蒂被趕出家門。凱蒂與赫伯特離婚導致杰生失去工作,以至于他更加仇視凱蒂和她的女兒。為了報復凱蒂,杰生將她趕出家門,卻將女兒小昆丁留在身邊,以此來勒索凱蒂。杰生不僅仇恨凱蒂和她的女兒,甚至仇恨所有的女人。他對待自己的母親同樣十分殘忍。康普生夫人將杰生視作是自己唯一的兒子,對其呵護備至,然而杰生卻認為母親是自己的麻煩和負擔。在杰生的心里,沒有女人是好的。他認為女人應該服從社會制定的原則和規則。凱蒂和小昆丁正是因為違反了傳統規范而被視作是賤人。在他看來,男人是女人的領導者,女人是男人的工具,這也代表了父權制下男人們對待女人的普遍觀點。
四、父權制下女性的地位
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和迫害還可以通過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狀況體現出來。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男人把女人當作是物品,甚至女人受男性主導思想的影響,也把自己看作是物品。康普生夫人就代表著這樣一類女性,她們受到父權制的壓迫,卻又毫無反抗。她們服從男性,充當父權制的捍衛者。生活在父權制的社會背景下,康普生夫人深受父權思想的影響,南方傳統的“淑女觀”及對女性的道德規范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康普生夫人的生活并不幸福,小說中她得不到丈夫的關愛,兒子的尊重,她只是南方傳統所要求的那種“淑女”,甚至都不是妻子和母親。和其他美國南方女性一樣,她沒有家庭地位,沒有社會地位,在男人的眼中只是生育工具。康普生夫人甚至用父權社會的教條和標準去要求自己的女兒。尤其是在凱蒂失去貞操之后,同樣作為女性的康普生夫人不僅沒有站在女兒這一邊,反而是和家里的男性有同樣的看法,認為凱蒂敗壞家門,違背了南方傳統的“淑女觀”,以至于“她穿著喪服戴了面紗在屋子里轉來轉去……她僅僅是一面哭一面說她的小女兒死了” (威廉·福克納: 1984, 255)。通過分析可見,康普生夫人是南方父權制的犧牲品和捍衛者,毫無女性意識。
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還體現在女性言語的缺失。小說中,凱蒂作為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卻沒有機會表達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在男性主導的社會,女性被剝奪了大量的權利,甚至是說話的權利。失去話語權證明了在舊南方父權制下女性低下的社會地位。小說中,男人可以直接公開地談論他們的想法、表達自己,而女性則以被動的方式發聲。在小說第三部分,凱蒂在與杰生的幾次對話中總是有意識地將話語優先權給男人,而自己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法控制對話,甚至自由表達自己。
五、女性意識的覺醒
在小說《喧嘩與騷動》中,凱蒂和女兒小昆丁雖然受到了父權制的迫害,卻并沒有像康普生夫人一樣成為父權制的犧牲品。她們內心強烈的自我意識引領她們去反抗男性主導的社會,追求和男性同樣平等的權利。
在凱蒂小的時候,她就體現出了追求平等權利的意識。當得知昆丁要去上學的時候,凱蒂也立即表達自己明年也要上學的想法。她想擁有和昆丁同樣的權利。正如小說中昆丁回憶的,凱蒂從來不是一個女王或者仙女,她總是一個國王或者一個巨人或者一位將軍。凱蒂小的時候就是一個勇敢的姑娘,她命令她的兄弟和仆人在祖母葬禮期間服從她。她爬上樹以確定房間里發生的事情,而她的兄弟們只是站在樹下等待她的消息。她不懼怕杰生的威脅,總是無所畏懼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小說中,康普生夫人要求凱蒂也遵從她一直遵守的規則,希望將凱蒂培養成像她一樣的“好女人”。然而,凱蒂卻有著自己的想法和主見。在凱蒂看來,婚前喪失貞潔的女孩并不可恥,貞潔對于女人來說也并非那么重要。
美國南方的父權制和傳統的道德規范扭曲了凱蒂的天性,壓抑了她的自然欲望。這種社會環境使她感到不滿和壓迫感。甚至是在凱蒂小的時候,她就說:“我會逃跑,永遠不再回來”(福克納,1929:24)。這表明了凱蒂的反抗意識和追求個人獨立的愿望。但凱蒂的個人經歷表明,在男性主導的社會女性對于平等和獨立的追求十分困難。凱蒂能夠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體現了她女性意識的覺醒。
小昆丁是凱蒂非婚生的子女,在她出生九個月后就失去了父親。在小說中,福克納將其描述為一個自我完善的人,她的自我完善主要表現在對叔叔杰生的反抗。小昆丁和她的母親一樣都是不幸的人,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她比凱蒂更加不幸。自從出生以來,她就被迫和母親分開,失去了獲得母愛的機會。她選擇和自己的母親一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體現了小昆丁同樣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的人。她經常逃學,說謊話,模仿祖母的簽名自己在學校的報告卡上簽字。此外,她還經常在外面和很多男人來往。她無視杰生不允許她在街上玩耍和徘徊的警告,拒絕按照杰生的要求行事。她不懼怕杰生的質問和威脅,在杰生抓住她的胳膊的時候,她并沒有被嚇倒,而是命令杰生松開她,并威脅道:“我會打你”(福克納,1929:167)。最后,小昆丁打了杰生。相比于凱蒂的“我會逃跑,永遠不再回來”(福克納,1929:24),小昆丁更加強硬,她用實際行動反抗那些壓迫她控制她的人。她告訴杰生自己寧愿呆在地獄,也不愿跟杰生住在一起。相比于凱蒂沒有意識到誰摧毀了她的人生,小昆丁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她對杰森說:“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你的錯。如果我不好,那是因為我必須這樣做。是你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福克納,1929:231)。
在小說的結尾,小昆丁偷走了杰生所有的錢,從當年凱蒂爬過的那棵樹逃走了。小昆丁知道只有逃離那棟令人窒息的房子,她才有機會迎接全新的生活,這些恰恰表明女性意識和自我完善意識在她身上的覺醒。她逃離康普生家族,走向追求個人獨立的道路正是美國南方父權制壓迫的結果。
六、結語
本文通過分析小說中三位男性人物對凱蒂的復雜態度以及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背景下女性的生活狀況和地位揭示了美國南方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與摧殘。通過分析康普生夫人、凱蒂和小昆丁三位女性人物在父權制和美國南方傳統規則面前的不同態度體現了女性反抗意識從無到有的覺醒和發展過程。
參考文獻:
[1]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M]. America: Penguin Book Ltd., 1929.
[2]胡文慧. 《喧嘩與騷動》中的三代女性人物分析[J]. 科技信息, 2010, (28).
[3]胡櫻. 威廉·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的女性主義思想解讀[D]. 西北大學,2010.
[4]威廉·福克納. 李文俊譯. 《喧嘩與騷動》[M].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