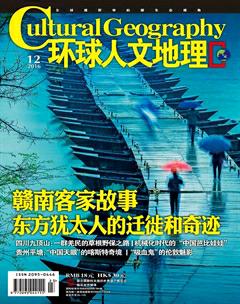北京絹人
文涓+曉翔
如今的“北京絹人”,雖誕生于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卻與遠古華夏的傳統布人、針扎等技藝一脈相承。“北京絹人”的三維立體軟變形工藝,非常難以駕馭,但制作出來的作品精湛,常被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送給外賓。
然而,在商業化的沖擊下,它雖然被列入“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這一工藝美術后繼乏人的現狀仍然令人擔憂……
在古代,絹人曾是皇親貴戚的玩物,幾經歷史變遷,絹人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而“北京絹人”作為各地絹人中的佼佼者,制作精美、風格高雅,被譽為“中國的芭比娃娃”。在新中國誕生之際,開國偉人尤其喜歡將它作為國禮,送給一些外國領導人。
然而,機械化時代的狂風驟雨,席卷了整個傳統手工藝行業。原本精美獨特的手工藝品,被大規模地復制、生產,曾經輝煌的手工“北京絹人”好景不再,已很少再有問津者。盡管如此,在東城區,“北京絹人”傳承人崔欣,依然將絹人作為一種藝術品,精雕細琢,傳承并創新這門工藝美術……
偉人國禮非常時期的非常傳承
北京東城區一棟普通居民樓里,樓道里光線暗淡,電梯咯吱作響,60歲的崔欣在家里忙碌著,她正一手脫模,一手運筆描畫。
在這座陳舊陰暗的居民樓里,崔欣的家與其他住戶別無二致,只是門框頂上寫著“崔欣北京絹人藝術世界”的字樣,才讓人感覺到這里不一樣。她手中的絹人,還未完成,就已栩栩如生,這與開國之初,“北京絹人”專家葛敬安大師的絹人作品形神俱似。
葛敬安,北京絹人專家,藝術造詣頗高,由她親手制作的絹人,深受國家領導人的喜愛。開國之初,毛主席就說:“工藝美術一萬年也不能丟……搞掉的要恢復得更好。”葛敬安大師帶著這樣的使命,無數次查閱資料,并多方走訪、咨詢,繼而建立起以絹人制作為主的“北京市東城區美術人形廠”。她通過不間斷地設計、試驗,最終創研出一套完整的絹人工藝制作流程,于上世紀50年代成功首創了具有傳統基因,又有北京韻味的“北京絹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包括北京絹人在內的傳統藝術被一一掃地出門。危難時刻,得益于鄧穎超的設法照應,東城區政府將葛敬安和幾名藝徒,安排在東城區九道彎胡同的兩間棚屋里,她們才得以繼續美術人形的創研、設計工作。這是北京絹人在非常時期的“非常傳承”,也是北京絹人傳承路上不能忘記的歷史。
正是在這兩間棚屋,藝徒中年齡最小的崔欣,得到了葛敬安、楊乃蕙兩代絹人宗師的直接指點和教導。“師傅當年對我的每一個要求、每一次稱贊,現在每每憶起,都歷歷在目。”崔欣感慨,“那時被師傅認為是殘次品的東西,拿到現在,件件都是精品。”
崔欣說,絹人制作,不能有點滴馬虎。頭型五官、體型四肢,均以絹紗科學創塑,不同于其他材料或機械化生產的品種。
制作工藝精雕細琢的傳神藝術
絹人的高度一般在30~50厘米,但崔欣創作的《海螺仙女·龍宮盜寶》《紅樓夢·李紈“教子”》《瑪麗亞懷抱“圣嬰”》和《幼年哪吒》,均不足10厘米,顯得小巧逼真,玲瓏可愛。其實絹人越小,制作工藝就更為精細,創作的難度也就越大。
在絹人制作中,材料的選取一般以蟬紗、羅、綢、緞、縐為主。根據傳統制作方法,絹人的制作分為信息設計、雕刻、翻模、脫模、塑裱五官、工筆畫頭、針結手腳四肢、織染裁剪、彩藝漆繪、發型飾物、靴帽道具、背景組合、金木油工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的要求都極為細致,必須嚴格把控。
其中,做人形首要的一步便是做頭,藝師們先用油泥或木,雕成不同人物、不同表情的頭型,然后翻成石膏頭模,再將針織品和喬其紗用粘合劑在頭模上裱糊,壓碾出五官,干燥后脫模、開臉,頭的初步模型——頭殼就做成了。不過,頭部最重要的在于工筆畫頭,其中最難的便是畫眼睛: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根據人物不同,畫出來的眉眼神韻也要完全不同。
畫頭,用筆基于國畫,但又不完全同于國畫。因為絹人的畫頭工藝,是在雕塑脫模等工序完成后進行的,如同內畫壺大師,一手轉動著壺面,另一只手握筆在壺內畫出逼真的山水人物。絹人頭模的傳神畫貌,雖非內畫工夫,卻是在凸凹不平的顴頰、眉眼、鼻口間自如運筆,筆法既有獨特之處,又與工筆國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待頭部美化后,再以棉花球卷、纏、裹填充五官,以蟬翼紗套緊,便制成了栩栩如生的絹人頭形。緊接著,是一道看起來非常簡單卻十分費心的工序——梳頭。
梳頭,即在頭模上用黑布粘出發的邊際,貼上發絲,裝上發卷,再裝點手工精制的裝飾品。另外,絹人的手的制作則需要高超的技藝和耐心;絹人的體形,在設計時要從人物的整體考慮,主要掌握體形結構的制作,金屬絲為“骨架”,棉花纏在骨架上便是“肌肉”;再給體形穿衣、戴帽,配上鞋襪就成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制作時不僅要考慮人物的身份、時代、式樣,還要選擇材料質量、配色、漆秀、圖案,其服裝的附件飾物,如風帶、佩飾、項圈、佩劍等,每個環節,都需要經過多方面調查研究,再細心制作而成。
此外,絹人手里的扇子、武器、彈奏的樂器、使用的案兒、身邊的盆栽、山石……各種小道具,都需要藝師們手工制作。
崔欣告訴我們,絹人的制作工藝,必須按工序學會學精、學出“彩”來,即學練出靈感、悟性和神韻來。“我和我的恩師們都是這樣學過來的,并各有所長。”她頗感自豪,“當然,如果由一個人來完成絹人的全部制作,也不是不可能。只是這樣,用時少則一個月,復雜的人物形象,甚至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尷尬處境北京絹人的傳承之路
在崔欣家里,我們看見了一個極大的四門衣柜,打開后全是她以前做過的絹人。其中,光頭絹人造型尤為搶眼。據崔欣介紹,雖說北京絹人的制作工藝已非常純熟,但數十年來,中、日兩國的絹人均未出現過光頭的絹人造型人物,這是絹人制作歷史上的空白。
但是,崔欣敢于突破和超越,經過她的長期設想和幾十次的試制,終于成功研制了光頭造型的絹人。這項“絹人光頭”脫模工藝 ,就半個世紀的傳統絹人工藝來說,是個可喜的突破。
而她創塑的紅樓夢人物、三國人物、聊齋人物、帝王將相、神佛菩薩、中外典型人物等,在歷次公開展覽中,博得了公眾的一致好評。而崔欣對作品創作始終如一的熱誠追求,也贏得了工美界的肯定,稱贊她“工藝精湛,赤忱質樸”。
盡管獲得無數的贊譽,但崔欣還是無奈地說:“不管什么時代,真正搞藝術的人都很清貧。我就是想傳承這種原生態的民間工藝,但是作為一種藝術,我還是想將它和純粹的市場經濟保持距離。”她認為,這不是清高,藝術不是商品,應給予它應有的價值。“也有人聯系我,讓我做絹人,一個一個地復制,很快,比我重新構思、設計要快得多,但我不想做。”曾經,北京絹人被合并到不同的行當,且并來并去,因而一直處于從屬地位,難有獨立開拓發展的空間。而這一切被急功近利的“智者”看在眼里,于是,“智者”用僅有的幾個絹人范本,進行大批量地機械化生產,絹人藝術淪為流水作業,失去了其原有的藝術價值……
雖然在2009年,“北京絹人”被列入“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后繼乏人的現狀不得不令人擔憂。崔欣感慨道:“雖然我現在收了三、四個徒弟,但徒弟們只能通過業余時間來學習絹人制作。我沒有能力為他們提供工資,我的退休工資才1900多元。學生們也需要生活保障,所以只能利用業余時間來學習,這是傳承的尷尬,也是我的憂慮。”
為了使“北京絹人”這項瀕危藝術能夠更好地得到傳承,崔欣希望有條件的大中專院校設立單項藝術專業,如雕塑、繪畫、絹人工藝等,培育科研與藝術相結合的新型人才。“絹人的壽命最長一兩百年,希望科學家們協助,延長絹人用料的壽命,使絹人成為一種可永久性保存的藝術品……”崔欣說,“這需要中科院納米技術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只有依靠政府的溝通幫助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