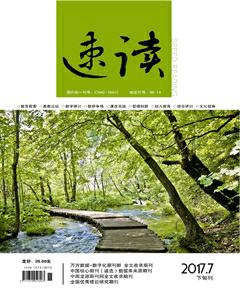淺談夸飾文學
摘 要:夸飾手法在抒情性文學中使用使得文章能夠更深刻地表現事物,更充分地抒發情感,本文從情景交融、詩畫一體、對話交流三個方面闡釋夸飾文學在文體上的內涵與特點。
關鍵詞:夸飾;空間性;讀者介入
《夸飾》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七篇,專論夸張的修辭手法。“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夸飾”手法歷史悠久,文辭產生之初,“夸飾”便已存在。夸飾手法以其獨特的文辭修飾作用,展現出了獨特的文體特色。
一、情景交融——夸飾之“和”
夸飾文學大多以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之景為基礎,以抒發作者內心情感喜惡為目的。“并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大圣所錄,以垂憲章。”不論是旨在歌頌,還是意在批判,通過夸張的修飾總能讓人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沒有情感的傾注,夸飾文學就像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般,失去生命活力。
夸飾性文學大多取材現實,經過個人生命體驗的過程獲得,若是脫離現實生活,不以生活經驗為中介,純粹通過想像創造新的意象,必定會落入“驗理則理無可驗”的境地,顯得荒誕詭譎。
做為中國傳統文學中最為常見、最為基礎性的藝術形式,“情景交融”以其恰到好處的情與事的處理,為中國古代文人普遍接受,反映出中國傳統的“和”的思想觀念。儒家人倫之“和”、道家自然之“和”、釋家禪理之“和”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夸飾文學也不例外地深受“和”字影響。夸飾之“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體現在取材的合理性,《文心雕龍·夸飾》:“又子云《羽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于朔野。”為了夸張而歪曲宓妃水神的形象,貶低他們的行為,不符合人們心中對他們的一貫印象,更不符合義理。這是因為取材方面的不當而導致的夸飾的荒誕。
其次體現在夸飾的度,欲寫樓臺之高,謂之“奔星與宛虹入軒”,鬼神都無法上去;為寫禽鳥之多,謂之“飛廉與鷦鷯俱獲”,園囿中竟有神話中的奇鳥。當樓不再是樓,園不再是園,夸飾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價值。
夸飾只有達到“和”的境界才能夠真正傳達作者本義,為讀者所接受。
二、詩畫一體——空間張力
作為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三大宗教之一,道家思想深刻影響著文學觀念和古代文論的發展。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莊子“至樂無樂”的說法,體現了一種“虛實相生”的思想。而“虛”和“實”正是夸飾文學的兩個方面,“虛”以“實”為創作基礎,“實”因“虛”而深刻動人;在有限空間中見無限想象,在無限想象中見有限情理。
所謂“實”,即藝術真實,是指夸飾文學中明確表述的物象,所謂“虛”,即以“實”為基礎產生的空間想象、藝術情趣以及人生哲學。具有空間張力的夸飾性作品,總能以有限的“實”構建出無限的“虛”,使得夸飾性文學作品在思想上得到升華。一般來說,具有空間性的“實”表現在立體感、動靜對比、色彩對比、數量變化四個方面。
從立體感方面來說,夸飾性文學通過具有空間性的名詞的堆砌,形成一幅立體性的畫面,打開了空間。譬如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黃鶴樓”、“孤帆”、“碧空”、“長江”四個物象組成了一幅極富立體感的圖景,擴大了讀者的視野,“天際”二字運用夸張手法,顯示出空間的渺遠。從動靜對比方面來說,動態觀感給人感覺上的空間立體。“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一句縮萬里于咫尺,使咫尺有萬里之勢,盡顯夸張之態,夕陽倚山的靜態美與黃河奔騰而去的動態美交相輝映。從色彩對比方面來說,色彩明暗對比,會使得事物空間性增強,“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風暗千家”,滿城風光盡收眼底。從量的方面來說,通過對長度、寬度或高度方面量的的夸大,增強了視覺效果。譬如“白發三千丈”、“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都通過量的變化使得事物性狀方面獲得強化,增強了空間感。
夸飾性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對“實”物空間性的增強,從而產生空間張力帶來的視覺與感覺上的強烈沖突,引發人們地空間想像,產生虛實相生的感覺。
三、對話交流——讀者介入
先秦時孟子就已提出“以意逆志”的說法,簡而言之,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別人的用意,不管是什么樣的文學作品,都遵循“作者以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規律。夸飾性文學作品通過讀者的介入形成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間的對話交流,產生出夸飾文學的豐富內涵。
不同時代的不同接受主體對于夸張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這主要是由于人的文明程度和認知水平的不一樣。譬如對于中國神話的認識與接受問題。中國神話是具有夸飾性的,大禹由父親懷孕生下的荒誕出生,女媧人首蛇身的人物形象,夸父追日的離奇行為,都充滿了夸張色彩,然而,不管是創世神話盤古化為天地萬物、女媧造人神話,還是堯舜禹治水神話、三皇五帝部落祖先神話,亦或是神話世俗化之后產生的實用性強的生活保護神,例如城隍神、灶王爺、財神等,中國古代勞動人們的心中對于這些神話人物和神話事跡的存在深信不疑。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的農耕社會,人們耕作勞動依賴自然,自然的力量在人們看來神秘而又強大,自然界中的神奇現象更讓人驚嘆不已,因此,對于自然,人們總是懷著一顆敬畏之心。當時的人們認知水平有限,對于他們無法解釋的現象,富有夸張色彩的神秘而又神奇的神話很好地填補了他們認知上的空白。但社會發展到今天,科學知識的普及,科學思想的灌輸下,神話故事只能作為文學存在,沒有人會相信它是真實的。
“一千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一樣的人生體悟、不一樣的文化底蘊造就不一樣的文化理解,不一樣的文學目的、不一樣的傳播對象形成不一樣的文化闡釋。夸飾文學以現實之景為基礎,通過藝術加工展現空間性的詩情畫意,抒發強烈的感情,表達深刻的理趣和人生哲學,在體現作家生命力的同時,經由讀者介入產生多樣性的文化闡釋,營造出別具一格的文化意蘊,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風格。
參考文獻:
[1]選自王運熙.周峰.文心雕龍譯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童慶炳.中華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M].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
徐穎(1995.10—),女,漢族,江蘇揚州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