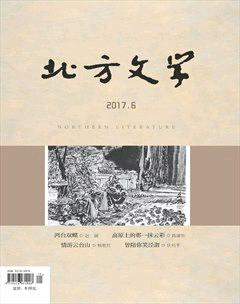紀錄片“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
賴丹
摘要:“情境再現”在紀錄片創作中早已被運用,特別是在歷史題材紀錄片中被廣泛運用。然而目前對“情景再現”的運用中,不乏為追求較強的可視性和趣味性而偏離紀錄片真實性創作原則之作。在眾多歷史題材紀錄片中,《故宮》對“情境再現”的運用較為嚴謹,充分運用紀錄片的模糊化處理方法使該片在符合歷史真實的情況下又不失藝術趣味。
關鍵詞:紀錄片;情景再現;模糊化
一、“情景再現”模糊化處理的方法
“情景再現”作為紀錄片的創作手法之一,已被紀錄片創作者廣泛運用。紀錄片“情景再現”應堅持宜虛不宜實的原則。在《故宮》中,對歷史人物的再現幾乎都堅持這個原則,體現在對歷史人物的模糊化處理上。為了實現藝術上逼近真實,《故宮》對“情景再現”的運用進行了模糊化處理,用畫面語言給觀眾提供一種“歷史的可能性[1]”。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曝光的處理
對被攝主體進行曝光過度效果的處理。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朱棣和大臣們在朝堂上的鏡頭,加強了對高光部分的表現,使得畫面亮的地方特別亮,失去了對被攝主體的正確還原。第三集《禮儀天下》里,玄燁登基大典的籌備,一個官員從院子里往外向大門走來,處在亮部的官員及其周圍景物曝光過度,暗部的大門曝光正常。陪體作為歷史遺跡得到正確再現,而被攝主體作為敘事因素通過曝光過度來模糊他們的形象,給觀眾留足對被攝主體的想象空間。
(二)景別的處理
《故宮》善于通過對兩極景別的運用,特寫表現被攝主體的局部,而遠景表現被攝對象的輪廓和線條,兩者都不能完整展現被攝主體的具體面貌。
特寫的運用。特寫本身就是對被攝主體局部的突出,無法展現被攝主體全貌。片中多次出現手、腳等的特寫。第一集《肇建紫禁城》朱棣手的特寫,看不到朱棣到底長什么樣,身長多少等等。只見局部,不見全貌,全貌留待觀眾去展開想象。
遠景的運用。遠景中被攝人物占畫面的很小一部分,只能看到被攝人物的輪廓和線條,而看不清細部。《肇建紫禁城》開頭介紹朱棣啟用永樂作為自己的年號,用了遠景鏡頭,只遠遠望見他身著龍袍,卻始終看不真切他的面貌。第三集《禮儀天下》情景再現“傳臚”,多次用到遠景再現當時的情景。這種處理方法把人物置于大環境下,能夠弱化對人物具體面貌的展現,從而實現對“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
(三)聚焦的處理
一般判斷一個畫面成敗的基本要求是對焦是否清晰,對焦不準確即虛焦,會直接導致畫面模糊,是失誤。但在紀錄片中,虛焦能增強畫面的真實感。《故宮》作為一部歷史題材的紀錄片也體現了對虛焦的獨特運用。《故宮》受其題材的限制,無法再現歷史人物本體。因此,《故宮》巧妙地利用虛焦處理“情景再現”,沒有展示人物的清晰面貌,而代以虛焦產生的模糊形象,既提供了對歷史人物的合理想象,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觀眾聯想的空間。
除了畫面整體虛焦外,被攝主體也可處于景深范圍之外,使人物的前景或背景清晰,而人物模糊。第五集《家國之間》秀女一字排開,模糊不清,反而是前景的燈非常清楚。這種方法與對曝光的控制有異曲同工之妙,使被攝主體不清晰,而陪體作為歷史遺跡被清晰展現。
(四)拍攝方向的處理
《故宮》盡量避開正面和前側面拍攝人物,因為這些方向都能展現人物全部或者大部分具體面貌,使觀眾能夠看清人物到底長什么樣。拍攝人物背影的畫面有朱棣、順治、徐皇后、大臣、宦官等的背影。還有一部分后側面和側面拍攝人物的鏡頭。《故宮》對于攝像機拍攝方向的選擇仍然意在最大限度地避免對人物全貌的展現,為觀眾提供聯想的空間。
(五)不規則構圖的運用
不規則構圖突破常規構圖方法,以不規則的、割裂的、不完整的方式構圖,產生強烈的帶出感,用這種構圖方式打破“情景再現”可能帶來的與真實的混淆。第五集《家國之間》慈禧和候選秀女背面的頭花和半個腦袋。第十集《從皇宮到博物院》溥儀和婉容吃蘋果的畫面,只拍攝了婉容前側面從臉頰到耳朵的部分,只拍攝了溥儀后側面后腦勺以下的部分。這兩個畫面很生硬地分割了被攝主體,但目的很明確,通過分割的方式避免出現被攝主體全貌,同樣實現“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
(六)光影的運用
影子的運用。全片多次運用投射在紅色宮門、宮墻或窗戶上的影子,以此代替人物面貌的直接呈現。第五集《家國之間》“珍妃”在被投進井里之前的影子透過鏤空窗戶投射在墻面上。第十集《從皇宮到博物院》溥儀打電話給胡適,溥儀的影子投射在墻上,都巧妙地利用影子來避開對被攝主體的直接呈現。
逆光、側逆光的運用。逆光或側逆光會使被攝對象處于陰影里的部分不能被清晰展現。第十集《從皇宮到博物院》溥儀和婉容吃蘋果,窗戶投射進來的逆光導致二人的具體面貌不能被清晰展現。第八集《故宮藏玉》馬戈爾尼被側逆光照射,面部大部分處于陰影里,看不清細部特征。
拍攝時機的選擇。日出之前、日落之后,畫面普遍亮度較低,總體效果較暗,不易表現被攝對象的細部層次。第十集《從皇宮到博物院》分別有清晨黃包車遠去,街上人來人往的畫面,以及夜晚宦官在皇宮行走的畫面,人物處在亮度較低的環境里自然看不清面部細節。
不管是影子的運用,還是逆光的運用,或者拍攝時機的選擇,都是為了使被攝主體不能被清晰展現,留給觀眾聯想的空間。最終使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合理想象融為一體。
二、“情景再現”模糊化處理的優勢
(一)明確歷史真實與模擬真實的界限
對于“情景再現”,不管多么逼近于真實,它始終都不等同于真實,所以不應與真實拍攝相混淆。有人建議對“情景再現”部分加上標注,提醒觀眾這不是真實,而是對真實的模擬。但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方式不存在誤導觀眾去相信這就是歷史的真實,而是為觀眾創造一種環境氛圍,留下余地給大家想象、聯想。人物形象一旦具象化,便阻斷了聯想的可能性,強制灌輸給觀眾創作者主觀對人物的想象。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正是明確無誤地告知觀眾,這是對真實的模擬,而不是真實本身。如果在畫面上加上“情景再現”的字樣或者解說詞里說明這是“情景再現”,那么模糊化處理不借助字幕或解說詞,而是直接利用畫面語言告訴觀眾這就是“情景再現”。
(二)增強了紀錄片的畫面表現力
早期中國的紀錄片說教味濃厚,因為技術的限制和對紀錄片創作手法認識的局限,一旦影像素材缺失,只能靠解說詞、文字資料、圖片等來彌補。而“情境再現”的使用,使得畫面內容更加豐富與生動,增強了紀錄片的畫面表現力。不僅提高了紀錄片的可視性和趣味性,而且使得畫面能夠擺脫早期紀錄片影像素材的不足,避免淪為解說詞的陪襯。
三、結語
“情景再現”在紀錄片中的廣泛運用,既是受眾審美的需求,又為紀錄片賦予了更加鮮活的生命力。對“情景再現”的模糊化處理既體現了“情境再現”的合理性,同時也體現了對紀錄片創作手法實踐上的探索。紀錄片的創作手法應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但應遵循紀錄片創作的基本原則。所以對“情景再現”的運用要不拘泥于度,但更應該掌握好度,使“情景再現”既符合歷史真實,又給予觀眾想象和聯想的空間。
參考文獻:
[1]張雅欣,張春玲.《故宮》與再現手段[J].中國電視,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