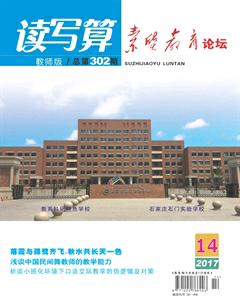天若有情天亦老
張海斌
摘 要 《古詩十九首》原本是東漢時期無名氏文人的五言詩,后梁蕭統從中選取十九首編入《昭明文選》而成。《古詩十九首》中表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不僅是當時下層文人失時傷世的詠嘆,還體現出了他們對于生命價值的深刻思考,包括生之如何度過,死之如何迎接的哲學命題。在經過了痛苦的探尋之后,文人們開始著眼于自己身邊的事物,其中愛情的渴盼,知音欲求乃是當時文人作品的兩大主題。
關鍵詞 古詩十九首 愛情 友情
中圖分類號:G6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7)14-0141-02
東漢末年,硝煙四起,朝野混亂,政局動蕩不安。社會的黑暗,使得當時的文人,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文人們,報國無門,進仕無路。儒學思想從興盛走向衰落,傳統的道德觀念被丟棄。尤其兩次“黨錮之爭”使大批文人慘遭殺戮,轉而遠離政治。在痛苦中他們將眼光投向自身,開始關注自我,反思自我存在價值,以期重新認識生命的本質。
及時行樂之,蕩滌放情志之,換來的卻是更深的苦悶,更深的痛悟。加之,漢末的游宦游學是一種風氣,游子只身在外,本想通過入仕,換得功名利祿,卻被社會打回了原形。這時候的文人們才發現,因為功名,舍棄了人生最為可貴的愛情,親情,友情,是多么的令人可悲。于是,詩人的眼光回到起點,,回到出發的地方。他們重新看到家中的妻子和愛人,看到共奏高山流水的知音良友。至此,漢末文人們的生命意識已經完成了一個輪回和重生,這是他們生命意識達到頂峰的標志。元人陳繹曾指出《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這個‘真‘至情正是生命之真,生命之情。”如果詩人對于生和死的看法和感慨是無奈和悲痛的,那么,對待愛情和知音良友則是至情和真誠的。
一、思君令人老——愛情的執著
《古詩十九首》中關于愛情的描寫大多是是閨中婦人對遠行的丈夫的思念,有喜有悲,大抵分為兩種,一種是苦苦的等待,渴望男子回家與之團聚。“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行行重行行》),思念一個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突然有一天發現自己容顏不再靚麗,自己的青春年華都在等待和思念中漸漸消失,這份無奈和落寞對女子而言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因此,要努力加餐飯,保持體力才有希望繼續思念和等待。這是怎樣的癡情和真愛才能堅持幾十年如一日的守候。“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青青河畔草》),這種大膽直白的話,在那個封建時代還是不常見的。在這里,女主人公的感情是極為強烈而熾熱的,沒有絲毫的顧忌和克制。這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是對封建禮教的反叛,也是想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望。“難獨守”便是孤獨寂寞的妻子對遠方的丈夫的深深的思念,昔日的“娼家女”如今卻要守著空床日以繼日的忍受著孤獨和寂寞,這份愛才難能可貴,才更顯得真誠。
一種是以物折相思,來表達深深的思念。“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便是用芙蓉來寄托思念。女子拿著剛剛采摘的芙蓉,想要送給心愛的他,卻發現已經和他相分別很久了。接下來的兩句感覺是在寫游子,游子回頭望向舊鄉,實際上,這兩句的“視點”仍在江南,表現的依然是那位采蓮女的痛苦思情。不過在寫法上,采用了“從對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鄉而嘆長途”的“懸想”方式,從面造出了“詩從對面飛來”的絕妙虛境。“芙蓉”往往以暗示著“夫容”,所以芙蓉在這里就有了以物折相思的效果。這種睹物思人的寫法,使思念之情顯得更加朦朧婉轉,沁人心脾。
《古詩十九首》里的愛情故事乍看上去都是悲情的,但是細細咀嚼,故事中的男女是享受的,因為他們懷有希望而不滅。仿佛對于這時候的男女來說,時間從來不是阻礙他們愛情的絆腳石。可以一別就是幾十載,可以一等就是一輩子。只要心中存有一點點希望就不會去放棄。可見,感情之真,之純粹。這樣令人感動的愛情,如果因為追求仕途而忽略那才真是人生一大遺憾。可惜,當他們意識到愛情的美好的時候,已經是在仕途追求的失敗,離家千里之外了。頓時有種為時已晚的感覺。但至少心已經有歸屬的地方,有希望在前方了。
二、高山流水覓知音
伯牙與鐘子期是一對千古傳誦的至交典范。伯牙善于演奏,鐘子期善于欣賞。他們互相能懂得彼此心中所想,遂成摯友。雖然《古詩十九首》的年代還沒有出現伯牙子期,但是對于知音良友的渴望是同樣的需求。“不惜歌者哭,但傷知音稀。愿為雙鷓鴣,奮翅起高飛。”(《西北有高樓》),作者聽到高樓上的弦歌聲,“音響一何悲”,不由得也跟著傷悲。可是作者擔憂的卻是無人能欣賞,無人能夠感同身受歌者之苦。同樣地,世間多少悲苦酸甜都無人一同分享。如若有知音良友出現,作者是毫無猶豫的與之一起振翅高飛,一起享受人生。這種對知音良友的渴望正是建立在“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明月皎夜光》)的背叛基礎上的。一起讀書的情誼卻因為追求仕途而被棄之若破履。令人心寒的不是求仕失敗,卻是自以為最信任的人拋棄你。只有同甘甜,不能共苦厄,這是讓作者心碎的重要原因。這就顯得覓得一知音良友很重要。可見,此時此刻的作者,享受的是“愿為雙鷓鴣”的高山流水,而非“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飛黃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