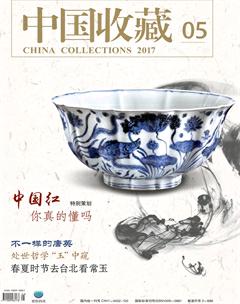來自皇家的“紅色訂單”
李春姣+魯益超



《禮記·月令》中有記載:“天子居名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紅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可見在明黃色成為天子之色以前,靚麗的紅色一直是天子身份的重要象征。紅色的傳統工藝制品因其色澤鮮亮、制作費工、成品可人,自古以來便得到中國貴族的喜愛和追捧,由此在我國工藝美術領域成就了數種紅色“奢侈品”。這些古物的紅色主要源于礦物和植物染料、寶石、珊瑚、朱砂以及銅還原物。以宋為開端,經過元明清三朝的歷練和試驗,呈現在今人面前的它們落落大方、氣度泰然。翻一翻當年皇家和貴族的紅色“訂單”,我們可以窺見“下單”的奔放和“接單”工匠的卓越技巧。
替代金銀成主角
金銀是古代宮廷首飾盒中最主要的材料,但從元代起,宮廷首飾盒里的顏色就更加豐富起來了。在金銀首飾上鑲嵌寶石是從元代開始興起的,至明代宮廷設計制作貴重首飾時,金銀和珠寶所占比例相當,到了清代,珠寶成了主角,金銀材料的使用反而更為減少了。
明代宮廷首飾通常會使用祖母綠、綠松石、紅寶石、藍寶石,點綴少許珍珠,清代則大量取用翡翠、珊瑚、碧璽、蜜蠟等等。這和明清時代中國與國外交往的頻繁有著很大關系,從首飾盒里也能看出王朝的實力與地位。這其中,紅色主要由紅寶石、碧璽、珊瑚來實現。
宮廷中用色規定嚴格,與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緊密相關,其中紅色寶石的地位很高。據《大清會典》中記載,清朝頂戴,從顏色上分官階:一品為純紅色,二品為雜紅色,三品亮藍色,四品暗藍色,五六品為白色,七品及以下則為金色。頂戴在雍正八年改為定制,細分為朝冠和吉服冠兩種。朝冠,自親王以下至一品官,冠頂均用紅寶石;一品官頂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二品官頂飾小紅寶石一,上銜縷花珊瑚;三品官頂飾小紅寶石,上銜藍寶石……吉服冠,親王至貝子均用紅寶石頂,一品官用珊瑚頂,二品官用縷花珊瑚頂,三品官用藍寶石頂,四品用青金石頂……由此可以得出,清代對彩色寶石貴重等級的排序為東珠、貓眼、紅寶石、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硨磲等等,紅色象征的權威也不言而喻。
在中國,碧璽這個名詞最早出現于清代典籍《石雅》中:“碧亞么之名,中國載籍,未詳所自出”,《清會典圖云》中也提到“嬪妃頂用碧亞么”。碧璽有藍碧璽、三色碧璽、西瓜碧璽和雙桃紅、紅色、綠色、粉色等顏色。清代,碧璽一度曾成為權力的象征,是一品和二品官員頂戴花翎的材料之一,也用來制作朝珠。晚晴時期慈禧太后執政時,大量從國外進口碧璽入宮使用,更讓碧璽在中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此外還有珊瑚,其在宮廷器物的使用中,以紅色為上品,被稱之為“火樹”。珊瑚的使用除了在首飾中多見以外,在宮廷的珠玉盆景中也是非常出彩的浪漫主角。
朱色一件抵萬金
印章是信用的代表,古人對其材質使用頗有講究,常見的有玉石、象牙、金等貴重材質。其中,雞血石從皇宮貴族到文人雅士,是頗受鐘愛的印章材質。
雞血石血色艷麗,質地溫潤,是我國特有的名貴印章石。雞血石中的紅色部分主要由辰砂礦物組成,紅色以外的部分稱為“地”或者“地子”。迄今為止,我國僅在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發現過雞血石礦床,分別是昌化雞血石與巴林雞血石。早在明清兩代,昌化雞血石就已經名揚天下、價抵萬金了。
提到印章,必然離不開印泥。朱泥的使用可以推早到戰國時期,在江陵楚墓出土的菱形錦面錦袍、龍鳳紋錦袍以及塔形文錦帶上都蓋有用印泥鈐印的朱印。朱泥的普遍使用則一般認為是在隋唐。
除去朱色,印色還有墨色和藍色兩種,用法各殊。朱色印泥歷來普遍用于文書、契約、書畫藝術品,起著信據、簽押的作用,墨色印泥在唐代已經普遍應用于圖書及寫經中了。從宋到明清各代,如父母有喪,百日之內蓋私印時,使用墨色,元代也有用青色的。藍色印泥是明清之際遇到國喪,在百日之內官印必須用藍色鈐蓋。
文人畫全盛時期的元、明、清三代,對于朱色印泥的使用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印章與詩文書畫合為一體,使黑的墨色、白的宣紙與紅的印章交相輝映,朱泥起到平衡構圖、點醒畫面的作用。印泥制作工藝的不斷改進也使得朱泥在留存下的古畫上依然熠熠生輝。明清時期,所制印泥都稱本宗為宋“宣和古法”,御用的印泥則皆稱為“宮中秘制八寶十珍印泥”,其用料十分珍貴,含紅寶石、紅瑪瑙、珊瑚粉、珍珠粉、赤金葉、鏡面砂、陳麻油、麝香等,具有不濘、不凍、不粘、不落、不霾、易干的特點,并且經久不變。
刻刀流轉現奢華
談到宮廷與“紅”相關的器物,雕漆,尤其是剔紅不能不提。
雕漆是我國漆工匠對漆材質運用的巔峰樣式,歷經唐、宋、元、明、清時期達到其工藝與產業規模的高峰。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剔紅,即在天然大漆中加入朱砂,使漆色呈現紅色,做法是在器胎上髹涂幾十以至上百道大漆,陰干后在漆地上雕刻圖案。
宋朝的剔紅令后人贊不絕口,元人在《至正直記》中提道:“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柈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柈底而后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銀、或銅、或錫”。到了明清,相關記載更是不絕如縷。比如《格古要論》“剔紅”一條有“宋朝內府中物,多是金銀做素者”;謝堃《金玉瑣碎》中稱:“宋有雕漆盤、盒等物,刀入三層,書畫極工。竟有以黃金為胎者,蓋大內物也。”
據悉,宋時國家祭祀、賞賜進奉、宮廷使用的多為朱髹,太后、皇后使用的便有朱漆紅黃藤織百花龍柈子、朱漆藤坐椅、朱漆小幾、朱漆梯盤、朱漆衣匣等。據史料記載,公元1029年至1036年間,宮廷曾經三次下令禁朱漆,可見朱漆的尊貴。
到了元朝,出現了以彭君寶、楊茂、張成等為代表的著名雕漆作者。明朝的雕漆,在生產上有兩個地區的系統,一為浙江嘉興,另一為云南。明嘉靖以后的作品露出鋒棱的剔法,逐漸成為雕漆的主要風格。延續到清代,隨著竹人封氏進入北京的造辦處,以刻竹的技藝雕漆,這種鋒芒畢現的風格演變為乾隆雕漆的特點。
而剔紅的精妙之處,主要在于工匠對朱漆的處理與刀法的運用,器物通體朱紅全憑刻刀塑造結構和明暗。據記載,漆工匠僅在底子的處理上就開創了200余種錦紋,穿插在繁密的內容之間,使得剔紅展現出極為奢侈華美的一面。
暈如雨后霽霞紅
再來看紅釉瓷器,其燒成難度極大,一直是深宮之中的珍稀之器,它所體現出的皇室尊嚴和技術自信與其美學價值一道,構成了紅色的魅力。紅釉在宋代已經零星出現。北宋晚期,河南禹縣的鈞窯窯工在1300°C的高溫下,創造了強烈的還原氣氛,燒出了放射狀的紅色,這些都是純凈紅釉出現的前奏。
元代景德鎮成功燒制出了紅色瓷器,自此紅釉瓷器能夠與青釉、藍釉共同成為瓷器珍品。元代窯工在窯溫的控制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由于銅元素在高溫下極易揮發,窯室內的溫度與氧化還原時氣氛的變化,以及銅元素在釉中的含量多少,都會對紅釉的成色產生影響,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能導致色調變異。
到了明代洪武三年,朱元璋正式頒旨“以紅色為貴”,并要求宮中皆以紅色作為裝飾。洪武瓷器中紅釉的不多,但出現了大量用銅紅在釉下繪出花紋圖案的瓷器,即我們所熟知的釉里紅器。明中期以后,紅釉瓷器的技術完全成熟,永樂年間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鮮紅釉,如初凝的雞血,《景德鎮陶錄》稱“永樂鮮紅最貴”;宣德時期出現了靜穆凝重的寶石紅釉色和名貴的祭紅。祭紅又稱霽紅,紅不刺目,鮮而不過,釉不流淌,裂紋不出。乾隆在《詠宣窯霽紅瓶》中贊譽道:“暈如雨后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擬,西方寶石致難同;插花應使花羞色,比畫翻嗤更是空。”明代紅釉瓷器是皇室祭祀的主要品種,紅釉只在最高階層中使用,而對于紅釉的配比和燒成,當時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加以研究試驗。
清康熙年間,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郎廷極在署理窯務時燒造出一種高溫銅紅釉,伴有強烈的玻璃光澤,可與紅寶石并駕齊驅,被稱為“郎窯紅”。其釉水的流動性大,口沿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體釉面除開有大片裂紋之外,還有許多細小的牛毛紋,垂流部分色濃釉厚,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圍,文物界稱之為“脫口垂足郎不流”。郎窯紅的油料制作和燒成溫度難以把握,甚至有著“要想窮,燒郎紅”的說法。
此時還出現了極為珍貴的紅釉瓷器品種——豇豆紅。豇豆紅僅見于康熙一朝,專供宮廷御用,器物以文房用具為主,有水丞、筆洗、印泥盒等,器物底部均書“大清康熙年制”三行青花楷款。豇豆紅釉以紅釉中有綠色胎點為特征,是高溫銅紅釉中最難燒的一種,既需要使用還原焰燒,還要適當放入一些氧氣,極難控制。因其燒成難度大,一直以來僅為宮廷御用。
通過這些皇家的“紅色訂單”,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不僅能尋見古代造物文明對自然的探索、開發、轉化和闡釋,在千變萬化的紅色器物用度中,也能瞥見東方文明的自信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