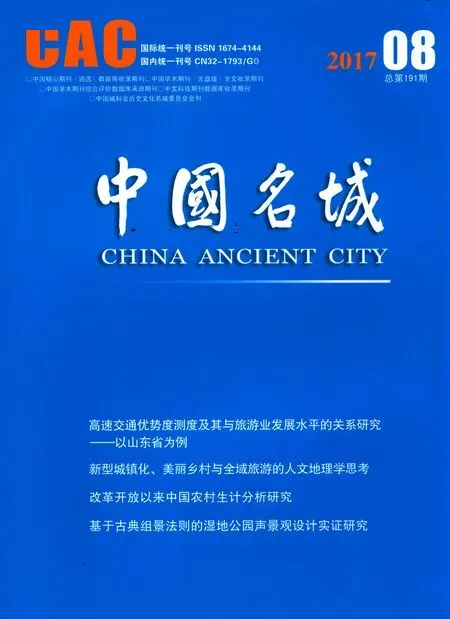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生計分析研究
高海峰 張可男 于 立 陸 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生計分析研究
高海峰 張可男 于 立 陸 琦
自2011年我國城市人口首超半數以來,城鄉人口數量差持續增長,城市擴張與鄉村衰落日益加速。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生活水平整體提高的背景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幾經起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30多年來的發展并非一味擴大了城鄉差距。通過對既往30多年的宏觀數據分析,揭示了國家宏觀政策對城鄉關系產生的重要影響,并以可持續生計法評估了城市化背景下農村的發展狀況。同時,基于運用可持續生計法評估得到的結論,對我國既往發展路徑進行了梳理,對未來農村發展與城鄉關系確立展開了基于可持續性視角的討論,為國家未來城鄉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及數據支持。
城鄉關系;農村生計;宏觀政策;可持續發展
Abstract:Ever since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exceeded half of its total in 2011,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speed of urban expansion whilst rural declining has been accelerated. However, as the livelihood improves in general, the incom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fluctuated several times, which illu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in previous 30 years did not increase the urban-rural disparity consistent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30 years’national statistical data, the paper unveils the national policies’important influence 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assess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status alongside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under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framework,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routes of China, discusses the futur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ew of sustainability,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s well as data for the futur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es.
Key words:urban-rural relationship ; rural livelihood ; national policie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研究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經濟上舉世矚目的成就,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三化”)日益鞏固并加速發展。但作為人口大國,即便在農業已非我國經濟支柱的今天,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1],但目前農村相對于城市的貧困與落后引發了社會矛盾和諸如食品安全等問題,嚴重影響了人民生計,也阻礙了我國的進一步發展。
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但“如何發展、為了什么而發展”的哲學命題,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倡下,才達成了可持續發展的共識,即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發展模式。這一定義,因其高度哲學概括而最為廣泛引用,但也因其寬泛而對現實缺乏具體指導意義。為此,學術界在既往30多年中圍繞“評估的對象”以及“怎樣評估一種發展態勢是否可持續”展開了密集研究。在國際上眾多圍繞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方法中,可持續生計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簡稱SLA)由Sen(1983)[2]、Chambers和Conway(1992)[3]等人從對消除貧困的研究而來[4]。該方法認為,生計是由資產和結構所組成的功能,是人們生存、收入、身份和存在意義的來源[5,6]。隨著各界對于貧困屬性理解的加深,以及各領域對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不斷精進,可持續生計法也在最初的模型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到了本世紀,可持續生計法已拓展成為以人為中心評估緩解貧困方案的建設性工具[7]。在過去數十年中,生計的視角已成為對鄉村發展思考和實踐的核心視角[4]。至今,SLA已被無數的發展機構(無論官方或非官方)用以評價現狀和設計、執行發展方案[7]。
我國對于城鄉關系的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多熱點、多爭論的狀態,但隨著城鄉人口拐點的到來,以及世界范圍內對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關注,近年來日益出現了城市研究成為主流的趨勢,而缺乏對農村發展狀況與發展趨勢的評估,以及其與國家整體發展關系的分析。因此,筆者以可持續生計法為分析框架,回顧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發展階段下的城鄉關系,農村在各階段下的發展狀況,以及國家宏觀政策在背后起到的作用。本文的分析結果或為國家未來城鄉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及數據支持。
2 研究方法與研究路線
2.1 研究方法——可持續生計方法
在過去30多年中,SLA模型也在持續發展,有著諸多框架,本文主要采用的是英國國際發展部門(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2000年所提出的框架,這一框架被認為是經典范式[4,8-10]。DFID對可持續生計的理解是:“只有當一種生計能夠應對、并在壓力和打擊下得到恢復;能夠在當前和未來保持乃至加強其能力和資產,同時又不損壞自然資源基礎,這種生計才是可持續的。”[11,12]SLA基本框架主要有5大要素組成,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計資本、結構與過程轉變、生計策略、生計產出,這些要素的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該理論認為,在此框架中最重要的良性反饋結果有兩方面,一是脆弱性在結構和過程變化中有所減弱,二是生計產出對于生計資本有所反哺[11],同時具有這兩點的生計即能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圖1 研究方法與研究路線圖
2.2 研究路線
城鄉關系問題與“三化”息息相關,生計的分析無法脫離國家層面的宏觀發展狀況,但由圖1可見,可持續生計框架是一個互為因果、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動態框架,從局部入手很難將全局問題討論清楚,本文篇幅內也無法將所有數據展開討論。因此,本文將框架分解到以下4個步驟予以研究:
步驟一:將“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與生計結果的相關度”作為切入點,使用線性相關度分析法,對人力資本、自然資本與生計產出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結果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發展階段進行時間分段,作為我國農村生計分析的背景。
步驟二:對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在城鄉結構和過程轉變的具體形式予以梳理;
步驟三:對國家宏觀政策制定的生計策略在農村的具體影響進行分析;
步驟四:對農村生計產出與生計資本積累間的對應關系進行了判別。
3 國家層面生計分析
國家層面的SLA分析,以勞動年齡人口、耕地面積、GDP總量分別代表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生計結果。耕地面積的統計有兩種,分別源于官方和世界銀行集團。官方在2000年前后各有一次全國國土資源普查,普查后都更改了統計口徑,故使官方的耕地面積數據缺乏連續性,因此本文中的耕地面積主要采用世界銀行集團的數據。
由圖2可知,2010年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GDP總量大致成正比,1991年后耕地面積保有量與GDP總量大致成反比,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大部分時間里,我國創造的經濟財富由人口紅利的增長與自然空間資源的消耗共同轉換而成。經對三者的線性相關度分析,可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分為7個階段(表1)。
由表1可得全國層面的生計分析結果如下:
一是,根據線性相關度與線性相關斜率,可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層面發展分為7個階段。
二是,在與GDP總量的線性相關度上,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在大部分時間都高于耕地保有面積,說明人力資本與既往生計產出的增長更為相關。第五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相關度突然下降,是受1999年開始執行的大學擴招政策影響,擴招延緩了大量勞動力年齡人口進入社會成為勞動人口;第七階段我國人口年齡發生結構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由增轉減,人口紅利效應相應大斜率減弱。
三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GDP總量的線性相關斜率在各時間段的橫向比較中,除第七階段是負關系外,其他各個時段都較前一時段有所提高,說明SLA框架中人力資本的效率在隨人口素質的不斷提高而提高。
四是,耕地面積與GDP總量的線性相關斜率在各時間段的橫向比較中,呈2000年前以正為主、2000年后以負為主的特征,且2000年后相關斜率的負數絕對值在增大,說明SLA框架中單位生計產出所消耗的自然資源越來越大。
4 我國農村生計分析
4.1 生計資本與結構、過程轉變
4.1.1 人力資本對應的結構、過程轉變
人力資本的人口數量方面,改革開放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開始松動①,但第三階段的1992年中央政府才正式對城鄉人口的流動放開②,第三階段鄉村的人口增長率下降,各地政府通過三年時間實施落地政策,城鄉人口的趨勢在第四階段的開始就發生了重大轉變,城鎮化進程加速,鄉村人口增長率由正轉負,大量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并且接下來的幾個階段中,鄉村人口的增長率不斷下降,向城鎮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最終在第七階段的開始,城鎮人口超過鄉村人口(圖3)。
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數量及從業性質方面,如圖3所示,前三個階段中鄉村勞動力主要從事第一產業或在鄉鎮企業打工,可謂“離土不離鄉”,第四個階段中國家采取財政貨幣政策緊縮[13],加上1997、9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對鄉鎮企業打擊巨大,鄉鎮企業開始大量裁員(圖3中1997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驟減),隨后鄉鎮企業的發展也缺乏后勁[14],與此同時1995年后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使得城市對配套設施建設需求增大(例如圖3中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占當年竣工面積的比例在1995年后不斷攀升),因此需要大量勞動力參與城市中配套設施的建設,從此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開始了“離土又離鄉”的生活,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這一現象使農村人力資本中實際在農村地域創造財富的勞動力數目開始劇減。
4.1.2 自然資本對應的結構、過程轉變

圖2 1978-2014年勞動年齡人口、耕地面積與GDP總量圖
第一階段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牽涉到結構的變更:耕地作為財產雖所有權一直歸集體,但聯產承包制實行后耕地的使用權由集體所有變為承包期限內歸農民家庭所有,是結構上私人財產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同時,國家政策倡導耕地的開墾(圖4),農民積極響應開墾耕地使耕地面積迅速上升這一階段自然資本的增長由結構和過程共同推動。在國家宏觀層面,這一階段GDP出現波峰段增長,且增長推動力來自于一產在產業比例結構中的增加(圖5)。
第二階段中,政策對耕地開墾依然倡導,但國家的經濟改革重心轉向城市③,建成區的面積由前一階段的負增長轉為正增長(圖6),導致耕地面積的增長速度在這一階段降低。
第三階段中,中央對前一階段提出的“八五”計劃進行了修正④,經濟增長出現波峰段增長,但這一階段一產比例不斷下降。經濟的高速增長背景下,建成區面積與耕地面積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建成區面積增長速度接近于前一階段的兩倍,導致耕地面積由前兩階段的增長轉為減少。另外,這一階段還有一個結構性的根本轉變,是中央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4,此后對于資源的調配越來越以市場為主導,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逐步退場,“五年”計劃中指令性的指標越來越少,這意味著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

表1 勞動年齡人口與GDP總量、耕地面積與GDP總量的線性相關分析結果表

圖3 城鄉人口變化與鄉村勞動力轉移圖
第四階段中,由于前一階段經濟高速增長導致了嚴重的貨幣膨脹等問題,政府開始執行適度從緊的“軟著陸”財政政策[13],加上1997、1998的金融危機,GDP的增長跌入低谷,建成區面積的增長跌至前兩個階段以下。這一階段政策一方面再次倡導耕地的開墾,另一方面通過頒布政策和修正相關法規強調對耕地的保護,使得這一階段的耕地面積有所增加。
第五階段中,雖然政策與法規繼續強調了耕地的保護,甚至“十五”計劃中提出了耕地保有量的指令性指標,但耕地的面積仍大幅度的減少,“十五”計劃的第一年耕地面積就跌至指令性指標以下(圖6,官方統計口徑對應五年計劃保有量指標),耕地減少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從谷底反彈(圖5)促使建成區面積的增長速度大幅度提升,是此前最快的第三階段的約1.5倍;二是由于2000年前政策多次鼓勵農民開墾耕地,但開墾缺乏科學規劃和指導,使許多生態脆弱區(如黃土高原地區)也被開墾為耕地,累計造成了許多生態問題,因此這一階段對“退耕還林”(或還草、沼澤)政策的強調也是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趙曉麗等人的研究[16],這一階段近4成減少的耕地是由于“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
第六階段中,上一階段耕地大幅度減少導致政策一方面更為關注耕地的保護,另一方面提倡農村將整理出來土地的優先復墾。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下,這一階段建成區面積增長速度較前一階段放慢。另外“退耕還林”一類的生態建設工程經過上一階段的大規模實施已逐步轉向成效的鞏固[15],減少的耕地中僅約兩成為“退耕還林”的措施所造成。政策強調保護耕地和復墾,建成區面積擴張的減速與生態建設的鞏固使耕地面積減少的速度有所放緩。
第七階段中,根據國家層面分析,人口紅利減弱的趨勢下經濟增長減速,雖然耕地的保護政策不斷加強但這一階段建成區面積的增長速度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快的階段,耕地面積減少的趨勢在加快。
4.2 生計策略
4.2.1 農業集約強化與規模擴大化
農業生產的集約強化和擴大化,分別選用各階段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增長速度和耕地面積保有量作為比較數據,由分析可得以下結論:一,第一階段農業的集約強化與擴大化都是所有時期中增長最大的,反映了農村生產力解中效率提高與規模擴大的并存;二,2000年前的第二、三、四階段呈集約強化與擴大化的負反饋關系,說明此階段效率與增量未能兼顧;三,2000年后各階段在耕地持續減少的狀況下,集約強化越來越受重視,并得到了顯著提升(圖7)。
4.2.2 生計來源多樣化
生計策略的多樣化由農民純收入構成比例數據來說明,根據圖8中的農民純收入構成比例,可得出以下結論:

圖4 耕地相關政策、法規與耕地保有量變化原因圖
一是,一產收入中,自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一直由農業收入為主導。縱觀七個階段,一產收入的所占比例呈波動性減小的趨勢,這一趨勢是由依賴于耕地的農業所占比例下降所引起,可見耕地作為自然資本對于農民生計策略的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是,工資性收入結合此前的人力資本與結構、過程轉變分析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段,鄉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第一、二、三階段為前一時段,后一時段為 “離土又離鄉”的第四、五、六、七階段。前一時段中,工資性收入主要源于鄉鎮企業打工,工資性收入所占比例分別在1984-1988年和1992-1995年兩段時間內出現增長,這與鄉鎮企業兩次飛躍發展的時間節點相對應,這兩段間之間是鄉鎮企業在國家整頓經濟環境背景下的調整與波折時期[17]。后一時段中,鄉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使越來越多的工資性收入來源變為進城打工,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加速擴大,同時一產收入所占比例持續減小,農民收入的非農化不斷加劇,第六階段結束時工資性收入已超過一產收入,第七階段中這一趨勢的繼續加劇使一產對于農民而言已“副業化”。
三是,收入構成中的轉移性收入比重在七個階段中呈現了由大變小再由小變大的過程,其中第一階段所占比例較大的時段和2003年后由小變大的時段,都與結構、過程的轉變有關:這兩個時段政府都通過且不限于當年的“一號文件”關注“三農”問題,另外2006年開始取消農業稅引發了結構上的轉變。
多樣化的生計策略能夠使農民在面對脆弱性背景中的沖擊時有更多的應對機制來緩解沖擊和壓力[6],但由以上三點總結來看,農村的生計策略經歷了一產收入主導、一產基礎上多樣化、工資性收入主導的過程,且工資性收入主導的趨勢仍在加強,說明農村的生計在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多樣化后又背離了多樣化的生計策略走向單方面主導。另外,農村生計策略的選擇空間上,農村本地向城鎮轉移的趨勢在加強。
4.2.3 移民
根據圖3和人力資本與結構、過程轉變的分析,第四個階段開始,向城鎮移民以獲得更好的生計成為越來越多農村人口的生計策略。

圖5 GDP增長速度與GDP的產業結構圖

圖6 耕地面積、年均建成區面積及五年計劃耕地保留面積目標圖

圖7 農業集約強化與擴大化圖

圖8 農民收入和消費構成、城鄉收入倍數關系、城鄉財富積累倍數關系圖
4.3 生計產出與生計資本的積累
4.3.1 收入增加與金融資本
收入增加水平以城鄉收入的倍數關系為代表,而金融資本實際是指農民獲得的收入扣除生存所需的消費后的積累,因此以城鄉的收入與消費之差的倍數關系為代表(圖8)。
在第一階段中,經濟改革重心在農村,生產力的解放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至改革開放以來最小時期,而金融資本積累也隨之縮小,加上農村的消費相對更低、大部分食品自給自足而無需交易成本的特點,使得金融資本積累在這一時期城鄉之間的差距已縮小到基本持平的水平,甚至偶爾農村超過城市。
在第二和第三階段中,農村居民雖在這兩個階段通過鄉鎮企業的兩次飛躍式的發展,實現了農村本地一產基礎上多樣化的生計策略,但經濟改革重心轉移至城市后,城鎮居民的收入快速攀升,導致了城鄉的收入倍數關系和收入消費差倍數關系都持續擴大,城鄉差距擴大。
在第四階段中,隨著城鎮中配套設施建設需求的增大,城鎮為吸引農村勞動力而提升了對進城打工的待遇,使得城鄉收入差距倍數關系縮小,而收入與消費差倍數關系的縮小幅度更大,原因是進城務工人員始終受自身素質和身份所限,提高了的收入仍與城鎮居民存在差距,且身處的城市中消費水平亦比農村要高,為了積累更多的金融資本,他們盡可能壓縮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雖達到了目的,但生活質量低下。
在第五和第六階段中,兩項倍數關系呈持續增大的趨勢,在2003年、2004年政府開始關注農民負擔過重、增收過慢等問題后,城鄉收入的倍數關系放緩了增大的趨勢,然而城鄉收入與消費差的倍數關系增大幅度更大,原因是進城務工人員接受了更多消費文化,生活方式亦開始城市化,生活質量提升卻使金融資本積累上與城鎮居民拉開了更大的差距。
在第七階段中,國家層面勞動年齡人口由此前幾十年的增勢轉為減勢,勞動力的緊缺使進城務工人員的待遇得以提升,因此城鄉收入的倍數關系減小,但收入與消費差的倍數關系仍在因務工人員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而擴大。
兩項代表城鄉差距的指標在前六個階段變化趨勢都相近,唯獨第七階段中兩項指標呈現剪刀差。從整個SLA框架來看,第七階段雖生計產出有所提升,但金融資本積累卻相對降低,將會影響到下一個生計循環的良性運作。
4.3.2 生活水平提高與物化資本
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物化資本積累主要選用農村消費結構數據進行分析,具體數據見圖8。
從恩格爾系數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持續降低,說明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圖9 糧食自給率、食品安全問題學界關注度圖
從消費支出的其他構成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居住消費支出是食品消費之外持續最高的部分,這造就了農村一波又一波的建房潮(見圖3農村農戶竣工住宅面積),但通過此前人力資本的分析,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在不斷降低,尤其第四階段開始負增長,但第五、六階段仍有建房潮的出現,人口下降與住房增長的剪刀差明顯不合理,具體原因是城市的房價上漲過快使進城務工人員無法在城市中購房定居落戶(見圖3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增長率),只得將收入投回農村,然而農村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設施極其有限,并沒有廣泛的消費途徑,于是只能將收入投入建房[1]。這一過程在SLA框架中是將生計產出反哺到生計資本積累時,由于物化資本不足,導致產出無法向人力資本(如圖8中文教娛樂消費始終較低)或其他資本投入,只得向物化資本中的住房建設投入。再進一步通過農民收入構成看這些積累的住房物化資本在SLA框架中的作用,由于住房與人口的剪刀差,過剩的住房中只有極少一部分通過出租(生計策略)換取了所占比例極低的部分財產性收入(圖8,財產性收入所占比例)。宏觀這一循環過程,除食品消費外的第一大消費投入產出了最微薄的收益。
由上述可得,從恩格爾系數來看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農村物化資本中社會服務等基礎設施的不足限制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在城市房價大幅上漲的協同下,造就了物化資本中住房的過度建設,阻礙了農村生計的可持續發展。
4.3.3 食品安全
食物安全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進行分析,數量由糧食自給率代表,質量方面由于作者研究方向所限,由“食品安全”為主題的各階段年均文獻數量為代表。由圖9可得兩方面結論:一是第五階段開始糧食自給率不斷下滑,最終滑落至九成以下,我國糧食越來越依靠進口;二是各階段年均“食品安全”主題的文獻篇數在第五階段開始持續大幅度上升,說明食品質量問題受關注的程度越來越高,還未能尋找到好的解決方案。結合兩方面結論,食物的數量和質量雙方面問題都從第五階段開始爆發,且在之后的階段里沒有出現改善的趨勢。
4.3.4 環境的可持續性
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1992-2012年單位農作物播種面積使用的農藥和化肥折純量分別翻了2.2倍和1.9倍。另一方面,我國化肥和農業的生產和使用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使用效率只有發達國家的80%左右[18]。
據2013、14年《中國環境年鑒》中對2011-13年主要污染物的統計數據里,COD總排放中農業所占比例分別為47.4%、47.6%、47.8%,氨氮總排放中農業所占比例分別為31.7%、31.8%、31.7%,COD與氨氮的排放中農業比例均超過工業,2012年前無農業污染物統計數據錄入《中國環境年鑒》。
由上述兩部分可見,一方面我國農業在集約強化的生計策略上持續增大投入,在投入的過程中更多的向環境索取能源與資源;另一方面,農業污染近年來才受到更多關注,在部分主要統計數據中對環境的污染甚至超過工業。環境的可持續性降低。
5 結論與展望
5.1 結論
根據研究方法中的論述,經過分步驟對生計重點指標在改革開放以來變化所做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是人口紅利與自然資源消耗雙重作用下取得的突飛猛進,反應了改革初期宏觀政策對國家生產結構調整得當,帶來生計資本部分消耗下的巨大收益。但自2010年以來,在長期耕地減少的背景下,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人口紅利也急速下跌,雙重生計資本虧損使得生計產出的減少也出現疊加效應,這說明當前的國家生產結構和生計實施過程已然不適應進一步發展的需求,急需得到深層次的調整。
二是,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結構性創新,我國在80年代初期取得了兼顧規模與效率,且城鄉協同發展的良好勢頭。但隨后長期以城市為發展核心的結構,一直未能兼顧規模與效率,農村生計策略的多樣化在短暫發展后受到全面抑制,且城鄉在發展過程中未能實現對農村生計資本的反哺,繼而在國家整體脆弱性減輕的進步之下,出現了社會矛盾與人口趨勢局部脆弱性增強的不良勢頭。
5.2 展望
從國家2015年10月宣布全面二胎政策,以及2016年以來持續強調“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都反應出國家對于當前生計脆弱性因素及生計策略問題的覺察與調整。但如本文分析所示,當前最根本的城鄉結構性失衡,城鄉生計產出反哺農村生計資本渠道匱乏的過程性問題,仍急需在下一個發展階段中做出重大調整。
注釋:
①1984年頒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1985年頒發了《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
②1992年頒布藍印戶口制度,在城鎮中買房即可落戶城鎮。
③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改革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
④1992年十四大上提出將“八五”計劃原定經濟年增長6%的計劃提高到8%~9%,同時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⑤此處食品自給率計算為,當年糧食總產量/(當年糧食總產量-糧食總出口量+糧食總進口量)×100%
[1]李立 . 鄉村聚落 : 形態 , 類型與演變 : 以江南地區為例 [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7.
[2]SEN 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M]. Lond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1992.
[4]SCOONES I.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36(1): 171-96.
[5]BEBBINGTON A. Capitals and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easant viability, rural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J]. World Dev,1999, 27(12): 2021-44.
[6]SCOONES I.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36(1): 171-196.
[7]G.ROBERTS M, 楊國安. 可持續發展研究方法國際進展——脆弱性分析方法與可持續生計方法比較 [J]. 地理科學進展,2003(01): 11-21.
[8]湯青. 可持續生計的研究現狀及未來重點趨向 [J]. 地球科學進展, 2015(07): 823-33.
[9]SOLESBURY W.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DFID policy [M].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2003.
[10]蘇芳, 徐中民, 尚海洋. 可持續生計分析研究綜述 [J]. 地球科學進展, 2009(01): 61-9.
[11]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12]ELLIS F.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王光偉. 貨幣, 利率與匯率經濟學 [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14]王先明. 走進鄉村-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發展論爭的歷史追索[M]. 太原: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5]易玲, 張增祥, 汪瀟, 等 近 30年中國主要耕地后備資源的時空變化 [J]. 農業工程學報, 2013, 29(6): 1-12.
[16]趙曉麗, 張增祥, 汪瀟, 等. 中國近 30a 耕地變化時空特征及其主要原因分析 [J]. 農業工程學報, 2014, 30(3): 1-11.
[17]劉小玄 . 中國企業發展報告(1990-2000) [M]. 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18]王永崇. 你還有什么理由不去促進化肥、農藥的科學使用 ? [J]. 農藥市場信息 , 2015(11): 17-9.
責任編輯:于向鳳
C912
A
1674-4144(2017)-08-14(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嶺南漢民系鄉村聚落可持續發展度研究”(編號:51278194)。
高海峰,華南理工大學與卡迪夫大學(英國)聯合培養博士生。張可男,卡迪夫大學(英國)建筑學院博士。
于立,卡迪夫大學(英國)地理與規劃學院高級講師,博士生導師,國際規劃研究中心主任。
陸琦,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亞熱帶建筑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風景園林系主任(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