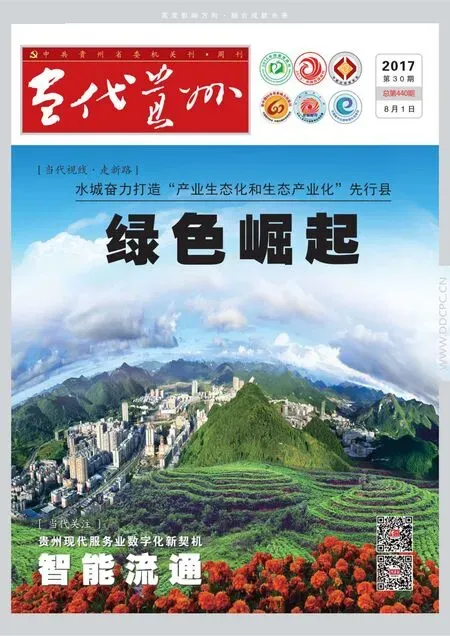秋月冬雪兩軸畫
秋月冬雪兩軸畫

梁衡
本刊顧問,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歷任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等。
文章之精,也易。精雕細刻,反復推敲就是了。難的是如行云流水,精巧而又不露斧鑿之痕。
有一種畫軸,且細且長,靜靜垂于廳堂之側。它不與那些巨幅大作比氣勢、爭地位,卻以自己特有的淡雅、高潔,惹人喜愛。在我國古典文學寶庫中,就垂著這樣兩軸精品,這就是宋代蘇東坡的《記承天寺夜游》和明代張岱的《湖心亭看雪》。
凡文學,總要給人一種美。然而這美的塑造,于作家卻各有其法。秋之美,大抵是因了那明月。和刺目的陽光比,月色柔和;和沉沉的黑夜比,月色皎潔。月光的色相大致是青的,它不像紅那樣熱,也不像綠那樣冷,是一種清涼之色,有一種輕柔之感。人們經過一天的勞作后,在月光下小憩,心情自然是恬靜、明快的。月色給人以甜美。
蘇東坡只用了18個字,就創造出了這個意境:“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庭、水、藻、荇、竹、柏,他用了六種形象,全是比喻。先是明喻,“庭下如積水空明”。月光如水,本是人們用俗了的句子,蘇軾卻能翻新意,而將整座庭子注滿了水。水,本是無色之物,實有其物,看似卻無,月光不正是如此嗎?“空明”二字更是絕妙,用“空”去修飾一種色調,出奇制勝。第二句用借喻,以客代主,索性把庭中當作水中來比喻,說“藻荇交橫”,最后總之以“蓋竹柏影也”,點透真情。這樣先客后主,明暗交替,抑抑揚揚,使人自然而然地步入了一片皎潔、恬靜的月色之中。
月光是青色的,人們在月光下尚可看到一些朦朧的物;而雪則干脆,是白色的,白得什么都沒有。花紅柳綠,山川形勝,都統統蓋在一層厚被之下。再加上寒氣充塞天地,生命之物又大都冬眠和隱遁。這時給人的感覺是清寒、廣漠、遼闊、純潔。春光有明媚的美,這雪景也另有一番清冷的美。張岱是用42個字來創造這個意境的:“霧淞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他這里沒有像蘇軾那樣借幾個形象來比,偌大個全白世界,用何作比呢?作者用直寫的手法,高屋建瓴,極目世界,突出一個白字:“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三個“與”字連用得極好,反正一切都白了。由于色的區別已無復存在,天地一體,渾然皆白,這時若偶有什么東西裸露出來,自然顯得極小。而這小卻反襯了天地的闊,天地的清闊,則又是因為雪的白和多。這正是其中的美和趣。作者是怎樣寫出這種美感和情趣的呢?他無多筆墨,而是精選了幾個量詞:痕、點、芥、粒。按照陳望道先生的辭趣之說,語詞本身就帶有自己的歷史背景和習慣范圍。這恰如一種無形的磁場。我們只要說出一個詞語,自然就能勾起人們的一大堆聯想。這痕、點、芥、粒,本是修飾那些線絲、米豆之類的細微之物的,如今卻移來寫堤、亭、舟、人。毋用多言,他們自然也就變得極小,那天地自然也就極闊了。
文章之精,也易。精雕細刻,反復推敲就是了。難的是如行云流水,精巧而又不露斧鑿之痕。這兩篇短文都是作者的隨手筆記,并不是他們的力之作。正因為如此,才現其自然之美,也見其功夫之深。文章是寫景,但都先不點景,一個寫解衣又起,一個寫駕舟下湖,使讀者隨作者自然地步入景中。蘇東坡記文與可畫竹之法說:“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寫文也應如此,統觀全局,眼前之景熟稔于心,然后用寫意筆法,一揮而成。蘇軾寫月,開頭就是“庭下如積水空明”,一下就把你推入月光之下,那竹柏影就在你的頭前身后婆娑搖曳。張岱寫雪:“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巨筆如椽,直掃天際,讓你視野與心胸頓然開闊,一飽冬雪之美。看到什么寫什么(如月光空明、天地皆白等),自然成文;想到什么寫什么(如,竹、柏似藻、荇,堤、亭、舟成痕、點、芥),順理成章。劉勰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作者是成“景”在胸之后,將景和情溶在一起,于筆端自然地流瀉出來而為文的。景不生造,情不做作。
(責任編輯 /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