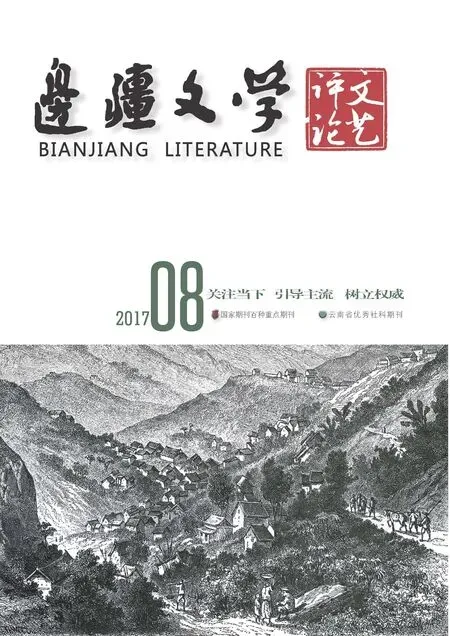余斌先生記
黎小鳴
余斌先生記
黎小鳴
我1991年秋天到云南教育學(xué)院中文系求學(xué),余斌先生時是該系教授,有幸受業(yè)于余先生。
聽余先生講授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課,是第二學(xué)年的事。但第一次聽余先生的課則是在第一學(xué)年的時候。當(dāng)時余先生為教院學(xué)生開了一次講座,我也去聽了,而且坐在前排。至今仍記得余先生那天穿一件圓口黑色毛衣,外加一件休閑西服,講一陣喝一口金屬杯里的水。依稀還記得其間喝過兩次止咳糖漿之類的藥。講座的具體內(nèi)容記不得了,大意是中國的當(dāng)代文學(xué)跟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勢不斷呈階梯狀下降一樣,呈現(xiàn)出各自的特點。近兩個小時下來,只覺得新穎別致。余先生視野的開闊,立論的宏大,脈絡(luò)的清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來拜讀先生的專著《中國西部文學(xué)縱觀》,便也就格外注意先生對“西部文學(xué)”論述的整體把握,于是明白了什么是“點”,什么是“片”。問題大到了無邊的程度,自然無從把握,無從說起;但如果沒有足夠的寬度與厚度,卻也難以看出一個人的功力與才華來。余先生從“西部文學(xué)”概念的厘清開始,直到西部重要當(dāng)代作家、作品的地域特征、精神特質(zhì)論述,以及他們所體現(xiàn)出來的整體精神、時代特點把握,宏觀、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從而“把西部文學(xué)的研究引上了真正的學(xué)術(shù)軌道”(《上海文論》1992年第4期)。而余先生這種對文學(xué)的人文地理學(xué)意義上的考察、探討、思考方式,則成為我考量一部作品,把握自己創(chuàng)作的方式之一。
后來知道余先生正在做一件其價值與意義肯定不遜于他的西部文學(xué)研究的事:西南聯(lián)大研究。
讀書期間,我并不知道余先生那時候已經(jīng)開始了這個在我看來同樣龐大的課題研究。課余時間,余先生曾帶領(lǐng)我的同學(xué)在昆明城的大街小巷里追尋講解西南聯(lián)大時期文化巨擘們留在昆明的身影,以加深大家對沈從文、冰心、聞一多、林徽因等等作家的理解與感性認(rèn)知。余先生于教,有心如此。此后不久,我就在云南的主要報刊上陸續(xù)讀到了余先生這方面的文章。
2003年,三卷本文史隨筆集《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出版。于今看來,這應(yīng)當(dāng)是近十幾年來,云南本土出版與閱讀中的一件重要的事:若要完整了解昆明現(xiàn)代(主要是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地域文化(偶及其他地區(qū)),特別是要完整了解西南聯(lián)大歷史,西南聯(lián)大與昆明城,潘光旦、金岳霖、吳宓、羅常培、沈從文、冰心、聞一多、林徽因等等歷史文化名人客居昆明的這段歷史,《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已經(jīng)成為必讀書,再也無法繞開。201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慧眼識珠,改書名為《西南聯(lián)大,昆明天上永遠(yuǎn)的云》再次修訂、增補、合集出版,也間接地佐證了我的想法。
余先生為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描繪了一幅較為詳盡的“文化地圖”。
“文化地圖”一說,是湯世杰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的序言里提到的說法。照湯先生的定位,余先生就是西南聯(lián)大群杰在云南(主要當(dāng)然是在昆明)活動地圖的繪制者。這一說法,應(yīng)該是非常準(zhǔn)確恰當(dāng)?shù)摹?/p>
余先生在《后記》中說:“我做的是半文學(xué)半史學(xué)的事”。正是這“半文學(xué)半史學(xué)”的定位,使《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具有了作為文化歷史散文的別樣藝術(shù)韻味與史料價值,也讓讀者從另一方面感受到了作者的功力、學(xué)養(yǎng)與性情。且不說余先生根據(jù)名人回憶、散文、雜文、書信、傳記甚至日記、年表、年譜等各種資料上的蛛絲馬跡,在昆明的大街小巷、郊區(qū)小村尋訪,求證當(dāng)年的當(dāng)事者活動痕跡的繁難,單查找那些資料就是一件閱讀量極大的工作。余先生以其豐富的學(xué)養(yǎng),傾十年之力,孜孜以求,樂此不疲,終于描摹出了這樣三卷“文化地圖”。其執(zhí)著耐煩,求證唯真,探討唯實,獨立發(fā)見,中正平和的精神,常讓我面對自己寫下的文字也是誠惶誠恐,心生敬畏,生怕以誤訛遺流讀者,因差錯貽笑方家,更不敢口吐狂言以博才名了。
余先生在《許淵沖的〈追憶逝水年華〉》一文中說:“我喜歡讀當(dāng)年西南聯(lián)大師生寫的散文、回憶錄,越讀越有味,覺得可以藉此追尋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精神風(fēng)貌。”
對“精神風(fēng)貌”的追尋,正是貫穿《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的一條線索。余先生的此類文章都不算長,少則兩三千字,多不過萬余言,可文化信息量的豐富,時時可見的深思識見,言盡意不盡的深情厚意,掘幽探微、力透紙背的筆下人物的心路搜尋,則比時下的很多長文章長多了。我個人以為,也正是在掘幽探微中追摹先賢,在軼聞軼事中發(fā)掘精神,在真相追尋中揭示底蘊,而這些又與一個生長于斯的老昆明人的舊時記憶相結(jié)合,使余先生的文字具有了別樣的價值,這不僅對昆明具有著重要的地域文化意義,對當(dāng)下的民族精神文化建設(shè)同樣具有現(xiàn)實意義。
余先生的寫作,十年前還集結(jié)成了《大西門外撿落葉》一書于2007年出版。收入其中的第三輯作品,同樣延續(xù)著《西南聯(lián)大·昆明記憶》的思路與情懷,但題材內(nèi)容上則超出了西南聯(lián)大的范圍,屬于單純昆明記憶的作品,如《昆明,花燈歲月》《昆明,京戲歲月》《昆明:過去的旅館》等,更多的則散見諸報刊。《大西門外撿落葉》第一輯收入了他的《對現(xiàn)實主義深化的探索》《邊疆: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重疊》《論中國女性文學(xué)縱深意識的演進》等文學(xué)論文,第二輯則收錄了《面對著云南》《讀女性散文六本——兼評于堅、湯世杰》《話劇史研究的學(xué)術(shù)拓荒——評吳戈著〈云南現(xiàn)代話劇運動史論稿〉》等對云南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盡管余先生已將他的主要關(guān)注目光轉(zhuǎn)向了文史隨筆的寫作,但作為資深的文學(xué)批評家,依然熱心關(guān)注著云南當(dāng)下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
我對余先生的文字,算是熟悉的:平和語調(diào),雅如其人,用語與口語接近,如行云流水,當(dāng)行則行,當(dāng)止則止,并無滯礙,也無故作的高深或太過用力之處。作為文史隨筆,“文化地圖”當(dāng)是其內(nèi)容,“散文”當(dāng)是其形式。地名的變化,當(dāng)年的模樣,如今的某一幢樓房的房東及當(dāng)年的住戶……躲警報,談戀愛,泡茶館……流行風(fēng)、花燈、京戲……那些在昆明生活的文化名人們的精神世界,在戰(zhàn)爭影響下如何謀生……音容笑貌、奇聞軼事……上下求索,左右佐證,娓娓道來,讓讀者如聽往年家事,有親近感覺,進而深切感受親切文字的別樣藝術(shù)魅力。
湯世杰先生在序言中說,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說話做事,親切平和,從不張揚”,確是的評。
余先生少時負(fù)笈入川,求學(xué)于四川大學(xué)。畢業(yè)后又一直在西北從事文藝編輯及理論研究近三十年。八十年代著名的文藝評論刊物《當(dāng)代文藝思潮》一度引領(lǐng)文藝思想新潮,他即是該刊主事者之一。一次家中置席待客,我請先生作陪,席間他才淡淡向客人略述了其間原由。其實也是語焉不詳。倒是后來我偶然看到一篇別人的回憶文章,才知道了其間緣由與過程。當(dāng)年《當(dāng)代文藝思潮》發(fā)表徐敬亞的論文《崛起的詩群》,引起文壇轟動,后路坎坷難行,終至于停刊。余先生隨后也調(diào)回昆明任教。作為當(dāng)事者之一,那過程里的種種感受,大約也在世風(fēng)的日愈清明中,如過隙時光,淡化在余先生的“親切平和,從不張揚”中了。
在理論批評與學(xué)術(shù)研究方面,余先生的主要貢獻(xiàn)一是西部文學(xué)研究,二是西南聯(lián)大研究。整體、系統(tǒng)地評價余先生在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就,非我力所能及。相信會不斷有人從余先生的西部文學(xué)研究中另有體會,并成為新的認(rèn)知起點;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余先生西南聯(lián)大研究及老昆明憶舊文章的新讀者。近些年,余先生依然新作不斷,諸如《吳宓先生的昆明歲月》(北京《新文學(xué)史料》),《抗戰(zhàn)時期的昆明文學(xué)》(《昆明作家》),《蔡威廉:藝術(shù)之星殞落昆明》(《云南文史》),還有《文學(xué)大師沈從文在昆明》(《云南日報》),等等,——余先生的“文化地圖”并沒有畫完,而且這版圖仍在不斷擴大,變得越來越詳細(xì)。最近又聞余先生新著《西南聯(lián)大的背影》已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喜歡余先生西南聯(lián)大研究及老昆明憶舊文章的朋友,還可以不斷看到余先生以平和中正的態(tài)度繪制的新“地圖”。
作為學(xué)生,我從余先生處得益甚多。自從調(diào)昆明工作之后,便常常或電話咨詢,或登門請教,余先生也是或委婉建議,或直言鞭策,往來至今。光陰荏苒,轉(zhuǎn)眼竟然已經(jīng)二十余載。
前年某日,我一時興起,自撰并行楷書一聯(lián)送與先生:
著述必要出己意
學(xué)問豈肯步后塵
先生展開看了一眼,默然擱置一旁。今天想起,忽然有些惶惑——或許,這是余先生留在我潛意識里的另一面的印象?但這印象與“說話做事,親切平和,從不張揚”肯定也沒什么矛盾,也許正是從這里衍生來的。想到這里,心下釋然。
(作者供職于中國電信云南公司辦公室新聞信息中心)
責(zé)任編輯:楊 林

馬立康 國畫 涼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