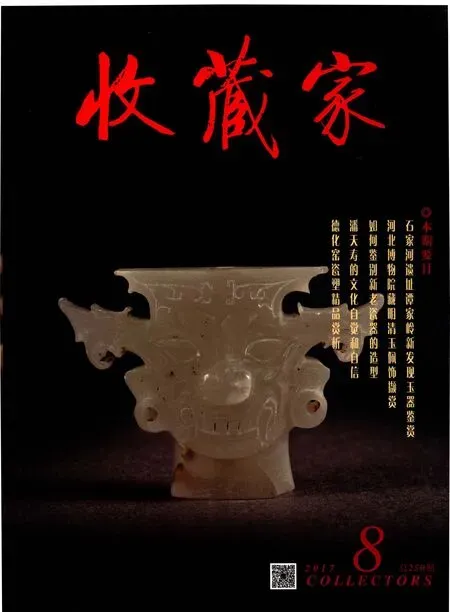大邦之夢吳越楚青銅器特展
□ 楊藝 漆躍文
大邦之夢吳越楚青銅器特展
□ 楊藝 漆躍文
西周初,太伯、仲雍奔吳,至十九世壽夢立,習用兵乘車,吳始益大,稱王。再經諸樊、余祭、余眜、僚幾代吳王苦心經營,吳國漸成春秋重要方國。及于闔閭,吳重筑都城,是為蘇州城之源。
吳楚之爭自壽夢始,互有征伐,吳越結怨也因吳楚相爭而起之。直至公元前473年,勾踐臥薪嘗膽后卷土重來,復圍姑蘇山,夫差自剄,吳國遂亡。越滅吳后,雖會齊、宋、晉、魯等諸侯于徐州,然不能正江淮北。楚漸東侵,廣地至泗上。公元前333年,楚威王興兵東伐,殺越王無彊,越國覆亡。又歷百年,楚益衰,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虜楚王負芻。吳、越、楚的大邦之夢,終歸于秦。
千年已逝,滄海桑田。大邦之夢雖遠去,故國舊物可重歸。6月28日,蘇州博物館“大邦之夢—吳越楚青銅器特展”在蘇州博物館開幕。本次展覽展出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安徽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國內22家文博單位及蘇州博物館收藏的吳、越、楚青銅器92套115件。展覽分“兵戎相見”、“禮尚往來”、“樂享天籟”、“工精技良”四部分。
一、兵戎相見—青銅兵器
戰爭是吳越楚相互關系的直接形式,青銅兵器是吳越楚爭霸會盟的真實寫照。在追逐大邦之夢的征途中,在戈光劍影的戰場上,他們常年兵戎相見,互相廝殺。吳、越兩國尚武輕死,兵器數量豐富,質地優良。楚國好勇善戰,兵器兼容并包,盡收吳越。
吳王余眜劍(圖1),春秋晚期,通長57.5、寬4.8厘米,蘇州博物館藏。劍呈“一”字形窄格,圓莖帶兩道箍,圓盤形首,劍脊隆起,寬斜從,近鋒處明顯收狹,雙刃呈弧曲形。銘文在劍脊兩側,每側各一行共75字。吳國王室青銅器存世較少,且多為兵器,但銘文極少有記事內容。本劍銘文涉及壽夢、余祭、余眜三位吳王,吳、越、楚三個國家,伐麻之戰、御楚之戰、御越之戰三場戰爭。因此,本劍是吳國王室兵器中較為重要的一件,也是目前所見先秦兵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
吳王夫差劍(圖2),春秋晚期,通長58.3、格寬5.5厘米,蘇州博物館藏。劍作斜寬從厚格式。劍身寬長,覆有藍色薄銹。劍格作倒凹字形,飾獸面紋,鑲嵌綠松石(一面已佚)。圓莖實心,有纏緱痕跡。圓盤形首,鑄有多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圓凸棱。劍身近格處鑄有銘文2行10字:“攻敔(吳)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這柄劍鑄工精致,歷經2400余年仍完好如新,無比鋒利,是迄今已知幾柄吳王夫差劍中最精美完整的一件。
越王勾踐劍(圖3),春秋晚期,通長55.7、寬4.6厘米,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劍身向外翻卷作圓箍形,內鑄有11道同心圓圈。劍身滿布菱形暗紋,劍格兩面分別鑲嵌藍色琉璃和綠松石。劍身近格處刻有2行8字錯金鳥篆銘文:“越王鳩淺自作用劍。”“鳩淺”即勾踐。楚越關系密切,楚惠王之母為勾踐之女,越國亦為楚國所滅,此劍或為越人陪嫁品,或為楚人戰利品。
王子于戈(圖4),春秋晚期,長24.3、寬11厘米,1961年山西萬榮廟前賈家崖出土,山西博物院藏。此戈同出兩件。舌形長援微翹,上下有刃,中脊隆起,下刃弧連寬胡,胡上三穿,闌、胡端截平,長方直內有一穿。戈上共有錯金鳥書7字,一面援上2字,胡部4字,識為:“王子(于)之用戈”,另一面援上一字識為:“王”字。內端錯金云紋。此戈系吳王僚為王子時器。
楚屈喜戈(圖5),春秋晚期,通長26.4、援長18.8、援寬4厘米,河南南陽八一路金漢豐商廈住宅工地M32出土,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尖鋒、寬援、有脊,援胡交角稍大于90度,胡下端為直角。援的根部有一個半圓形的穿,欄側有兩個長方形穿,內上有一個長方形的穿,內較長,內兩面均飾有紋飾。胡部鑄有銘文:“楚屈喜之用。”屈氏為楚國王族三姓之一,在楚國地位顯赫,世襲莫敖之職。此戈出土于楚申縣貴族墓葬區,說明了屈喜與申公巫臣有一定的淵源。

圖1 吳王余眜劍及銘文

圖2 吳王夫差劍

圖3 越王勾踐劍
二、禮尚往來—青銅禮器
禮儀是吳越楚逐鹿會盟的內在動力,青銅禮器是吳越楚文化交流的實物佐證。在嫁娶姻親的儀式過程中,在烹食煮酒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學習中原禮儀制度,保持禮尚往來。楚國與中原相通較早,率先禮制革新,吳、越兩國相較懸遠,自成風尚。
克黃鼎(圖6),春秋晚期,通高36.7、口徑38厘米,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嶺楚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侈口,方唇外折,長方形立耳外撇,束腰,并有兩個變形的獸形飾,腹部微鼓,平底,蹄足,耳飾三角形紋;腰部飾一周凸弦紋,其上飾一周寬帶狀蟠螭紋,其下飾兩排垂鱗紋;蹄足根部浮雕獸面。鼎內底部正中有一行4字陰文銘文:“克黃之”。

圖4 王子于戈

圖5 楚屈喜戈
楚王酓歬鼎(圖7),戰國晚期,高59.7、寬60.5、口徑46.6厘米,1933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故宮博物院藏。體圓,直口,方唇,雙立耳,深腹,三蹄足,足上端飾浮雕獸面紋。有蓋,蓋頂中心有一雙獸耳銜環(環已失),周圍有三鈕,鈕上飾直線紋。通體飾云雷紋,蓋面飾凸弦紋二道,腹上凸弦紋一道。器口沿刻有銘文12字:“楚王酓歬作鑄鐈鼎,以共(供)歲嘗。”蓋頂刻有銘文4字:“集脰攻鼎”,蓋內銘文3字:“囗集脰”。“酓歬”即戰國楚考烈王熊元,公元前262年~前238年在位。“集脰”是負責王室飲食的機構,“攻”是祭祀名稱。銘文表示這件鼎由集脰管理,以作祭祀之用。

圖6 克黃鼎

圖9 蔡侯申作媵尊

圖7 楚王酓歬鼎

圖8 上鄀府簠

圖10 工吳季生匜

圖11 曾侯與鐘

圖12 秦王卑命甬鐘
上鄀府簠(圖8),春秋晚期,通高22厘米,器口長33.6、寬23.5厘米,1972年湖北襄陽山灣取土場收集,襄陽博物館藏。銅簠蓋、體基本相同,上下對稱。整器作長方矩形,平口,直壁,下腹壁斜折,矩形足外侈,平底。蓋、器兩短邊斜壁各有一對獸首耳,蓋長斜壁上有6個獸首卡扣。通體飾蟠螭紋。蓋、器內底銘文相同,有5列32字:“隹(唯)正六月初吉丁亥,上鄀府(擇)其吉金,鑄其(瀝)(簠),(其)(眉)老(壽)無記(期),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圖13 臧孫鐘

圖14 配兒鉤

圖15 楚叔之孫途為盉

圖16 菱形暗格紋劍
蔡侯申作媵尊(圖9),春秋晚期,通高28.5、口徑23.5厘米,1955年安徽壽縣西門內蔡侯墓出土,安徽博物院藏。喇叭形口,長頸,鼓腹,圈足。口部飾嵌紅銅三角形回紋。頸下部有銘文9字:“蔡侯申乍(作)大孟姬賸(媵)尊”,是蔡昭侯申為大孟姬出嫁所做的媵器。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晚期蔡國國君,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在位。
工吳季生匜(圖10),春秋,長28.7、腹寬22.4、高16.1厘米,1985年江蘇盱眙舊鋪鎮馬橋村王莊組出土,盱眙博物館藏。器身呈橢圓形,筒形流,流上部前端浮雕獸面紋,后端浮雕饕餮紋,拱身螭龍形鋬,螭嘴銜住匜口沿,螭無足,尾部上翹。內底有豎行銘文9字:“工(吳)季生乍(作)其盥會匜。”
三、樂享天籟—青銅樂器
音樂是吳越楚古韻流淌的重要象征,青銅樂器是吳越楚藝術碰撞的承載主體。在敲鐘鳴镈的伴奏中,在句鑃錞于的擊打中,他們樂享天籟,如夢如幻。楚國的音聲悠遠流長,令人心曠神怡。吳、越兩國曲終人散,終成千古絕唱。
曾侯與鐘(圖11),春秋晚期,殘高87.2、舞修46、舞廣34.2、銑間51.2厘米,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M1:2出土,隨州博物館藏。此件銅鐘,為出土8件曾侯與編鐘中形體最大的一件。惜已殘破嚴重,僅存局部鐘體殘片,可基本復原。鐘體為扁圓呈合瓦形,在鐘體的鉦部、兩側鼓部鑄有陰刻銘文。M1:2全鐘銘文內容與M1:1基本一致,只是行款有所差別,個別字的寫法也有不同。曾侯與編鐘銘文記載了吳、楚之戰中“吳恃有眾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荊邦既變,而天命將誤”,是曾侯“親博武功”才使得“楚命是靜,復定楚王”。曾國保護了楚王,楚王便與曾侯與共立齋盟,恢復了曾國故有的疆域“余申固楚成,改復曾疆”。故曾侯與鑄此鐘以記載這段豐功偉業“擇選吉金,自作宗彝,和鐘”。銘文與歷史文獻中記載“吳楚相爭,吳師入郢,楚昭王避難隨國,受到隨國的庇護”之事相印證。此外,銘文中國名“吳、楚、曾”同文獻記載國名“吳、楚、隨”可合二為一。據此認定“曾國即是隨國,為一國兩名”。從而,破解了學術界一直以來的“曾隨之謎”。
秦王卑命甬鐘(圖12),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通高38.2、甬高10.4、銑間20.5厘米,1973年湖北枝江季家湖楚城遺址出土,宜昌博物館藏。圓柱形甬部,上部兩側分別有一鈕;鐘體呈合瓦形,平舞,鉦部共有柱形枚36個,銑部下闊,于部向上收成弧形。鐘體大部分飾有花紋,以蟠虺紋為主,間以云雷紋、绹紋、渦紋等。鐘體一面鉦部與鼓左分別鑄銘“秦王卑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共12字,該鐘銘文不全,應為一套編鐘中的一件。學界對銘文釋讀意見不一,其中較為公認的意見之一認為其大意為:︰受秦王卑(秦哀公畢)求師之命,強大的楚平王率軍至定援救秦軍。銘文可能反映了楚國出兵救秦的重要歷史事件,尤其對研究秦楚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臧孫鐘(圖13),春秋晚期,通高23.4、銑間15.2厘米,1964年江蘇六合程橋1號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該青銅編鐘同出六件,此為其中一件。長腔短鈕式,體作合瓦形,長方環鈕,鈕飾斜角雷紋,篆、舞、鼓部均飾交龍紋。鉦間和鼓部有銘文37字:經“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仲)冬(終)歲之外孫、坪之子戕(臧)孫,擇氒(厥)吉金,自乍(作)龢鐘,子子孫孫永保是從”。

圖18 蔡侯產戈

圖18 嵌錯紅銅龍紋方豆

圖17 青銅復合劍
配兒鉤鑃(圖14),春秋,通高46、柄長16、銑間17.6厘米,1977年浙江紹興越城區府山街道亭山村出土,紹興博物館藏。勾鑃主體部分似兩個筒瓦的復合狀,兩側有合脊并略向舞部傾收,截面呈橢圓形。于口凹弧形,銑角上揚,深腔,平舞。舞面中間植一扁方實柄。鉦體下端鑄飾三角云雷紋和雷紋帶,舞面飾云雷紋,柄的上端飾蟠虺紋。鉦體兩側合脊的左右邊分別陰刻篆書二行,因銹蝕僅存20余字,其中有“配兒”和“鉤鑃”銘文。
四、工精技良—青銅工藝
鑄銅是吳越楚富國強兵的基本保障,青銅技術是吳越楚高超工藝的典型代表。在鑄范成型的青銅器物上,嵌錯以金、銀、紅銅,可謂交相輝映,工精技良。吳、越兩國兵器上的同心圓首、菱形暗格紋、復合劍技藝,在當時獨領風騷。楚國首創失蠟法,青銅冶煉和紋飾裝置,實乃登峰造極。
楚叔之孫途為盉(圖15),春秋,通高25.2、口徑10.8厘米,1980年江蘇蘇州吳縣楓橋何山東周墓出土,蘇州市吳中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藏。小口,廣肩,扁圓腹,下置三蹄足。肩前后設夔龍形提梁。前有短曲形龍首流。兩側輔以蟠虺紋,填以細密的羽狀劃紋。蓋作圓盤形,蓋頂有環形鈕。蓋面密飾回紋與云雷紋組成的裝飾帶。腹部二周凸繩紋內密飾相互纏繞的蟠虺紋。肩部施一周云雷紋。腹下設三蹄足,足上部鑄獸面紋,兩側輔以卷云紋。肩部篆書銘文8字:“楚叔之孫途為之盉。”
菱形暗格紋劍(圖16),春秋晚期,通長52.4、格寬5厘米,蘇州博物館藏。劍身寬長,近鋒處收狹,前鋒尖銳。中脊線隆起,兩從斜弧。一字形平格,空心圓莖,環形式首。劍身滿飾雙線菱形暗格紋,在每個菱紋的交叉點各飾一個實心菱形紋,劍身紋飾虛實結合,排列有序,具有較強的裝飾性。此菱形暗紋與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紋飾相似。
青銅復合劍(圖17),戰國,長63、寬4.6厘米,張音濤捐贈,蘇州博物館藏。該劍呈寬格、圓莖、圓首式樣,莖部設兩道凸箍,劍格為素面。
蔡侯產戈(圖18),春秋晚期,通長21.6、援長14.6、援寬2.6厘米,1997年安徽六安城西窯廠M5出土,皖西博物館藏。寬援有脊,略上揚,前段呈尖葉狀,中后段上刃平直,下刃微向上曲,援基一小穿,胡基二穿。長方形內上二穿,前穿長方形,后穿為圓形,內兩面均飾雙鉤鳥紋。穿側胡上有錯金銘文兩列6字:“蔡侯產之用戈。”蔡侯產,即蔡聲侯,春秋晚期蔡國國君,公元前471年~前457年在位。
嵌錯紅銅龍紋方豆(圖19),戰國,通高29、口徑17厘米,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河南博物院藏。豆盤為方斗形,細高柄,圓牌狀座。蓋呈覆斗形,圓形握手。盤與蓋滿飾龍紋,并鑲嵌以紅銅。
(責任編輯:田紅玉)
Dabangzhimeng
Yang yi Qi yue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