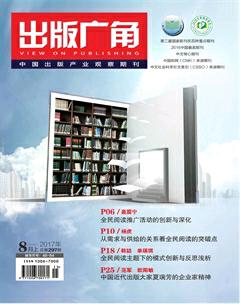我國動畫電影中的文化雜糅與趨同
【摘 要】文章以我國的兩部動畫電影《大圣歸來》和《大魚海棠》的生產制作為例,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動畫電影發展中的文化趨同與雜糅共生的狀態。全球文化傳播并不只是單向的文化運動,它包含著全球化與地域性、同質化與異質化這兩種文化力量的對峙和互動。
【關 鍵 詞】全球化;文化趨同;文化雜糅;中國動畫電影
【作者單位】徐百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喀什大學人文學院。
【中圖分類號】G240 【文獻識別碼】A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現代技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不斷“密集化”,這就是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全球化,即“發生在某一地方的事情很可能是因為距離遙遠的某一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所致”[1]。在文化上,則主要表現為某一文化現象在全球范圍的傳播。學界存在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雜糅等不同的觀點。前者認為,在資本的運作下,世界逐漸趨同化,主要表現為世界文化向強勢文化的趨同;而后者則以相對樂觀的態度看待全球化中的文化實踐,認為不同地域對外來文化的接受是帶有選擇性的,是與本地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是一種文化的混雜,即文化雜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全球化就在這一過程中產生[1]。所以,文化的發展既不是一個簡單的趨同或異化的問題,而是既存在混雜化,同時也伴有趨同化的復雜狀態。
本文將以我國的兩部動畫電影《大圣歸來》和《大魚海棠》的生產制作為例,分析這種文化的趨同與雜糅共生的狀態。雖然這兩部國產動畫電影都有不足之處,但是在目前的國產動畫電影中已經是較高水平,尤其是2015年的《大圣歸來》,得到了業界和觀眾的認可,有人還將2015年稱為中國國產動畫電影元年[2]。
一、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雜糅
1.文化帝國主義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該理論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其經濟、軍事和信息的優勢,在全球范圍內確立了霸權地位,亞非拉等地區的新興民族國家盡管獲得了政治獨立,但在經濟和文化方面仍然嚴重依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領域仍舊存在著權力的控制[3]。
在全球化的媒介市場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人員、資金等因素,本地制作商很難制作出具有競爭力的節目,因此不得不去購買發達國家生產的低價而優質的文化產品。這就導致發展中國家在節目供應鏈上被發達國家所控制,同時也帶來另外一個后果,那就是觀眾逐漸依據在發達國家流行的標準來判斷節目的質量。另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商業傳播模式也就此推廣到國際領域[4]。
2.文化雜糅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受到一些學者的批判。一些傳播研究也指出,即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單向輸出的文化產品,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經過改良以適應地方受眾的文化、消費以及社會習慣,而且不同的受眾群體對同一文化產品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地區性的文化混雜現象,如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的文化產品在區域內流行,進而出現了在全球化傳播背景下的文化雜糅。
霍米·巴巴認為,在殖民話語與被殖民文化接觸的過程中,殖民話語并不能形成單向的流動,并非完全按照本來面目灌輸給被殖民者,而是雙向的滲透與彼此互相影響。他推崇文化的流動性,認為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流動的、混雜的[5]。然而,這并不代表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無可取之處。“媒體產品在全球的流通是被少數富裕國家主宰的”,“這種貿易嚴重地限制了世界上窮人表達自身經驗的能力”[6]。這就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資本主義既促進文化同質性,又促進文化異質性;既受到文化同質性制約,又受到文化異質性制約”[7] 。
二、國產動畫電影生產中的文化雜糅與趨同
就整體而言,我國動畫產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國很多動畫的內容比較單薄,品牌競爭力不強,主要原因是內容同質,缺乏吸引力,一些動畫形象模仿歐美、日本動畫形象的痕跡過重,缺乏辨識度[2]。即便是較高水平的《大圣歸來》,也有人認為其模仿痕跡過重,而《大魚海棠》的評價更是毀譽參半。由此可知,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動畫電影發展呈現出復雜的狀態。
1.國產動畫電影創作內容的雜糅與趨同
(1)故事梗概
《大圣歸來》講述在五行山下寂寞沉潛了五百年的孫悟空,被兒時的唐僧誤打誤撞地解除了封印,在相互陪伴的冒險之旅中找回初心,完成自我救贖的故事。《大魚海棠》的創意則來自莊子名篇《逍遙游》,講述一個居住在“神之圍樓”里的女孩椿,在成人禮的巡游中出現意外,被人類男孩鯤所救,而鯤卻因此喪命。為了報恩,椿拿自己的所有換回鯤的性命,并和自己的伙伴湫在他們的世界展開了一場冒險。這兩部動畫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確實與以往的國產動畫不同,其改變了過去動畫作品低幼化的狀態,并展現了豐富的想象力,總體質量較高。但作品中的人物造型設計、動畫技術等都受到好萊塢、迪士尼以及日本動畫的影響,包括對資本市場的妥協也類似于國際商業傳播模式。
(2)動畫創作中的雜糅與趨同
首先,從《大圣歸來》的故事選取來看,它與好萊塢、迪士尼改編其他國家傳統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傳說所運用的手法一致,以大家熟悉的傳統故事《西游記》為腳本,借用原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不需要另外構筑人物角色。《大圣歸來》的主題是一個關于自我價值、成長、愛的普適性話題,結局是孫悟空拯救了被混沌捉去煉丹的小孩,并最終得到了心靈上的重生。采用普適性的內容能夠獲得觀眾的認同,這是好萊塢慣常采用的電影主題。其次,在形象的塑造上,創作者一改往常《西游記》中猴子的形象,有意將猴子的臉部夸張成馬臉;土地公卻似土撥鼠,也更像西方作品中的精靈;而山妖的形象被設計成青面獠牙,體形夸張,看起來更像西方的怪獸,而非中國神話中的妖怪。
然而,對此設計觀眾并未表現出不適應,因為中國觀眾尤其是年輕人群已經非常適應美國動畫電影的慣常風格。這種形象上的混搭在《大魚海棠》中也有明顯的體現,雖然《大魚海棠》更多地運用中國的文化元素,比如,對中國傳統建筑風格、傳統服飾、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形象等的運用,但仍有觀眾質疑動畫中的一些造型與日本動畫《千與千尋》中的畫面極其相似。所以,這兩部動畫其實都存在好萊塢、迪士尼以及日本動畫中吉卜力風格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