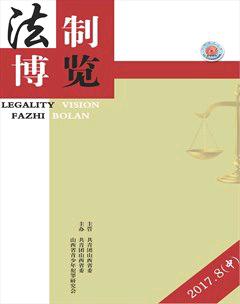先占制度研究
郝雅琪
摘要:目前無主的荒廢的物在不斷被利用發現,數量日益增多且價值顯著增大。但由于目前我國對于無主物權屬界定的相關立法不明晰,使得現實中無主物權屬糾紛案件司法實踐困難。繼2012年四川天價烏木案之后,2015新疆狗頭金事件又引起學術界的熱議。同時以民法典編纂為契機,筆者通過案例分析法和比較分析法等深入研究無主物權屬制度。
關鍵詞:無主物;權利歸屬;先占
中圖分類號:D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23-0175-02
一、引言
我國現行立法中目前并未規定詳盡全面的無主物歸屬制度,僅規定無主物一律歸國家所有。雖然在一定階段發揮過作用,但與現代社會發展情況不相適應,并且忽視個人權利,造成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沖突與失衡,由此造成實踐中諸多問題。以近年引起社會熱議的四川天價烏木案和新疆狗頭金案為例證,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案件的處理往往同案不同判,法院的態度模棱兩可,究其原因在于相關法律的缺失。值此民法典編纂之際,本文通過案例分析發現問題,以引出研究對象—無主物權屬制度,并圍繞此問題展開論述,協調好民法典物權法編和其他相關法律以及司法解釋的關系,妥當安排民法典物權法編的立法體例。
二、案例回顧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村民吳高亮在自家承包地發現巨型烏木,經專家鑒定,價值不菲市價超千萬。通濟鎮政府接到舉報后將天價烏木運走暫存,彭州市國資辦認為“烏木屬于國家所有,獎勵發現者吳高亮7萬元。”吳高亮認為烏木是在自己承包地發現應歸自己所有,于是在2012年7月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成都市中院經審理裁定駁回吳高亮關于烏木所有權歸屬問題的起訴。吳高亮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成都市中院一審裁定,駁回其上訴。①至此頗受輿論熱議的天價烏木案落下帷幕,但現行相關立法的缺失及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使得理論界仍對于烏木歸屬問題爭議不斷。無獨有偶,2015年發生的新疆狗頭金事件又一次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2015年1月30日新疆阿勒泰地區的一位牧民撿到一塊重達7.85公斤的狗頭金。新疆清河縣政府主張狗頭金為國家所有。但有學者表示狗頭金是無主物,應歸先占者,法律應尊重合法先占。從案例中可以分析得出對烏木狗頭金性質和權屬問題難以判定的根源在于現行立法的缺失,使得現實生活中糾紛不斷,往往出現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沖突。應如何完善立法,理清國有財產與公民個人財產之間的界限,避免與民爭利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烏木與狗頭金屬性分析
對于烏木與狗頭金的定性問題,學者們觀點不一,目前主要有無主物,埋藏物,礦藏,天然孳息等幾種說法。筆者現對這些觀點歸納分析,以明確其定性問題:1.“埋藏物”說:埋藏物為“隱藏或埋藏于于他物之中,而所有人不明的動產。”烏木與狗頭金符合“所有權人不明”和“動產”的特征。但要認定埋藏物必須具有“埋”和“藏”的人為行為,烏木與狗頭金是自然原因所形成,并非故意人為埋藏于地下。且埋藏物為有主物,只是其所有人不明,因而將烏木與狗頭金定性為埋藏物并不恰當。2.“天然孳息”說:天然孳息是因物的自然屬性而獲得的收益。而烏木與狗頭金是由于自然力被埋于地下的,河道或土地不具有自然孕育產出烏木和狗頭金的天然屬性,因而不可能是其天然孳息。3.“礦產資源”說:我們所知礦是具有一定儲藏規模并具有大規模開發價值的資源聚集形態,然而烏木與狗頭金并不具備此種特征,且查現行礦產資源分類細則,烏木與狗頭金并不在其列。4.“無主物”說:筆者認為烏木與狗頭金是由于自然力形成且無所有權人,結合無主物的基本特征,定義為無主物更為合理。
四、無主物權屬界定的立法現狀及缺陷
(一)現行法律規定
我國目前對無主物權利歸屬的立法主要規定在以下幾條:《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第2款,《物權法》第113條,《民法通則》第114條,《民事訴訟法》第192條。分析以上法律條文,我國在無主物權利歸屬問題上并未有明確詳細的規定,涵蓋的范圍狹小且都以“國家或集體所有”作為兜底條款,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明顯,在現代社會中屢屢凸顯其局限性。
(二)存在的缺陷
現行法律規定無主物一律收歸國家所有,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有利于將價值重大或涉及國家、社會重大利益的財產統一利用,但一味強調國家或集體的所有權就導致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沖突,忽視個人所有權的保護。例如現實生活中有人以采摘野生藥材為生,有人以拾荒為生,如果將此類行為都認定為侵害國家所有權的違法行為,否認個人取得所有權,那么國家為了微薄的經濟利益所損害的是個人的生存利益,不利于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同時這樣的權利歸屬制度削弱了人們的所有權觀念,缺乏利益刺激機制,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五、先占制度
傳統民法中對無主物規定了先占制度以明確其歸屬問題,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在其民法典中也都有先占制度的規定,但我國回避了先占制度,且現行立法存在瑕疵難以有效調整實踐中無主物權屬爭議糾紛,因充分保障村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其次,《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十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本法的實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權利”,這一條規定不應“沉睡”,筆者認為,“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違反前款規定的,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并不適宜,應將此審查權交由地方各級人大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
(二)行政驅動自治
“當下存在的‘村官大貪和不少農村群體性事件事實上是國家管控不力和社會參與不足的共同產物,他治介入自治和自治參與他治是并行不悖的。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政府承擔著重大的政策執行壓力。這種壓力也是動力,能夠一改鄉鎮政府“不出事、不做事”的行為邏輯,同時可以彌補村民自治的軟弱無力。鄉鎮政府因為掌握更多資源,可以發揮整體布局作用,科學合理規劃農村土地調整、積極推動各方議事協商、提供相應的財政支持和民生保障。必須明確的是,行政的介入是“驅動”,是“引導”而不是“領導”,要在過程中充分尊重農村村民在村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中的自治主體地位,堅決杜絕鄉鎮權力隨意“撤免”村干部等干預村民自治現象的發生。
(三)加強司法保障
既然憲法和法律規定了村民自治權,那么相應地,當村民自治權遭到侵犯,司法機關應當裁決,確認違法行為,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涉及村民自治的訴訟請求,一般不予受理,有觀點認為這樣體現了司法對于村民自治和村民集體意志的尊重。自治是法治下的自治,村民會議決議也要依法進行,村民集體意志不能成為剝奪少數人權益的正當理由。司法實踐的現狀只能導致基層群眾自治中的問題涌入“上訪”的途徑中,不能及時地解決村民自治過程中的爭議、制止違法行為。回顧2009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中涉及司法保障的條款主要有五條,村民選舉權遭侵犯、鄉鎮政權干預村民自治等情形,村民可以向基層法院提起訴訟。但由于村民自治司法保障條款將給法院系統帶來巨大壓力,最終被撤銷。筆者認為,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村民自治問題必將不斷涌現,中國6億多農民的權益需要國家承擔必要的司法成本。對于賄選、鄉鎮政權干預村委選舉、非法干預村民自治等訴訟應予受理,提供司法救濟。
[參考文獻]
[1]遲建剛.審理“舊村改造”案件法律問題研討[J].山東審判,2001.10.
[2]孫桂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不足與完善[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3]溫潤.勞動力的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79,380.
[4]徐勇,趙德健.找回自治:對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7,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