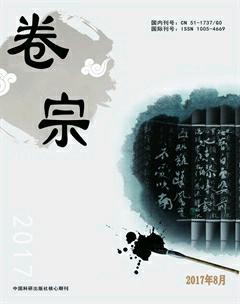論和合文化對現(xiàn)代鄉(xiāng)村糾紛解決的啟示
陳嘯
摘 要:任何制度都是民族歷史傳統(tǒng)的自然演說,作為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國和合文化理應(yīng)且能夠在現(xiàn)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構(gòu)建中尤其是鄉(xiāng)村社會矛盾解決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從和合文化的內(nèi)涵入手,闡述其介入鄉(xiāng)村糾紛解決的歷史淵源、司法價值以及現(xiàn)代啟示。
關(guān)鍵詞:和合文化;鄉(xiāng)村糾紛;調(diào)解
1 和合文化介入鄉(xiāng)村糾紛解決的歷史淵源
和合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和合思想的理念化和體系化。所謂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沖突、融合,以及在沖突融合過程中各要素、元素合為新的結(jié)構(gòu)方式、新事物 、新生命的總和。從《周易》的“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gòu)精,萬物化生”到《國語.鄭語》的“以他平他謂之和”,從《尚書.堯典》的“協(xié)和萬邦”到《論語.學(xué)而》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不難發(fā)現(xiàn)和合文化具有極強(qiáng)的超階級性,它因應(yīng)了中華民族追求和諧、和睦的價值追求,契合了蕓蕓眾生“和實生物”的思想意識。而經(jīng)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淀,和合思想已經(jīng)滲透進(jìn)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日常生活中,不同階級、派別的尖銳對立均可以在“和”的思維下達(dá)至平衡。
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奠基和影響,決定了我國不是一個嚴(yán)格三權(quán)分立、法律至上的國家,親緣、道德等因素充斥并指導(dǎo)著人們的生活。相比西方的為權(quán)利而斗爭以及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我國公民可能更希望與鄰人和平共處。尤其在人口眾多的農(nóng)村,本應(yīng)標(biāo)榜權(quán)利與自由的法律未進(jìn)入村民視野,敦厚的儒家文化、禮義廉恥卻是婦孺皆知。古代的法制史記載的嚴(yán)格依法裁決的審判極為鮮見,而人情、權(quán)力等在解紛排難和維持社會秩序中卻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是禮法合一的社會,追求和諧的和合狀態(tài)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基底。在制度層面,禮既是日常行為規(guī)范,又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在古代社會,糾紛的調(diào)解與司法判決的基本原則都是禮。
2 和合文化介入鄉(xiāng)村糾紛解決的司法價值
近年來,大量鄉(xiāng)村糾紛涌入司法領(lǐng)域,以筆者所在的基層法院為例,案件量從2013年5638件到2014年的7328件再到2015年9403件,呈現(xiàn)急劇上升趨勢。而隨著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社會的發(fā)展,蜂擁而至的鄉(xiāng)村糾紛將進(jìn)一步加劇司法負(fù)擔(dān),也為現(xiàn)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的構(gòu)建提供了契機(jī)。多元化糾紛解決是為了避免法律在司法實踐運(yùn)用上的僵化、不合時宜、失卻公正、效果不佳等弊病。它主張通過法院外的多種渠道、運(yùn)用法外靈活的多種準(zhǔn)據(jù)來實現(xiàn)糾紛解決與公平正義。而在鄉(xiāng)村社會最為典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就是調(diào)解。調(diào)解是對糾紛的化解,是對禮制秩序的修復(fù),更是社會維持自身的需要。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法律是現(xiàn)實事實的邏輯關(guān)系表達(dá),但是在鄉(xiāng)村,法律未必能與傳統(tǒng)習(xí)俗和諧相容,從而實現(xiàn)其應(yīng)有的價值。現(xiàn)實司法中“案結(jié)而事未了”的問題正是對法律原有價值的嘲笑,而鄉(xiāng)村矛盾糾紛解決的司法價值體現(xiàn)在法律與傳統(tǒng)文化交融的邏輯循環(huán)之中。鄉(xiāng)村矛盾糾紛解決的終極目標(biāo)是及時修復(fù)社會關(guān)系,防止矛盾激化,它追求的是途徑的多元化和結(jié)果的實質(zhì)正義。它并不需要得出誰是誰非的結(jié)果,只要符合雙方的利益所需,平息矛盾,有助于維護(hù)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就是一種成功。面對這種靈活和協(xié)調(diào),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法律往往會不相適應(yīng),甚至將之視為“和稀泥”,認(rèn)為有違法治精神。事實上,糾紛多如牛毛且微乎其微,若一概納入正式的訴訟程序去解決,不但耗時耗力、成本昂貴,最終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好。諸如離婚、相鄰關(guān)系等糾紛,在處理的目的上所強(qiáng)調(diào)的往往并非是非的判斷,反倒是越強(qiáng)調(diào)判斷是非,越容易擴(kuò)大糾紛,無法收拾局面,走向糾紛解決的反面。這點恰恰和我國源遠(yuǎn)流長的和合文化理念不謀而合。
3 和合文化對鄉(xiāng)村糾紛解決的啟示
鄉(xiāng)村社會中的諸多糾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看主要是利益糾紛和宗族糾紛,而不純粹是法律糾紛,僅僅運(yùn)用法律去解決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故此筆者以為,應(yīng)當(dāng)從多元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鄉(xiāng)村矛盾糾紛調(diào)解中現(xiàn)代法律與傳統(tǒng)文化的功能和價值,并為鄉(xiāng)村倫理與權(quán)利自治預(yù)留更多的空間,同時,將和合文化諸如天理、人情、倫理、習(xí)俗等融為一體協(xié)助法理解決糾紛,讓不同類型的糾紛解決方式互動互補(bǔ),充分發(fā)揮固有功能并共存發(fā)展。
在糾紛解決機(jī)制的建構(gòu)上,國家應(yīng)當(dāng)堅守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根據(jù)各地具體情況適當(dāng)分流暢通糾紛解決渠道,同時,讓民眾和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糾紛解決機(jī)制的生成和創(chuàng)制過程,并依據(jù)理性人的偏好選擇不同的糾紛解決途徑和方式。以和事協(xié)會為例,由于土地資源稀缺,民風(fēng)彪悍,灘涂、宅基地糾紛頻發(fā),如何化解村民糾紛,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一直是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往政府僅僅依靠宣講法律法規(guī)和依法管理的剛性方式,但一直未能妥善解決糾紛,由此和事協(xié)會應(yīng)運(yùn)而生。根據(jù)鎮(zhèn)里實際,該協(xié)會專門聘請了部門站所的工作人員、村干部等在當(dāng)?shù)鼐哂幸欢ㄍ⑸鐣绊懥驼{(diào)解說服能力的人擔(dān)任理事,與熱心調(diào)解素養(yǎng)較高的村民組成完整的網(wǎng)絡(luò)。一旦出現(xiàn)村民糾紛,由村民自行選擇調(diào)解員進(jìn)行調(diào)處。如今和事協(xié)會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shù)厝嗣裾{(diào)解的重要組成部分,處理的案件實現(xiàn)了零上訪,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均得以保證。
作為實現(xiàn)社會控制的糾紛解決機(jī)制,一方面要著眼于糾紛的解決,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糾紛的預(yù)防。正所謂“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和合文化熏陶下的古代傳統(tǒng)糾紛解決機(jī)制十分突出和強(qiáng)化教化功能。為此,必須發(fā)揮司法的能動作用,重新審視和定位司法的功能。加強(qiáng)司法行政部門之間的合作,積極指導(dǎo)和培訓(xùn)各種非正式的糾紛解決組織和個人,特別要加強(qiáng)對農(nóng)村基層調(diào)解員的指導(dǎo)和培訓(xùn)工作。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裁判者、仲裁者、調(diào)解者等應(yīng)強(qiáng)化道德倫理的教化功能。在平息糾紛雙方不滿情緒和復(fù)仇激情的同時,加強(qiáng)對糾紛當(dāng)事人的思想教化,比如勸惡從善、弘揚(yáng)誠實信用等良好道德風(fēng)尚。在糾紛解決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灌輸倫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法與情、理的有機(jī)融合。這既是提升糾紛解決的權(quán)威性、公信力、親和力,也是避免一些“民轉(zhuǎn)刑”糾紛態(tài)勢升級的有效手段;這既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應(yīng)有之義,也是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和諧無訟,調(diào)處息爭。這不僅是中國傳統(tǒng)司法文化的追求,也慢慢成為世界其他國家多元解紛的理念,為世界人民所共享。在未來的司法和社會改革的道路上,完善中國模式的多元解紛機(jī)制應(yīng)注重立足于當(dāng)下,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切忌全盤否定與照搬全收,唯有如此才能讓中國的多元解紛之路越走越寬廣,越來越賦有生命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