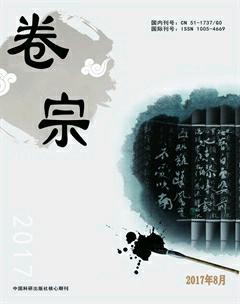晚明江南城防建設中的市民參與
摘 要:晚明倭亂頻仍給江南帶來極大騷擾,曾經因久居安定、無城可守的江南開始了大規模的城防修繕活動。江南城鎮中富戶市民的大力支持,彌補了國家筑城經費不足的問題。以官民結合的籌資方式筑城,也使市民力量在城防修建的過程中得以體現。正是在政府主導,民眾支持響應的共同合作中,江南建立起自成一格而又兼顧全局的備倭城防體系。但是,在筑城和修繕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弊端,屢修屢廢,惡性循環,民力的耗費現象顯著。相較于倭寇劫掠,政府采取的修建城防這項備倭政策對于江南市民的生活以及市鎮經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倭亂;市民;江南城防
中國古代傳統城市在建立伊始便與軍事緊密相連,除了鞏固政權外,抵御外敵侵擾無疑是城市加強防御設施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自古多強鄰,邊境城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遏制內亂的未雨綢繆之心也使得各級地方對城防工事不敢懈怠。宋代以來,江南城市和市鎮的市場和經濟職能日益突顯,其軍事防御能力和防御意識都相對弱化。這種狀況,一但遭遇外來侵略或者沒內部叛亂引發的動亂干擾,必定會給城市生活帶來嚴重影響。明代的倭寇劫掠東南便是其中一例。明代后期的倭亂與江南城防建設力度的加強因果相連,在城防建設中,市民力量的體現也是市鎮發展中值得關注的內容。
有關晚明倭亂的研究主要有倭寇大舉侵犯東南沿海的原因、倭寇群體的構成、倭亂對江南社會的沖擊等方面的分析,典型的如: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童杰《“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等。一些學者關注到倭亂威脅下的城防建設,他們主要從軍事史的角度對這一時期的城防加以評析,如:張德信《嘉靖年間海防重建與倭寇潰敗——兼及中日關系變化與斷絕》,李俊清《明代城防的寶貴經驗——論劉以守〈乘障瑣言〉》等。還有學者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出發,探尋江南的城市規劃及發展問題,如:蔡志鵬《明代倭患背景下的閩東地區城市地理研究》,馮賢亮《城市重建及其防護體系的構成——十六世紀倭亂在江南的影響》等。而城市建設與市民群體必會受到倭亂其影響,目前對于市民群體的研究主要關注了市民階層的興起發展以及市民文化、市民社會諸問題,如:馮賢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階層及其社會影響》,陳國慶《市民視野下的明代商人群體研究》,吳迪《明代后期江南城鎮的群體抗議事件》等,對于市民力量在整個社會運作中的參與還有待完善。
城防是城市、市鎮等的自我防衛,即使在城市經濟文化功能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其自衛功能也應當是必不可少的。明代倭寇頻繁劫掠東南沿海,選擇這一地區必然經過一番思量,除了江南富庶的物質吸引之外,或許當地相對薄弱的城防力量也給了倭寇以可乘之機[1]。本文試圖以晚明倭亂頻發這一歷史現象為背景,著重關注江南省屬州縣的城防建設,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探尋城防建設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市民力量,以及當時大規模興修城防對于市民生活和市鎮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1 晚明江南大興城防的背景
本文所述及的江南地區大致指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以及錢塘江流域,也即明代的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鎮江、杭州等地。嘉靖、隆慶以及萬歷年間,江南地區可謂倭亂四起,據馮賢亮對明代各朝的倭亂數量分布統計數據,僅嘉靖一朝江浙地區的倭亂次數已經占有明一代當地倭亂總次數的八成以上。[2]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江南城鎮在歷史上比較缺乏強大的城防意識,現實中的城防力量并非經歷多代沿革,固若金湯。早在宋代,司馬光就曾說,吳越素不習兵,常少盜賊。[3]可見其戰守意識的薄弱。明初,倭亂基本平息,江南幾乎在安定的穩步前進之中走過了一百余年,以至江南各地的城池或者頹廢不存,或者尚未建立。萬歷《嘉定縣志》載徐學謨《筑城記》,其中寫道“大江以南,邑多無城者,即有城,鮮堅致宏麗也”[4]。不僅是嘉定,江南地區城防松懈、武備廢弛的情況普遍存在。嘉善縣在倭亂筑城之前就沒有城池,史載“嘉善故無城,盜寇鮮警”[5]。又如靖江縣,明成化年間的靖江縣依舊是“衙門草創,且無城郭”[6]。嘉靖二十一年初設青浦縣時也是如此[7]。在這樣的情況下,遭遇倭寇侵擾的江南地區發起城防建設運動,從縣級基層治所起,甚至從最基層的鎮市開始,全面地建設城池防御設施已是迫在眉睫。
以敏銳的政治軍事嗅覺感知到這一點的是守土有責的地方官員。地方志中有關筑城歷史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實例。面對嘉善無城可守,倭寇侵擾不斷的局面,嘉靖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王忬與知府劉愨議請筑城,且得到了中央首肯,于是嘉興城防在歷經五個月的修繕后竣工。[8]嘉靖三十三年,時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鄭曉上奏,祈請皇帝念及江南沿海“財賦重地,漕運要津”的地位,針對“如皋、海門二縣與通、泰二州相為唇齒”的地理局勢,闡明倭盜出沒無常,幾個重要地方均無城池防守,他們提出筑城備倭,“內則聯絡通、泰,外則葆聚鹽場,且于淮、揚二府亦有藩籬之固”的好處,這些建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皋縣士民筑城以備倭患的愿望。[9]另外的例子是,當時地勢“切近長江,密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的要地瓜州,面對倭寇進擾,也是“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眾”,嘉靖三十四年,他們提出修筑城垣以備倭患的建議,不僅獲得了皇帝的批準,也受到了各級官吏的積極支持。揚州知府吳桂芳也親臨瓜州,相度地利,參與設計營堡墩臺。[10]與之類似的由地方官員上奏而起的筑城案例還廣泛的存在于江南各地。
2 市民力量影響下的江南城防建設
在地方官吏據實奏請,中央政府積極回應,江南各地開始啟動一場大規模筑城運動的同時,民間力量的參與也不容忽視。一方面,伴隨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群體的擴大以及市民意識的覺醒,明代江南城市的市民已經成為參與社會活動的極為重要的群體。他們擁有自主的人格,在地方經濟、社會與文化建設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防御性的城池建設在帶給地方安全穩定的經濟環境的同時,在交通、稅收、市場設置和物流等方面也會影響市民經濟和社會生活。
面對倭亂沖擊,亟需加強防御,而江南民眾對于大興城防的態度卻不盡相同。嘉善縣初建城防時,便有“嘉善久襲承平,民不知警,聞大役而不樂者有之”[11]的記載。這種反對意見的存在或許不僅僅是因為突如其來的徭役,還有他們一直以來沒有城墻的習慣。市與鎮界限的模糊并非一朝一夕,卻要在朝夕間將這界線劃得涇渭分明,的確不是那么容易被民眾接受的。在明朝洪武時期,上海建城初期的記載中曾描述上海由鎮升格為縣時本無城,在準備修城時又面臨 “無遺址可因,其勢頗難”[12]的問題。新筑城既無傳統可依,又無舊址可循,草創開局的難度可想而知。endprint
城池建設是一項浩大的公共工程,不僅所需資金巨萬,還必然會耗費民力,勞役久長。這是主政者和地方居民都必定關注的大問題。大舉建設城防所需的竹木、磚石以及修筑工匠必定伴隨著巨額開銷。從史料記載看,江南各地筑城經費構成包含三個部分,第一是這來自中央撥給的經費,如崇明縣在嘉靖三十四年修筑磚砌城垣時,由巡按周如斗“奏請帑金四萬兩”[13]。第二部分是地方財政支持,如皋、海門二縣城防建設時,如若經費不足“聽本官將可緩錢糧下量行動支”[14],這是動支地方財政支持城池建設的例子。第三部分是民間籌資。尤其是當中央撥給不足以支持城防開支的時候,民間籌資的力量愈加凸顯。嘉靖三十四年,嘉善縣修繕城防共支出三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兩九錢白銀,當時實際參與的公帑僅有二萬兩,地方官員采取了“其余照丁田派征諸民以助役”[15]的辦法從民間獲得了絕大部分的經費。顯然,當時江南各地的筑城活動是一場由政府、民間合力籌辦的大規模城市公共行動。
倭患猖獗,對于筑城御倭事業,士紳富戶慷慨解囊、大力相助的也不在少數。畢竟筑城對于抵御倭患本身是還有積極作用的。一些相反的例子也能證明筑城御倭對捍衛家園的重要性。浙江慈溪的百姓曾經反對筑城,但是當真正遭遇倭患深擾之后,他們追悔不已,《國朝典匯》中有這樣的記錄:
倭入慈溪:初,王忬在浙,令兩浙諸縣皆筑城自固,獨慈溪士人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柳東伯不知所御,攜印組走匿。倭殘殺人民無算,縉紳被禍尤慘,始追悔不城為失。[16]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面對倭寇的強勢劫掠,比普通民眾遭遇損害更為嚴重的是縉紳大戶。這也是許多大戶積極支持城防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的影響不容小覷。嘉靖三十一年,江陰縣修繕城防時,“義士黃鑾輸銀六千,造城三百余丈”[17],且城防建設完備,以至“倭至,民得無患”[18]。嘉靖三十二年,常熟重筑縣城,不僅有富戶譚曉“輸四萬金”[19]以助城防,更有邑人王魯,“獨任西城之役,自阜成門至鎮海門,數百丈一力成之”[20]。這里當然不是指他一人修筑,而是王魯一戶承擔了整個西城數百丈城垣的筑城費用。無論是義輸銀錢造墻百丈,還是一力承擔獨筑西城,這樣的開支顯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小戶能夠負擔的。
在政府統籌主導,民眾積極支持參與,官民合作共同努力下,江南地區廣泛地建立起了成體系的城防設施,抵御倭亂擾害。這對于維護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有積極的意義。中國古代城市與地方行政等級關系密切,城防城池也可以根據行政層級的不同區分為若干等級。有集軍政一體的省級府州城市,包括各府治及直隸州治;有相對次之的省屬州縣,包括普通縣治以及非直隸州治;還有各地巡檢司、守御衛所等治所。[21]或許當時江南各地城防在建立伊始并沒有直接考慮到整個江南抗倭的戰略部署,然而在各地城防修筑過程中究山河、因地利的布局思慮之下,犬牙交錯、唇齒相依的城防體系逐漸呈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既有官方主持籌劃的作用,也要注意到民間力量的廣泛參與對城池建設的影響。
3 市民參與城防建設的社會影響
在倭亂頻繁的形勢下,江南大興城防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保境安民的作用。清代的常熟縣邵北虞祠還在紀念明代為防倭亂積極筑城的北虞邵公[22]。瞿式耜曾講述他筑城御倭的歷史事跡說,當時在“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的情況下,北虞邵公極具遠見卓識,心懷宗國百姓,不顧邑侯反對,力排眾議,“壘石陶磚,干陬雉堞,跨高山以臨水,屹然作御寇金湯。”他的未雨綢繆沒有被辜負,時過不久,“倭寇果至,蒼野王公出戰殉身,而邑中數萬生靈獲享生全。”[23]對于地方官員,守護一方生靈的任務他完成得很好;對于城防設施,抵御外敵入侵保全境內黎民的作用也已然實現。然而城防建設對于整個江南社會的影響卻沒有就此止步。
在江南城防建設的過程中,民眾的廣泛參與也讓政府對市民力量有了新的審視。在籌集筑城資金方面,中央對于官民共同承擔城防開支的做法持肯定態度。嘉靖三十三年,在鄭曉提議興修如皋、海門二縣城防的批復中便說明,如若經費不足,可以“相度地方緩急漸次修筑,其余不敷之數亦聽本官將可緩錢糧下量行動支”[24],給予地方相應的財政自主權。同時還有“各該州縣廉干正官務要多方設處,或勸貸富家出給工食,或借債貧民暫勞筋力。”[25]借助民力興建城防的建議,可見政府對于民間力量的重視。
但城防建設過程中也存在一系列問題。興建城防事關賦役錢糧,加之事從權宜,“主事者若貪墨營私,則往往勞民傷財”[26]。加之修繕質量不過關的問題,城防屢修屢廢的現象時有發生。萬歷二十年重修嘉善城防,當時曾對嘉靖三十四年的筑城情況有這樣的評論:“城始筑時,倉促從事,規制卑隘,日就傾圮”[27]。這對于民力的耗費顯而易見。而新城縣知縣范永齡“清介質直”、體恤貧民,“倭亂筑城,計貧民無經費,乃借富豪之寄”[28],收到了所謂“民不知擾”的效果。富戶出資,貧民出力的安排看似合理,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富戶私有財產的增殖。同時貧民出力修城也會將勞動力從生產領域的部分抽調,加上時廢時修的力役干擾,對市鎮經濟的發展而言也存在阻礙,因此干擾晚明江南經濟的不僅是前來劫掠的倭寇,筑城設防的力役、經費消耗也不容忽視。
對于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我們雖然無法完整地得知城防對于百姓個體的影響,但是在他們的眼中,那厚實的城墻與水柵,或許既是保家護院的屏障,又是妨礙穿行自由的籬墻、阻滯商業流通的屏障。城墻建設對于晚明江南市民生活和市鎮經濟的這些改觀所引起的社會反映,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我們往往歸咎于頻繁的倭患,或許相較于來去無常的倭寇,明政府針對倭患所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更為深遠持久。這種政策本身在執行之后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心照不宣的規則,有力地影響著他們未來的行動決策。
參考文獻
[1]馮賢亮:《城市重建及其防護體系的構成——十六世紀倭亂在江南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月。endprint
[2]馮賢亮:《城市重建及其防護體系的構成——十六世紀倭亂在江南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月。
[3](明)黃淮:《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七,明永樂十四年內府刻本,第25頁。
[4]萬歷《嘉定縣志》卷三,明萬歷刻本,第4頁。
[5]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二,光緒十八年刊本,第13頁。
[6]嘉靖《新修靖江縣志》卷八,明隆慶三年刻本,第5頁。
[7]萬歷《青浦縣志》卷一,明萬歷刊本,第35頁。
[8]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二,第12頁。
[9](明)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二《淮陽類》,明隆慶五年項氏萬卷堂刻本,第34-35頁。
[10](明)鄭曉:《端簡鄭公文集》卷十,明萬歷二十八年鄭心材刻本,第55-56頁。
[11]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二,第13頁。
[12]弘治《上海志》卷一,明弘治刻本,第7頁。
[13]康熙《重修崇明縣志》卷三,清康熙刻本,第2頁。
[14](明)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二《淮陽類》,第35頁。
[15]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二,第13頁。
[16](明)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百六十九《兵部》,明天啟四年徐與參刻本,第48頁。
[17]光緒《江陰縣志》卷一,清光緒四年刻本,第6頁。
[18]光緒《江陰縣志》卷一,第6頁。
[19]康熙《常熟縣志》卷三,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2頁。
[20]康熙《常熟縣志》卷三,第2頁。
[21]馮賢亮:《城市重建及其防護體系的構成——十六世紀倭亂在江南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月。
[22]康熙《常熟縣志》卷四,第42頁。
[23](明)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十《雜文》,清道光刻本,第3-4頁。
[24](明)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二《淮陽類》,第35頁。
[25](明)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二《淮陽類》,第35頁。
[26]孫兵:《明代湖廣地區城池修筑研究》,武漢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27]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二,第14頁。
[28]乾隆《杭州府志》卷七十八,清乾隆刻本,第29頁。
作者簡介
索蓉(1992-),女,漢族,山西太原,大學本科,研究方向:中國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