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與孤獨:朱文穎筆下的南方世界
李 曼
曖昧與孤獨:朱文穎筆下的南方世界
李 曼
關于南方的記憶和想象其來有自,相對于與正史緊密相關的北方,南方似乎總是游離于正史之外,長期處于政治的邊緣地位,然而也正是這份“邊緣性”,使得它獨立于政治之外,開辟出一條獨特、瑰麗的文化之路。說到南方,人們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南渡、南遷、偏安等與政治掛鉤的詞匯,但同樣也會想到楚辭章句、六朝駢賦、昆曲評彈、明清小說等文學藝術現象。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后者可能更接近真實的南方,這種獨立、自足的文化傳統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巨大魅力,培育出一代代作家,也吸引著一批批文學愛好者。在當代文學中,著力書寫南方的有蘇童、葉兆言、余華、格非等作家,蘇童筆下的南方衰落、破敗、頹廢、死亡氣息濃重,葉兆言則在人物選取和文學地理上都充斥著南方氣質……事實上,從古至今,南方詩性的、頹廢的、浪漫的文學傳統一以貫之,朱文穎正是在此傳統上繼續發揮,以上海和蘇州兩座城市為依托,塑造著自己心目中的南方世界。在她的筆下,南方有著明朗的曖昧,更存在著隱匿的孤獨。
一、明朗的曖昧
小樓東風、閑庭落花、芭蕉夜雨,南方通常以這樣的姿態走入人們的視野,溫情而浪漫,憂郁又感傷。與此普遍的認識相適應,朱文穎的南方世界唯美、精致、古典,在人物呈現、意境營造和語言文字的把握上都明顯表現出“曖昧”的狀態。學者王彬彬說“‘曖昧’,是朱文穎小說的基本品格,或者說,是朱文穎小說基本的美學特征。”
她這種曖昧品格的形成一方面與其所處的文學地域和女性自身的纖細氣質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她選取的意象有關,在她的作品中,“雨”和“狐”兩個意象反復出現,凸顯了曖昧的本色,但這種曖昧又是明朗的、磊落的,不是想透故意不說透,而是作家本身就沒有想透的。朱文穎小說中多次寫到下雨,如“雨一點都沒有變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像一張網,也像無數的銀針。太陽卻是耀眼的,有著灰色的襯托,它忽然顯出明晃晃的亮度……一時間三白也有些呆滯,看著眼前的光影晃來晃去,街巷頓時就有著不真實的意味了,仿佛整個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與物都籠在其中了。”(《浮生》)“雨”成了朱文穎小說中人物活動和故事展開的背景,她筆下的雨絕不是疾風暴雨,也不是傾盆大雨,而是細細密密的小雨、微雨,這種雨下也下不大,但也不會停,就那樣綿綿地溽濕著城市的空氣、作品中的人物和讀者的心情。
與“雨”同樣重要的一個意象是“狐”,《浮生》中第一節標題即為“狐”,文中也多次提到狐貍,如“狐貍?三白皺皺眉頭,心想,三天兩頭的老提狐貍干什么!蕓娘什么時候也變得那樣神神鬼鬼的呢?他們以前可是從來都不這樣講話的啊。”“一講到狐貍,那就說明在三白與蕓娘之間已經發生了一些講不清楚的事情。狐貍就是講不清楚的事物的代表。至少在于三白看來是這樣的。那么,再換一個角度來講,也就是說,三白與蕓娘的關系,在不知什么時候已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這里,“狐貍”仿佛成了介乎三白和蕓娘之間的第三者,但它是否真正存在卻是模糊不清的,作者借助狐貍的似有還無、若隱若現、若即若離引導著我們穿越迷蒙的氛圍和敘述的表象,洞悉隱藏在其后的人們隱秘的內心世界。在我國的文學傳統中,“狐”本身就是曖昧的代名詞,朱文穎對這一意象的選取是有意識的,并且也做到了使其與作品的氣質相映成趣、珠聯璧合。
由于對“雨”“狐”等意象嫻熟的運用,使得她特別擅長氣息的營造,平淡的故事經由她情思的點染,往往在超越故事之外升騰起一股“氣息”,迷離曖昧,如真似幻,余味悠然,讓人產生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作家在不確定的情感漫游中的一個替代符號的錯覺。可以說,朱文穎這種文學品格與南方自有的精神一脈相承,無怪乎張清華會說“江南那古老、絢爛、精致、纖細的文化氣脈在她身上獲得了新的延展。”
二、“局中人”的孤獨
關于孤獨,朱文穎自然有著自身的理解,如果說她作品中的“曖昧”是明朗的,一眼即可看穿的,那么“孤獨”便是隱匿的,只有穿越表層才能發現其實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孤獨的,無論是作為物質時代的“局中人”還是脫離時代的“局外人”都無法逃脫孤獨的宿命。
與文明的進步相伴隨的往往是人的物化,朱文穎對此懷有深深地警惕。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上海這一城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朱文穎的《高跟鞋》和《戴女士與藍》故事發生的背景均為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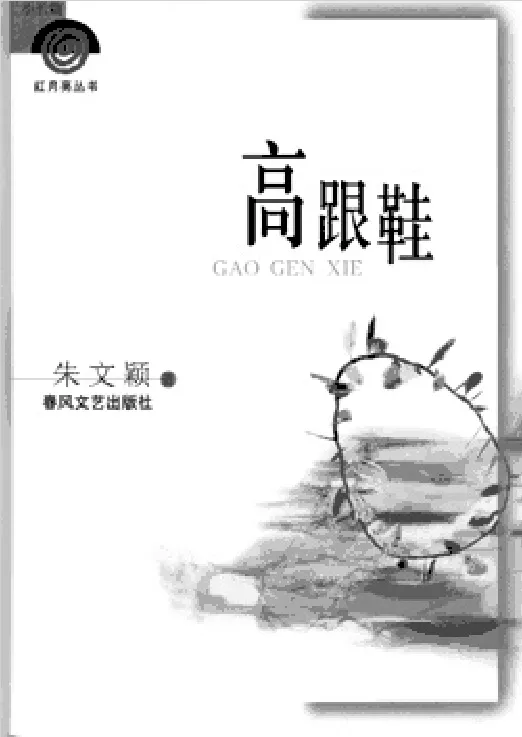
《高跟鞋》
《高跟鞋》從兩個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女孩——安弟和王曉蕊在上海十寶街的經歷入手,寫出了她們在日益強大的物質誘惑面前的希冀向往與矛盾不安,從而揭示現代都市人在物質大潮沖刷下的心靈特征和精神秘密。安弟和王曉蕊有共同的東西,她們都喜歡漂亮的事物,都不安于現狀,都喜歡錢,但二人也有明顯的區別,“年輕漂亮的太陽一樣的”王曉蕊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她可以接受無愛的性并坦然接受由此帶來的物質享受,而安弟則復雜一些,她追逐物質,但也并未放棄對精神和愛情的追求,試圖通過物質到達一個自己都說不清的所在。她喜歡外婆生活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喜歡超拔孤獨的大衛,認為自己了解他,可以帶他走出孤獨,但后來才發現大衛對生活的懷疑和絕望,遠遠高于她原來的猜想。在物質節節勝利的時代,無論是作為現實主義者的王曉蕊還是理想主義者的安弟都注定要碰壁,王曉蕊被情人拋棄,安弟最終也還是孤身一人,對她們來說,與廣闊的物質相對的是更為廣闊的孤獨。
《戴女士與藍》第一人稱敘事者“我”是一個赴日打工同時又沉湎于過去無法自拔的中年男人,在日本期間與一個同樣來自中國的女人在日本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穿上魚的衣服,分別扮演“辛巴”和“星期五”(兩條白鯨的名字),并在相應的時間作為魚互動,但二人卻從未真正見過面。“我”1994年回國,三年后認識女友陳喜兒,又三年后認識陳喜兒的游泳教練戴女士,當“我”認定戴女士就是在日本期間的“星期五”時,她卻極力掩蓋與否認,再加上樹懶一樣粘人的女友陳喜兒的自殺使“我”陷入絕望之地。過去無法確證,現在又萬劫不復,只能陷入深深地孤獨。
在外人眼中,赴日總是光鮮亮麗的,所以不管是去國前還是回國后,都有一群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去“紅房子”吃飯,去機場接送,然而并沒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隱匿的孤獨,去國離鄉的孤獨,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孤獨以及不能作為人存在的孤獨。在一次電視臺的訪談節目上,一個禿頂教授文縐縐的大談特談孤獨,說“所有的現代人都是孤獨的。有一首歌,叫做《亞細亞的孤兒》,它講的也是現代人的這種孤獨。當一個人遠在他鄉的時候,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葉孤舟。”而只有真正經受過孤獨的人,比如“我”才會知道,“什么孤舟不孤舟的,根本就是放屁!我理解的孤獨,很簡單,就是一個人,他穿著一條魚的衣服,在水里面漂。”而后,“我”對孤獨有了更深的理解,“孤獨,就是一個人,他穿著一條魚的衣服,但后來當他把這衣服脫掉時,發現自己其實還是一條魚。”
物質極其豐富的現代“局中人”精神卻遭遇了巨大的孤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悖論,朱文穎即是在對這一悖論的揭示中顯示出了她對現代社會物質與精神之關系的思考。
三“局外人”的孤獨
最能代表這類“孤獨”的作品是《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這部長篇小說以回憶式的結構展開,敘寫了從上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前10年家族三代隱秘的歷史以及那些南方底色里的種種人生和命運。包含這樣長的歷史跨度,卻稱之為“細小”,似乎有些矛盾,其實不然,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有意避開宏大的歷史敘事,采用的是一種“‘私人場景’與‘宏大歷史’之間迎面相遇又迅速躲開的交錯方式”。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文中的時代編碼,如童莉莉填寫成分、潘先生不斷地抄寫毛主席語錄、公私合營、大躍進、改革開放等,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沒有匯入到歷史的大潮中,而是處處顯得格格不入,是形形色色的孤獨者。
比如“我”的外公童有源,他“出生在京杭大運河蘇杭段的一艘木船上。在中國最美麗富裕地區的一個大霧之夜,外公哭叫著來到了這個漆黑一片、景色不明的世界上。”這仿佛預示著他此后的命運也是如霧一樣的模糊、不確定。他放著好好的家庭和幾個兒女不管不顧,經常地、短暫地離家出走,終日往返于各個航道上,跟身份不明的傳教士去遙遠的香格里拉,為了追蹤跑碼頭的小評彈團數月流連在運河上,花掉僅有的盤纏喝上幾杯啤酒,再啃上幾個雞腿,甚至去研究農婦籃子里帶血的雞蛋是否為處女蛋,他有時也在月圓之夜的梅樹下吹吹簫,疊幾塊怪石。他自顧自的生活著,簡直就不太像這個世界上的人,在外婆王寶琴的眼里,他簡直連個好好的人都完全不像。他向往自由無拘的生活,癡迷流浪與行走,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孤獨者。
再比如姨媽童莉莉,這個與外公最像的孩子也是孤獨的,她渴望融入時代的大潮,“希望挽起街上迎面走來的哪個人的手,匯入那浩浩蕩蕩的人流里面去……但是眼睛明亮、歌聲嘹亮的人們,手里舉著鮮亮亮的紅旗,他們看都沒有看他,雄赳赳氣昂昂地從他們身邊走過去了……”后來她遇上了潘菊民,以為從此可以拯救自己的孤獨,可以與之一起與這個硬的讓人心痛的世界相對抗,事實上,潘菊民自與父親、妹妹去了上海之后就再沒有出現在童莉莉面前。希望再次落空,從此尋找潘菊民就成了童莉莉生活的全部,也許她尋找的不單是潘菊民,也是自身無處安放的孤獨。童莉莉深愛著的潘菊民也是孤獨的,他很早就對童莉莉說:“真的,我發現從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孤獨的。”他的孱弱、悲觀和孤獨注定他只能做一個逃跑者,而非拯救者,他不能拯救童莉莉的孤獨,反而放大了她的孤獨。
可以說《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就是一部現代人的孤獨寓言,不管是放蕩不羈的童有源、強忍悲痛的王寶琴、賭氣折騰的童莉莉,還是隱忍節制的潘氏夫婦、逃避畏縮的潘菊民都是孤獨的,所以由他們組成的“細小南方”也是孤獨的。朱文穎用善感的心靈和曖昧的筆觸寫出了生活在時代深處或者是時代之外的每一個具有痛感的心靈,關照著他們的內心體驗和精神痛苦,塑造著曖昧又孤獨的南方世界。
(李曼,武漢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在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