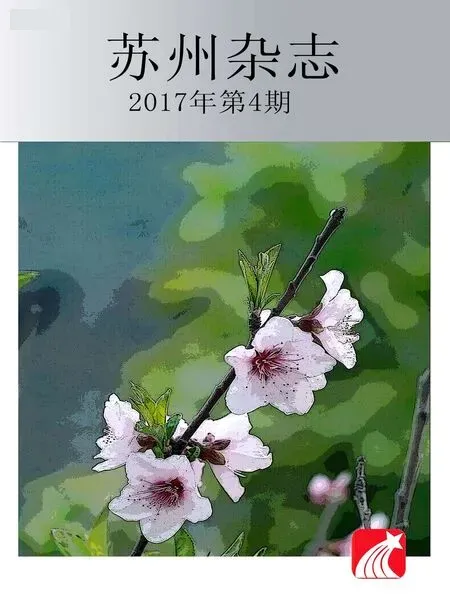回首夕陽已含山
黃惲
回首夕陽已含山
黃惲

回首已夕陽西下,只有紙上的掌故、耳邊的吟唱和那寂寞的笙簫……
王畹香的《三笑》
光裕社、普余社中,說《三笑》的名家很多,其中能獨樹一幟的,當推王畹香為第一。
王畹香之所以能獨占擅場,說起來也不意外,乃是有一個另起爐灶的腳本,與別的《三笑》腳本不同。
這,說起來還有個故事。
原來,王畹香的父親王少泉頗有點江湖習氣。所謂江湖習氣,就是尚俠好義,推己及人。從好的方面說,就是已衣衣之,己食食之,性格豪爽,與人推誠相見;從不好的方面說,有時候為了朋友情,會蔑視法律,輕于一擲。
他們是專制社會、禮法制度的潤滑劑,有這種人存在,那個社會就留給人多一點空間多一點可能,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破壞和諧,挑戰秩序。這樣的人物,金庸的小說中有很多,大抵虛構,現實生活中更多只是把朋友一倫提到前面。
王少泉就是這樣的人,他太喜歡交友了。民間傳說著一個王少泉穿破鞋的故事,這個故事很有點不合理的夸張,編得不夠包圓,但多少可以明白民間對王少泉的看法。
話說王少泉終年穿著破履,不是沒有錢買新的,而是他穿不得新的。一旦換上新的鞋子走在街鎮上,只要一看見有親戚、朋友破靴舊履在街上走,他一定會心生憐憫,馬上脫了自己的新鞋,把來和別人的交換,不換還不行,自己就趿拉著舊鞋回家去。弄到后來,據說很有人新鞋也不買了,只等王少泉出現,而王少泉成了鞋莊的大客戶。
這個故事有點夸張得不合情理,首先,每個人的腳大小不同,并不是都可以穿上王少泉的鞋子;其次,過去很多人的鞋子都是妻子兒女自己家里做,并不需要買,懶婆娘即或有,女兒也懶到某種程度畢竟不多。王少泉也不會完全照顧鞋莊的生意。不過話說回來,我小時候,同班級的同學,大冬天寒風中穿著前賣姜后賣鴨蛋的破鞋的也不在少數,但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后,農民沒有布票,無可奈何。王少泉那是清末,不至于如此之甚也。
故事雖然不盡實在,但它要表現的意思是真的,那就是王少泉這人,交游廣,朋友多,豪俠仗義不吝錢財。
王少泉的朋友中就有一個人,叫做吳振初,此人是個不第秀才,用一句套語說吧:吳先生絕對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真正滿腹詩書,博學多才。那么人家要問了:既然是這么高才,為什么竟是不第呢?
原來他的毛筆字不行,筆下春蚓秋蛇,幾乎要把中國的方塊字寫成蟹行文字似的,這樣當然難邀科舉的青目,每次考試都只有名落孫山的份了。仕途絕望的吳振初,貧窮無聊,日以聽書為樂,于是結交了王少泉。
王少泉就請吳振初另編《三笑》腳本。這樣吳振初版的《三笑》腳本就凌空出世,自然與別家不同。當時報紙上的考語是“溫柔細膩,文句之香艷,猶如一朵嬌花”。
王少泉、王畹香父子把新腳本磨了幾年,于是,王畹香的《三笑》在評彈界就“鶴立雞群不雷同”了。
有人拈出王畹香吳版《三笑》的與眾不同之處,譬如有這樣一個唱段,為其他《三笑》所未有,錄如下:
(想)為人薰沐必須勤,記否滄浪孺子吟。周公一旦三沐浴,湯盤曾有日新銘。
四月清和須浴佛,僧家借此作營生;楊妃出浴增嬌媚,見慣君王亦動心。
還有祝枝山除夕寫春聯一節,曾為澡堂題寫:進來兵部禮,出去翰林身。這副對聯也為當時人夸為妙對。
嘉興畫家吳藕汀《書場陶寫》詠王畹香云:
王畹香彈唱《三笑》
華文華武呆兄弟,牡丹亭被秋香戲。老母當丫鬟,貪歡死不關。 移風余舊格,生意殊難得。早已少人知,留聲空有機。
吳藕汀聽到的,大概是王畹香和蔣賓初合作灌制的唱片《三笑·梅亭相會》。
賈嘯峰父女與《濟公傳》
女說書在過去總是曇花一現,她們里面名角多,真正深入大眾心中的卻并不多見。試想,說早點十三歲出道,到十八歲紅極一時,二十歲前后就嫁人了,從此走下高臺,走入墻門之內,琵琶生塵,歌喉再不嘹亮。倒是五十年代后,有很多女說書真正走上了職業化的道路,藝術生命比較長了,可惜黃金時代已過去,很多賴以成名的書無法說了,歌冷舞歇,其藝術生命的質量還是低落了。
女說書長得漂亮不好,長得不漂亮也不好。怎么說?長得漂亮的話,性騷擾也多,容貌往往超越書藝而成為聽客的首選,聽客捧的是那張臉,而不是咳唾成珠的說唱,對于其藝術的進步有害;長得不漂亮呢,少人捧,營業往往不佳,畢竟很多聽客都是狎戲子心理,賞音不多,她的事業也難以長久。
當然事情總有例外,譬如色藝雙全的,很多還有家傳,這類女說書,一亮相于舞臺就不一樣,譬如說《濟公傳》的賈粲云。
《濟公傳》一名《醉菩提》,此書內容豐富,包羅萬象,諸如神怪、釋道、武俠、偵探、滑稽等等,都被說書藝人羅致一起,能合大眾的口味。不過,擅長這部書的說書人,在書壇卻并不多見,屈指說來,范玉山、龔炳南、虞文伯、沈笑梅、陳浩然、賈嘯峰父女而已。
書壇有句笑話,說《濟公傳》不登大雅之堂,說《濟公傳》的都是蘇北人。原來《濟公傳》這部書就是蘇北人編的,也是從蘇北人開始說起。在揚州,《濟公傳》又名《大羅漢》,有揚州評彈,據說在江南說《濟公傳》,要算賈嘯峰為第一人。
賈嘯峰倒不是蘇北人,比蘇北還要遠,是山東人。賈嘯峰當兵出身,清末時在揚州做下級武官,他熱血反清,存身不住,逃到上海,依蘇灘鄭少賡(大胖子莊海泉的岳父)。鄭少賡是有名的蘇灘演員,賈嘯峰在他家,自然也入了這行,學得不少的蘇州閑話(蘇白)。清末文明戲勃興,賈嘯峰就和鄭少賡一起唱起了宣揚驅滿革命的文明戲。
在揚州帶兵時,賈嘯峰喜歡聽書,在揚州小校場交了一班說揚州評話的朋友,他最感興趣的乃是《大羅漢》,因此到上海后,看看文明戲、蘇灘都不是自己的長處,決定下海說書為生。鄭少賡給他指點了噱頭,自己又琢磨了不少心得,就這樣,賈嘯峰說起了《濟公傳》。
賈嘯峰去世后,身后一貧如洗,其女賈粲云不得不繼承家學,也靠說書為生。當年不能男女拼檔,賈粲云就和嚴誦君合作,在蘇州、常州、上海說《濟公傳》為生,成為一時名家。
賈粲云也通文墨,有一陣在《東南正報》和《力行日報》撰文,談書壇掌故,表現不俗,是少有的嘴上來得筆下也來得的女性。
王燕語與《珍珠塔》
王燕語,原是光裕社中人,以說《珍珠塔》見長。他的父親叫王少泉,他有個哥哥叫王畹香,有個妻子叫王鶯聲,都是書壇中人,一家都吃開口飯。
王燕語、王鶯聲,一眼看去,就是藝名,燕語鶯聲,燕語呢喃,鶯聲嚦嚦,感覺就很不錯。王燕語在光裕社,王鶯聲呢,卻在普余社,原來,光裕社有個鐵的規矩,不許男女拼檔,認為有傷風化。想想也是,一對男女,走南闖北,到處走碼頭,雙方都是異鄉之客,日里夜里說書又頗多眉目傳情,互遞風情,夜里歇下來,就容易壞事。不過,這個規矩是為了防閑的,但未免思慮不周,因為如果是夫妻,又有什么關系呢?
然而,當年定這條規矩時,大概很少有夫妻一起走江湖的,多的是說書人帶一個女徒弟之類,往往說上幾次,就說到一張床上去了。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光裕社的規矩定得很嚴,一旦有這種情況,輕則取締,重則開除出光裕社,這也是為光裕社的聲譽計。
這樣一來,就王燕語的具體情況來說,夫妻兩人不得不分飛在外。王燕語就退出了光裕社(一說是除名),轉入普余社,這樣,夫妻雙方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一起說書了,不過,在光裕社勢力極大的蘇州,男女檔還是要干涉取締,因此普余社人一般不到蘇州來說。
自王燕語轉入普余社,他和哥哥王畹香就分屬兩個社,有人把他們比作東吳諸葛瑾,和蜀漢諸葛亮,兄弟倆各走各路,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王燕語原名根香,早年師從魏鈺卿習《珍珠塔》,不過他用的腳本卻是馬如飛的,所以人們聽下來都說王燕語一點都沒有師傅魏鈺卿的味道。
王燕語、王鶯聲可稱雌雄雙俠,自從兩人拼檔以來,第一個到的是烏鎮第一樓書場,一舉打響,后來更是所至有聲,到一地,紅一地,無錫、上海、南京等地,都是響檔,很受聽客的激賞。不過,老聽客對兩人的本事也有評價:王燕語說表好,唱功稍遜色;而他的夫人嗓音嘹亮,正像她的藝名,婉轉清脆,而說表方面就不及乃夫。兩人取長補短,雙劍合璧,難怪江湖上名聲響亮了。
再說王鶯聲,原名王石香。她于歸王燕語時,王少泉去世,王家家道中落,只得也出來說書謀生,《書壇三國志》封王鶯聲為甘夫人,王燕語則是諸葛瑾。所幸夫婦兩人拼檔,珠聯璧合,夫唱婦隨,生涯日盛。
普余社說《珍珠塔》的名家,還有李燦章、唐月仙師徒,李燦章是楊月槎的高徒,可惜很早就染了嗜好,所謂嗜好,就是吸上了鴉片,中氣不足,慢慢地,王氏夫婦就成了普余社說《珍珠塔》的翹楚了。
席云霞之孝與學
在民國評彈界中,席云霞以好學和純孝著稱,《書壇三國志》把他擬為徐庶,正是著眼于他的純孝。
席云霞原名仲賢,洞庭東山人。東山席家是個大家族,富商眾多,他卻因為貧窮而早早下海說書。他一開始在上海的報關行里跑街,他口齒伶俐,頭勢清爽,待己刻苦,有一段時間月入千金,但戰爭一爆發,上海的外貿一落千丈,他只能拜王似泉為師,以說書謀生了。
八一三淞滬抗戰時,還不到二十歲的席云霞就獨自在上海闖蕩了。那年歲,生活動蕩,人心不安,評彈從業者的生涯自然大受影響。有一次,席云霞赴某公館堂會,早已是深秋時節,重陽已過,涼風颼颼,大家都穿起了夾襖、大衣,席云霞出現在臺上時,竟是一襲白夏布長衫,大家相當驚訝。和他拼檔的事后告訴大家說,這天早上,席云霞收到東山二老的來信,知道父母生活艱難,即刻把自己身上的一襲當令長袍到當鋪當了三十元,寄往東山了。從此,席云霞的孝心為大家所熟知。除了孝心,席云霞還很俠義,推己及人,往往讓朋友分享自己獲得的資源。他有個朋友徐綠霞,從外碼頭回到上海,一時找不到書館說書,很是狼狽,找到席云霞設法,席云霞在華興電臺彈唱《雙珠鳳》,看到朋友滿身的寒酸,就馬上薦了徐綠霞,接下自己的場子。
席云霞以唱開篇聞名一時。
過去,老聽客都不注重開篇,覺得這不過是開場時等待客人到來前熱身的唱詞,無關緊要。甚至還有老聽客對開篇蹙眉疾首,他們早早來到,希望早些登堂入室,聽到昨天的“下回分解”,賣的關子已經折磨了他們一夜,無不渴望早些進入正題,而開篇仍在不痛不癢地唱著,就像急色兒脫緊裹的衣裳,雖然過程有點吊胃口,卻無不想著遂了心愿。因此,開篇于評彈家是必須的,于聽客卻是一種累贅,當然根本原因還是評彈本身不能吸引聽客,而以前評彈家也并未認真對待開篇。
開篇一旦精彩而充實,吸引聽客的耳朵和目光,開篇就不再成為評彈的附庸,有了其自身的價值。席云霞正是把開篇唱出獨特價值的人。自席云霞的開篇一出,聽客們才發現開篇亦大有滋味,值得一聽了。
席云霞是王似泉弟子,但他的開篇,卻不是來自王的傳承,而源自老名士徐哲身。席云霞拜徐哲身為自己的國學老師,授《東萊博議》一書。呂祖謙的《東萊博議》是本很好的書,說理明晰,見解獨特,雖然當年不過是“為諸生課試之作”,實在很能為國人整理思緒和擴展思路。席云霞從《東萊博議》學得的是開篇的寫作,他唱的開篇,都是自己創作,再奉呈徐哲身糾正平仄和韻腳,一上臺,自然不同凡響了。
席云霞已經被目前評彈界忘卻,能記得他的,看了我這篇小文,想必會勾起一點往昔的回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