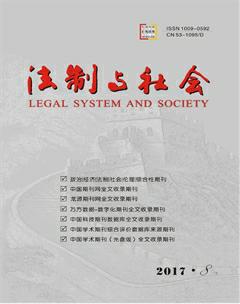法國刑事程序中的人格調查
摘 要 法國人格調查制度有著200多年的歷史,它將對被告人人格證據的甄別交給了法官,這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和制度原因。加繆于小說《局外人》虛構的默爾索殺人案引人深思,反映了法國刑事程序中的人格調查制度。人格調查是一把雙刃劍。我國若欲借用他國經驗,應立足國情,在將其本土化的過程中建立起適合我國刑事程序的證據規則。
關鍵詞 局外人 人格調查 人格證據
作者簡介:趙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2016級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圖分類號:D956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304
一、案件背景
(一)時代背景
為了免于被追問審判默爾索的具體法庭,以及這個案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地點,應當說明,默爾索案完全是假想出來的。20世紀中期,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創作了小說《局外人》。這部小說雖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對審判的敘述缺乏真實性,例如,默爾索的老板不可能不出庭作證,另外,在當時的情況下,殺死一個阿拉伯人也不可能被判死刑” 。但是,書中指明的案件發生地點阿爾及爾是當時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城市,這個虛構的故事多少可以反映出法國刑事程序的一些特征。
(二)案件事實
小說中記敘的默爾索案,在認定案件事實上可能不會有任何疑問。因為書中的文字已經清晰地表達了在阿爾及爾附近的海灘上殺人事件的經過:“我(默爾索)往前走了一步……阿拉伯人并未直起身子,卻把刀子拿出,在陽光下用刀對準我……我全身緊張,緊握槍托。扳機扣動,我觸及光滑的槍托,這時響起生硬而又刺耳的聲音,一切都在這槍聲中開始……接著,我又對著那不動的身體開了死槍,打進去的子彈并未出來……。”
(三)案件審判
案情如此明確,以至于擺在法官面前的問題,不再只是默爾索的謀殺罪名是否成立,而是他的何種人格致其殺人。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所有的法律從業人員達成了出奇的共識。律師告訴默爾索,預審法官獲悉他在母親的葬禮上無動于衷,“如果找不到任何解釋,這將是指控的重要證據” 。在重罪法庭上,證據顯示默爾索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所以檢察官指控他“在埋葬母親時懷有一顆殺人犯的心” 。盡管律師反駁“他受到控告究竟是因為埋葬了母親還是殺了人” ,但是辯護依然圍繞默爾索的人格展開:“(他)為人正直……工作任勞任怨……希望老母能過上舒適的生活才把她送進養老院……” 似乎默爾索和母親的關系與他槍殺阿拉伯人似乎有著深刻的聯系,而法庭判處絞刑也是合法合理的。
二、法國證據法上的人格證據
(一)對本案起決定性影響的檢方證據
如果承認默爾索的人格與殺人行為存在因果關系,那么檢方只需證明默爾索人格不端,就可以令法庭判處其殺人罪。為此,檢方提供了三位證人作證。養老院院長證明默爾索的母親曾責備默爾索把她送進養老院,養老院門房證明默爾索不想跟母親遺體告別,母親的老友證明默爾索的確沒有在葬禮上哭。而辯護方證人為默爾索作證時,盡管并未達到辯護的效果,但也圍繞這樣的邏輯展開。馬松作證默爾索為人正直,但未被采信。瑪麗的證詞,反而成為了對控方有利的證據。而雷蒙的證詞證明力則因其職業被削弱。
可以說,在法庭上,檢方充分證明了默爾索與母親關系不佳,即默爾索的人格存在問題,據此,法庭對默爾索定罪。可見,在法庭看來,人格證據對定罪量刑極為重要。
(二)人格證據的內涵
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中,“人格”一詞常常出現。“人格”指的是人身上所擁有的獨特而穩定的心理品質的集合,而圍繞其展開的人格調查不僅涉及被告人人格特征、處事風格、行為傾向,還涵蓋其個人經歷、家庭生活、教育情況等客觀方面的因素 。
(三)人格證據的收集與展示
人格調查基本貫穿了法國刑事程序的大部分過程。例如,依照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在審前程序中,“預審法官依法進行其認為有益于查明事實真相的一切偵查行動……親自……或者委派任何有資格的人按照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資政意見以后頒布的法令確定的文件,對受審人的人格、家庭狀況、物質與社會狀況進行調查” (第81條)。在審判程序中,“證人僅對被告人受到指控的事實或被告人的人格與精神道德提供證言” (第331條)。“如被告人不同意當庭接受審判,或者案件的準備尚未達到審判狀態……輕罪被告人或他的律師,可以向法院提出請求,要求法庭命令進行其認為對查明被告人受到指控的事實真相及其人格所必要的任何偵查行動” (第397-1條)等等。
三、法國與中國對待人格證據的態度
(一)差異
證據左右著案件審判的走向。在默爾索案中,檢方的證據起到了決定性影響。實際上,檢方即使不拿出默爾索的人格證據,僅依靠已定性的殺人行為,也能夠獲勝。但是,他們正是在反復圍繞該證據的論證中,不斷淡化對殺人行為的關注,強化對默爾索個人的審判,最終取得了勝利。
默爾索案雖然是虛構的案件,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可以反映出法國刑事程序中人格調查的特征。如果將法國與中國對待人格證據的態度作比較,我們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了八種證據,人格證據并不在其中。在司法實踐中,通常也不將與人格有關的證據作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根據。盡管如此,并不是說我國刑事程序從未關注人格證據。雖然法律并未作明文規定,但是與犯罪行為有密切關系的一貫表現,卻是酌定量刑時應當予以考慮的因素。“如果行為人一貫遵紀守法……應予從寬處罰;如果行為人一貫表現不好……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較大,一般予以較重的刑罰。” 但在總體上,我國證據制度對人格證據是持消極態度的。
實際上,在價值目標的追求上,法國和中國的刑事程序都要求盡可能發現事實真相。差異集中體現在對人格證據的證明價值的理解上,最終導致對人格證據的不同態度。這種差異所反映的,不僅是立法政策的差異,也是學說理念的差異,更是歷史文化的差異。
(二)成因
1.刑事歸責根據原因
人格證據能否作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據,與刑事責任根據有關。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一般從“有責性”討論刑事責任的根據問題,主要有三種學說。
行為責任論認為,個別的犯罪行為是刑事責任的根據。但是,只有行為人基于自由意志做出實施行為的決定,其行為和后果可歸責。行為責任論為追究刑事責任確立了客觀標準,但將人的自由意志絕對化,忽視了作為責任主體的行為人的意義 。
與行為責任論對應,性格責任論認為,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它看到犯罪行為與行為人的聯系,但片面強調危險性格,否定了犯罪行為的獨立意義 。
為了克服前者缺陷,大陸法系學者提出了人格責任論:行為人受自身和環境的制約,仍有行動的自由 。也就是說,先將行為作為責任判斷的直接對象,再將犯罪行為與人格相聯系,做出評價。但是,它接納了人格證據,卻依然無法解答人格與犯罪行為的關系問題。這種困惑,不僅出現在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更是反映在以相關內容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
我國并非大陸法系國家,但也要面對刑事責任根據的問題。通說認為,刑事責任的根據是符合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由此全面貫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也是我國刑事程序基本不接受人格證據的重要原因。
2.刑事證據制度原因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確立了自由心證制度,正如《刑事訴訟法典》第353條規定:“……法律不責問法官形成自我確信所依據的理由;法律也不規定一種規則并讓法官必須依賴這種規則去認定某項證據是否完備、是否充分。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靜氣、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決定,本著誠實之良心,按照理智,尋找針對被告人所提出的證據以及被告人的辯護理由所產生的印象……” 。對此可以理解為,對證據是否有證明力以及證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預先作出規定,而由法官據內心確信自由判斷,認定案件事實 。這種制度賦予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于人格證據應當如何評價,也在個案中由法官具體分析。
我國的刑事證據制度尚沒有統一的名稱,但是理念基本相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實事求是”或“客觀真實”。這種證據制度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相對應,要求對被告人的有罪判決必須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也促使司法人員在對待證據時采取審慎的態度。
3.歷史文化原因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家開始致力于重建社會構架,將國家作為建立既定秩序的正統性的核心,反復強化“國家”與“共和國”的理念,構建抽象的高度標準化的“法國公民”形象 。而法官正是據此對個人進行審判的。這就解釋了為何法官要對被告人的生活、人格進行調查,也解釋了為何《局外人》中法官判處默爾索被絞刑要“以法國人民的名義” 。
在我國,傳統法治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強的道德意味,被告人人格也的確是司法人員所看重的因素。盡管立法上沒有對人格證據的性質和地位予以明確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總能找到與人格相關的內容。
四、結語:法國人格調查對我國的啟示
法國人格調查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在這過程中,不斷有人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提醒著法官是否能有效甄別人格證據。正如我們無法忽視人格證據的弊端,同樣也不能否認它的優勢,其中有著深刻的社會與制度原因。因此,我國對待人格證據時,應立足國情。想要吸收外國經驗未嘗不可,但是必須秉著謹慎的態度,在將其本土化的過程中建立起適合我國刑事程序的證據規則。
注釋:
阿爾貝·加繆著. 徐和瑾譯.局外人(譯者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7.
阿爾貝·加繆著. 徐和瑾譯.局外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70-77,80-81,122,132,136.
宋洨沙.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品格證據之比較研究.政治與法律.2012(5).
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85-86,242,275,87.
曲新久.刑法學(第四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234,192,193,248.
汪海燕、胡常龍.自由心證新理念探析——走出對自由心證傳統認識的誤區.法學研究.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