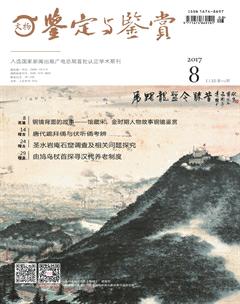江蘇書畫 書畫江蘇
侯仲春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2017年1月,江蘇省美術館時值建館80周年之際,為領略江蘇書畫藝術之洋洋大觀,了解江蘇書畫歷史之綱概,特別策劃推出“江蘇歷代書畫大家經典作品特別展”。本展覽由“圖表資料”和“經典作品”兩個部分組成。展覽分“砥礪與前行”“輝煌與蛻變”“多彩與滄桑”和“復興與繁盛”四個板塊,以作品創作年代為軸,對江蘇歷代書畫大家和流派進行學術梳理,以史料圖表、經典書畫作品的展覽展示,呈現六朝以來延續一千六百多年江蘇美術發展脈絡。展品以館藏中國書畫真跡為主,為展示和復原發展脈絡概貌,部分展品由影印件、二玄社書畫復制品代替補足,同賞共鑒。通過此次展覽,回顧江蘇書畫曾經創造的輝煌,凸顯江蘇美術強省、美術巨省的特殊地位,并以此為新的起點,推動江蘇書畫藝術不斷健康發展,加快文化江蘇的建設步伐。
江蘇自古以來經濟繁榮,美術發達,人文薈萃,千百年來涌現了無數的書畫名家和書畫流派。他們以其非凡的藝術才華,共同譜寫出絢爛多姿的江蘇書畫藝術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江蘇書畫藝術史幾乎構成了中國書畫藝術史的主流和主干,在全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離開了江蘇,中國書畫藝術史幾乎黯然失色。
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變化,江蘇書畫藝術從三國兩晉南北朝開始,此起彼伏,幾經消長,逐漸步入循序前進的發展階段。
東晉南朝時期是江蘇文藝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隨著北方貴族的南遷和南方政治中心的誕生,江蘇經濟出現了第一次繁榮,引發了文化藝術的逐漸高漲。當時,風云激蕩的社會、紛繁復雜的環境,為風流倜儻的魏晉風度的滋生、成長提供了溫床。禁錮與開明并存的社會文化大背景,為絢麗燦爛的藝術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名士粉墨登場,他們歌著、舞著、癲狂著,以其獨具魅力的表演充分展現著自己的才華,于各個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江蘇美術也由此展現出非同凡響的成果,無論是繪畫、書法,還是雕塑,風度與精神并存,并誕生了諸多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赫赫地位的美術家、書法家,曹不興、戴逵、顧愷之、陸探微、宗炳、蕭繹、張僧繇、王羲之、王獻之等,不一而舉。這一長串名單真如過江之鯽,首尾相銜,可見其盛況空前。特別是顧愷之、王羲之,更是成為后世書畫家頂禮膜拜的宗師,至今影響不絕。
隋唐時期,全國實現大一統,由于政治中心的北遷,江蘇文化藝術基本處于一個潛伏期、過渡期。然而,魏晉風度像潛流一樣依舊在滋潤的江南大地上潺潺不息,造就了江蘇藝術溫文爾雅的文人風采,并為其再一次勃發積累了堅實的基礎。
五代十六國時期,南北割據,中原戰亂不息,而江南一地卻相對和平。江蘇地區政治、文化又回復到南北朝時期的精彩局面,江蘇書畫藝術因此迎來了第二次輝煌。南唐皇帝雅好文藝,特別是后主李煜潛心詩文書畫,在相當程度上助長了書畫風氣的形成。也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江南本是文藝家的搖籃,而不是政治家的舞臺,各種因素交織一起共同為江蘇藝術的復興提供了孕育的溫床。南唐宮廷設立畫院,美術蔚然成風,為后世提供可資參考的樣板,王齊翰、周文矩、顧閎中等人承前代余緒,開創人物畫之新格局,光彩奪目。在民間,徐熙、徐崇嗣祖孫創立的“野逸派”文人水墨花鳥風格,具有石破天驚的風格史之意義,成為千余年寫意花鳥畫之源。董源、巨然開創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畫風格,成為文人畫發展的正脈之源,歷千載而風采依舊。總的來看,五代時期,江蘇對中國美術的貢獻是全方位的,從人物畫到花鳥畫再到山水畫,構成了一個緊密而有序的關鍵鏈,影響長遠而深刻。
江蘇書畫藝術真正達到全國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是從元代開始的。元代中期以來,緣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江南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并一躍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元蒙朝廷相對寬松的文化政策,使得江南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傳統,以吳中為中心為蘇南地區日益成為文人活動的中心,江蘇書畫藝術隨之步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常熟黃公望、無錫倪瓚成為彪炳千秋的一代大師,久盛不絕,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明清千余年的繪畫史離開了黃、倪二人,真不知這歷史該怎么寫?實際上,元代的江蘇書畫藝術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她與浙江地區的書畫藝術共同組成一個統一的體系。特別是元末,華亭曹知白、昆山顧瑛嗜好詩文書畫,喜交文人雅士,在其周圍形成了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文化藝術網絡,浙江柯九思、楊維楨、張雨、唐棣、趙雍、王蒙等人往來其間,共同描寫出元末江蘇文人書畫的精彩篇章。
明清兩代,江蘇經濟中心的顯赫地位逐漸凸現,正如吳人王世貞感嘆:“蘇州拱稠,文物萃東南之佳麗,詩書衍鄒魯之源流,實江南之大邵,信天下之無仇……至于治雄三殿,城連萬雉,列巷通衢,華區錦肆,城高綦列,橋梁櫛化,梵宮蓮字,高門甲第,遠土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萬金一箸。所謂海內繁榮,江南佳麗者。”經濟的發展、商業的活躍,帶動城市的全面繁榮,文化藝術自然發達。江蘇地區文風蔚然,人文之盛居全國之冠。江蘇終于演化成全國的文化圣地,掀起了中國書畫史上一個又一個創作高潮。
首先,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畫派”、以祝允明、陳淳為代表的“吳門書派”崛起,蘇州成為書畫家的樂園。眾多文人士子歷經宦海沉浮,閑居城鎮,將雅集宴饗、賦詩作畫的文人情趣帶入市井生活,帶動新興的富商追隨文人雅好,成為一時風尚。接著,以董其昌、陳繼儒為代表的“松江畫派”“云間書派”興起,江蘇書畫盛況空前。特別是董其昌執藝壇之牛耳,倡導書畫之學,引領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潮流。在董其昌的啟迪下,以王時敏、王原祁為代表的“婁東畫派”和以王翚為代表的“虞山畫派”同時誕生,將南宗文人繪畫風氣從江南一隅迅速擴展至全國,并影響著北京的宮廷書畫活動,歷時達三百年之久。與此同時,“清四僧”“金陵八家”等集聚金陵城,南京成為當時與北京相抗衡的繪畫重鎮。其中,石濤往返于南京、揚州之間,其書畫實踐為揚州繪畫的崛起注入了活力。而后,“揚州八怪”“海上畫派”繼起,打破傳統文人畫的雅俗之別,使繪畫藝術走向市場,成為中國藝術經濟的先驅者。在他們的影響下,傳統中國書畫不斷向個性化、商品化、大眾化推進,由此開啟了近代美術之先聲。可以說,正是這些江蘇書畫名家的藝術實踐,構筑了明清書畫史的發展序列。
進入20世紀,江蘇美術發生重要變化。尤其是中華民國定都南京,各地的藝術精英又一次移居南京,江蘇成為現代美術的發源地。呂鳳子、劉海粟、徐悲鴻、陳之佛、傅抱石、張大千等人都在江蘇留下了藝術活動足跡,從事美術教育,為江蘇美術的發展書上了精彩的一筆。特別是徐悲鴻在中央大學藝術系的教學理念和體系,成為1949年以后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重要模式,影響至今;傅抱石在建國后開創的新金陵畫派成為20世紀中期山水畫的主流樣式,輻射全國。如今,江蘇書畫藝術仍在全國美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由此可見,江蘇書畫藝術史幾乎構成了一部濃縮的中國書畫藝術史,其地位的確舉足輕重,也是其他地區所無法替代的。
雖然,江蘇書畫前賢在歷史上曾留下不計其數的書畫精品,但由于歷時久遠,元代之前的書畫作品流傳甚少,江蘇文博機構收藏幾屬寥寥。除南京大學所藏五代王齊翰《勘書圖》為人所知外,江蘇早期書畫作品都收藏于海內外的公私收藏機構。考慮到實際情況,“江蘇歷代書畫名家精品特別展”充分利用江蘇館藏書畫之優勢,從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常熟市博物館等多家單位數以萬計的書畫藏品中著重挑選了從元代至現代的名家作品八十余件,以“文人畫實踐上的雙峰并峙”“繪畫千年實踐的理論升華”“傳統風格的反撥”“中西合璧的一代宗師”等四個單元,立體地呈現出江蘇書畫的悠久歷史和輝煌成就,勾勒出江蘇書畫的發展、演變軌跡,并概括出江蘇書畫的藝術特色和發展走向。
展覽匯聚江蘇歷代書畫名家精品,既有名家大師的力作、代表作,又有大量作為流派性反映的各地方名家的作品。舉凡“元四家”“吳門畫(書)派”“松江畫(書)派”“清六家”“清四僧”“金陵八家”“揚州八怪”“海上畫派”“新金陵畫派”乃至“京江畫派”等大大小小的書畫流派的典型作品,不一而舉,基本上涵括了元代以來江蘇書畫的各家各派、各種風貌,具有較強的系統性、資料性。其中部分作品屬首次公開展出,它對于廣大書畫家、美術史家、書畫鑒定家和文博、藝術工作者來說,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人們可以依托此次展覽了解江蘇書畫的發展脈絡,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對畫家的藝術特色、創新之處、風格異同進行詳盡地比較分析,掌握相關的知識。因此,舉辦具有濃郁的地域性特色的大型書畫展示活動,不啻是一次研究江蘇地方文化的絕好機會。它對于促進繼承、傳播地方優秀文化遺產,對于借鑒歷代書畫創作經驗、促進當代書畫藝術創作,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江蘇歷代書畫大家經典作品特別展”不愧為一次好展覽!我們有理由相信,江蘇書畫藝術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更加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