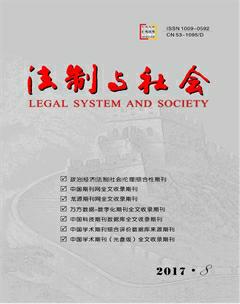清官文化的本質是法制文化
邸紅旗 孫永興
摘 要 在元雜劇中以包拯為代表的清官文化,其實質為法制文化。包拯等清官身上蘊含著百姓的法制理想,包公的道德斷案,實際上是規則之治,那種認為包公等清官斷案是“人治”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關鍵詞 “箭垛手法” 包拯 法制理想
基金項目:2014年度天津市藝術科學規劃項目(編號:A14013,主持人:孫永興)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邸紅旗,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天津行政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法社會學;孫永興,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天津行政學院教師。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136
在元雜劇中以包拯為代表的清官文化,其實質為法制文化,而非人治文化。法制文化強調的是政府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處理事務、審理案件中,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根本標準。法制文化不等于法治文化,兩者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判斷是非區直的“法律”是否為良法。法制文化也強調法律適用的普遍性,也強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盡管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缺陷。胡適在《<三俠五義>序》中指出:“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這種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們取了個名字,叫‘箭垛式的人物……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民間的傳說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其實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包拯本身就是一個尊崇法制、公正清廉的楷模。
一、包拯等清官身上蘊含著百姓的法制理想
元代清官文化的興盛與多樣化元雜劇的產生密切相關,包公藝術形象的基本成型也是也是在元雜劇中通過劇作家們的創作而完成的。在元代那個黑暗的社會制度中,對普通百姓來說毫無法律上的公平正義可言;屬人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導致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百姓觀賞元雜劇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為了追求元雜劇故事的愉悅,為其平淡的生活增加一絲快樂,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存在的法律公平和正義。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僅僅觀賞是不夠的,他們還情不自禁的加入到元雜劇的創作中來。元雜劇中很多劇目的作者都沒有名字出現就是這個原因。民眾參與創作是元代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公案劇產生的重要原因。有很多學者看到了這樣現實,在那種對法制理想的追求下 “一般的平民們便不自禁的會產生出幾種異樣的心理出來 ,編造出幾個型式的公案故事”。 在元朝野蠻統治下底層百姓自然想念那個和他們的時代相距并不遙遠的包拯。元雜劇是通過一個個司法案例將各種優秀的品質映射到包拯身上,是普通百姓對法律理想最樸素的體現。由于元雜劇及其他文學作品對包拯形象的不斷刻畫、不斷豐富,“老百姓所了解的包拯與歷史記載的包拯也不完全一致,老百姓心中的包拯形象主要來源于戲曲和小說,他們所知道的包拯就是他們心中清官的化身” 。但是,普通百姓相信那個能“日間斷人,夜間斷鬼”的人就是包公;我們相信那個隨身有八大護衛、帶有三口鍘刀,可以隨時處死皇親國戚的人就是包公,實際上的包公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對此,“我們不能因為清官文化主要來源于文學作品而否定其法文化的性質。這些文學作品就其內容而言,基本上是虛構的,而這種虛構本身并非毫無根據。通過對所有的包公案作品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故事雖形形色色,但其精髓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包拯的法律精神——這個宗旨就是包拯的法律精神,如果離開了這個宗,雖然其名字也叫包拯,但他無論如何不是人民心中的清官包拯”。 應該說,這種分析是非常有見地的。在元雜劇中被人民愛戴的包公不僅是因為他“清如水,明如鏡”,而是因為他不別親疏,不論貴賤,一斷于法。
二、包公的道德斷案,實際上是規則之治
眾多論者認為元雜劇中國的清官,其實是人治的典型,包括包公在內,他們判案的標準并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儒家思想和學說。并且他們指出,包拯不僅不依法斷案,而且也枉法裁判,典型的案例如《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在元雜劇中,兄弟三人打死豪強勢要葛彪,按照元朝的法律規定(盡管葛彪事先打死了他們的父親)起碼要有一個人要除以死刑,但包拯就因為三人爭相赴死的氣節,更由于其中母親寧愿讓自己的親生兒子去抵罪的行為,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包公對于這一重案的判決是:
偷馬的趙頑驢,替你償葛彪之命。你一家兒都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你本是龍袖嬌民,堪可為報國賢臣。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令,母親封賢德夫人。國家重義夫節婦,更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沾恩。(正旦同三兒拜謝科,云)萬歲,萬歲,萬萬歲!(唱)
論者指出,包公也“葫蘆提”。本來該判死刑的兄弟三人不僅沒受任何處罰,反而加官進爵,連母親也被封為賢德夫人;更可惡的是僅僅偷了一匹馬,趙頑驢就被包公判處死刑,并且是遭受酷刑,盆吊而死,被用來替他們三兄弟抵罪。這不是枉法裁判是什么呢,就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包公的行為完全夠的上枉法裁判罪。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使用儒家教義判案?如何看待包公的行為?這種情況在元雜劇中絕不是特例。
有元一代法制混亂,在法律適用方面更是如此。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的統治,法律適用上采取屬人法原則。屬人原則和屬地原則,是法律適用的兩個基本原則,本身沒有優劣之分。我國目前的法律適用上也存在屬人法原則適用的情況,比如對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適用不同于漢族的政策與法律。但元朝的屬人法原則人為的將一個國家的居民分化為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四個等級,每個階層的人享有完全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加劇了民族壓迫和階層壓榨。蒙古人適用蒙古習慣,色目人適用伊斯蘭教法本無可厚非,但同罪不同罰完全背離了法律公平原則。對于漢人、南人適用的民族壓迫的政策和法律,同命不同價,引起南人和漢人的切齒痛恨。法律適用標準的不統一,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法不可知,威不可測”,他們渴望實現法律規則適用上的統一。
表面上看,元代統治者制定了一些成文法,制定了判例援引的基本規則,但這都是形式上的。在金和南宋統治下,普通民眾對于“德治”、“仁政”、“明德慎罰”、“禮法合一”法制觀念已經全面接受,上述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但元代統治者對上述事實置若罔聞,完全漠視;實際推行的屬人法制建設極端混亂,實際上元朝社會可以說處于法律的真空。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元朝這種多元化的法律根本無法理解,更不可能取得心里上的認同。盡管元初的統治者對儒家思想采取了排斥態度,但自漢朝以來近千年的儒家文化浸潤已經深入普通民眾之心。更兼元初的知識分子其知識譜系完全是來自于儒家思想,他們更是渴望在現實生活中恢復儒家思想的規則之治。在傳統儒家思想的當中,引經入律本就是法制的組成部分。在《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中,包公的判決其實就是引經斷獄,實際上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將元朝多重法律規則,統一為一種規則,也就是儒家經典。
我們看到,元朝建后,統治者很快認識到多元化的法律規則不利于統治。他們也采取措施,促使法律走向統一。他們采取的使法律走向統一的途徑有:一是至元八年(1271年)前,主要有法司在擬判中大量引用其他王朝舊例做依據,這里的舊例其實是《唐律》、《宋刑統》和金朝《泰和律》,這些都是傳統中國的社會價值的法律表現。二是通過引入儒家理論作為“衡平”原則指導下的新判例,進而讓法律向傳統中國的法律靠近。 元朝統治者后續采取的這些措施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儒家思想的傳播。這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包公在《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中包公判決的合法性。
對于清官文化就是法制文化這個觀點,北京大學教授段寶林早在1999年5月6日就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關于包公的人類學思考》進行了論述,只是先生的觀點沒有得到應該有的重視。我們社會中大多數學者仍然認為清官文化就是人治文化,與法治的路徑是背道而馳的。現將段先生的論證重申如下:
“只要有社會存在,就要有法律;只要有社會不平存在,就會有特權霸道和貪贓枉法的事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在人民心目中,包公就會站在公正的社會法律一邊,站在受欺壓的民眾一邊,排除權貴和金錢的干擾,執法如山,鐵面無私。如此這般,包公的形象當然會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禮拜。所以,從本質上看,對包公的崇拜,實際上是對社會公正的崇拜,是對人民正義的崇拜,是對清明政治的崇拜,是對廉潔奉公的崇拜,是對不畏權貴、不通關節、執法如山的崇拜,一句話,是對法治的崇拜。”
注釋:
趙忠富.元代公案雜劇中的包拯為何受民愛戴.https://wenku.baidu.com/view/d981a903dc36a32d7375a417866fb84ae45cc331.html.
從公案文學的嬗變看元代公案劇的特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60(6).
馬康盛、宋元強主編.包拯研究與傳統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230.
李睿、潘志勇.包公也斷“葫蘆案”.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
胡興東.元代刑事審判制度之研究.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5(2).
段寶林.關于包公的人類學思考.光明日報.199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