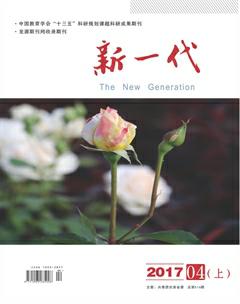重詩守禮
何榮
摘 要:我國家訓萌芽于五帝時期,產生于西周,兩漢時出現了成型的家訓著作,至于隋唐日益成熟,宋元之際得以長足發展,至明清而鼎盛。縱觀我國家訓篇什,或勵志、或勉學、或修身、或處世、或崇孝、或為政、或婚嫁、或治家,頗為宏富。其中對于“詩”和“禮”的提及成為家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溯其源流皆因《論語·庭訓》孔子談及了“詩”與“禮”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家訓;孔子;詩;禮;觀念
春秋末期,社會變動劇烈,奴隸制社會即將土崩瓦解,新興的社會力量正在醞釀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大大變革。值此之際,逾越周禮規范的事情在不斷發生和上演,這是封建制取代奴隸制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如《論語·八佾》篇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為何會如此,言其如若能忍受此事,那就沒有他孔子忍受不了的事情了?原來,季氏邀請孔子去他那觀樂,孔子看到有八佾舞于季氏的庭院。在古代,舞蹈奏樂,八人為一行,一行便是一佾,八佾即八行。對于每佾人數的解釋歷來有兩種,一是每佾有八人,二是每佾人數與其行數相同。但無論哪種解釋,八佾——六十四人的規格,在孔子極力維護的周禮中是有明確規定的,那種規格只能是周天子舞蹈奏樂的人數。周禮中還規定,諸侯觀樂采用六佾,大夫四佾,士只能是二佾。季氏是當時魯國很有實力的貴族之一,與同樣很有實力的孟氏、叔孫氏一起實際把持著魯國的國政。但這里的季氏只是大夫,因而他在舞蹈奏樂的時候只能使用四佾的規格,可季氏卻偏偏用了八佾,這一行為就是典型地對周禮的破壞,也就是不按禮制和規矩行事了。因而,孔子才會對此表現出極大地不滿和憤慨。又《論語·八佾》云:“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孔子侍奉君主,一切都會按照周禮中要求臣子侍奉君主的禮儀禮節去做,但是在別人眼里看來孔子卻是很諂媚的。當時社會面貌由此可見一斑了,正所謂禮崩樂壞。禮樂征伐,此時不再是堯、舜、禹、湯以及西周有道之時的自天子而出,而是自齊桓公稱霸諸侯之后的自諸侯出,更有甚者是自大夫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孔子對于子弟的教育便側重于對《詩》與《禮》的教導。
《論語·季氏》中有《庭訓》一章: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孔子的學生陳亢想知道伯魚在老師孔子那里是否得到過獨到的知識傳授,孔鯉回答“未也。”孔鯉告訴陳亢,父親只是曾專門向他談及了學習《詩》與《禮》的重要性。孔子問孔鯉是否學習了《詩》,孔鯉答曰:“未也。”孔子教誨兒子“不學詩,無以言”。這其實是春秋戰國時期所特有的時代風貌,即賦詩言志的傳統。在《左傳》中對此有著豐富的記載,如將《詩》中的句子合理地運用于外交活動中,就可以避免戰爭、爭取外援、孤立敵人。更為重要的是《詩》側重于對德行的教育,可以修身治國。《論語·陽貨》篇中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可以培養人的想像力、可以提高人的觀察力、可以鍛煉人的群合性、可以使人學到諷刺的方法,更有甚者可以使人學到如何服侍父母、侍奉君主的方法,《詩》因而具有著認知、審美、教育等多重社會功用,教導人們按道德準則行事,不越倫理綱常。孔子對于《詩》曾評價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論語·為政》)情感純正在孔子看來是《詩》最偉大的地方,因此,讀《詩》就成了孔子教育學生極為重要的教學內容。
《論語·陽貨》篇中還記載了孔子要求孔鯉要讀《周南》和《召南》的故事:“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孔子善于比喻,他說,不學習《周南》《召南》就像是面對著墻壁站立著,眼前什么也看不到,會使自己陷入無路可走的困境之中。在孔子看來,《詩》承載了他所倡導的“仁”與“禮”,對《詩》的學習,便是自我修養的提升。《毛詩·序》繼而將其擴充為“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可以明夫婦之道,講人倫綱常,教化人心向善。既有如此功用,君子怎可不學《詩》?
又《論語·學而》篇第十五章中記載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問老師,雖貧窮但是不諂媚,雖富有但是無驕橫之態,是不是可以,孔子雖肯定如此不錯,但是卻不如貧窮卻依然快樂,富有而有懂禮來的更好,子貢聽后若有所思,便援引《詩經》中的句子來總結老師說的話,他說,這就像要對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樣,要先開料、再糙銼、細刻、然后磨光。孔子聽聞后非常高興,并給予了子貢非常高的評價,他說從此可以和子貢好好談《詩經》了。由此可見,子貢對于《詩經》是經過熟讀的,同時他還學會了舉一反三、融會貫通,能夠深明《詩經》的旨意,并將其運用于生活和學習當中。同樣,在《論語·八佾》篇中亦有子夏問孔子有關《詩經》詩句的記載,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說:“繪事后素。”子夏聽后若有所悟地說:“禮后乎?”孔子則高興地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在《論語》中還可以看到,孔子說《詩》的作用時,常常和禮樂共舉。孔子所謂樂的內容,在《論語》中可以看到,是離不開禮的。無論是《詩》亦或是《禮》,它們的存在都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統治秩序:“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通過對于《詩》的學習,加之禮樂的輔助,人的自我修養才能得以提升,才能成為“人”。《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也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的記錄。又《論語·泰伯》有云:“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人如若只是注重容貌態度的恭敬而忽略了禮,未免就會使人有勞倦之感;只重視謹慎小心而忽略了禮,則不免流于畏葸懦弱;只是追求行事敢作敢為的勇敢膽量而忽略了禮,就不免因盲動而罹受禍患;只追求心直口快的爽直而忽略了禮,就不免使人頓生尖刻之感。因此,孔子在教育兒子孔鯉應當多讀《詩》之后,亦問詢孔鯉是否在讀《禮》,而孔鯉的回答仍是“未也”,孔子便教誨兒子“不學禮,無以立”。
孔子在魯國曾以知禮聞名,孟僖子曾命二子“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對于孔子而言,治國的根本在于人倫綱常,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而人倫綱常如何得以保障,便是“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了,禮的作用就是行事恰當可貴。孔子告誡孔鯉“不學禮,無以立”是因為他認為禮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劉向《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品行高尚的人是不可以不學習的,且一切都應有規矩,接待賓客是一定要穿戴整齊的,不修飾則沒有好的儀表,沒有好的儀表呢,就會失去理性,沒有了理性,為人一定會不忠誠,而人一旦不忠誠,就一定沒有辦法安身立命了。所以,在孔子看來,好禮則必然溫恭謙讓,不逾規矩。
孔子在他的家教觀中非常重視詩與禮樂的緊密結合,在對學生的教育中也有很多對于詩與禮的提及。孔子認為只有讀詩懂禮才可以正人之本,使人很好地立身處事,他的這種教育觀念這對后世的家教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
[3]西漢劉向著.向宗魯校正.說苑校正[M].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