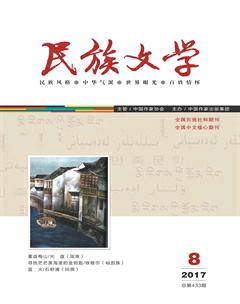歷史記憶與發(fā)展的幻象
劉大先
光盤《重回梅山》是一個鑲嵌型文本:恒通公司的董事長“我”為了完成抗日英雄爺爺?shù)倪z愿,重返他曾經(jīng)戰(zhàn)斗與生活過的梅山。“我”在重返梅山的途中,閱讀爺爺?shù)幕貞涗洠由盍藢γ飞綒v史的了解,同時也加劇了對梅山現(xiàn)實(shí)的憂慮。這個爺爺魂?duì)繅衾@之地是“我”心靈的傷口,因?yàn)樵跔敔斢洃浿胁菽咎鹑牡胤饺缃褚呀?jīng)是一座荒涼廢棄的野山。十年前,恒通公司在梅山開發(fā),石材加工污染了水源和土壤,雖然村里人因此發(fā)了財(cái),但他們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蔬菜糧食,患上怪病,一個接一個地相繼死去。存活的村人遠(yuǎn)避到縣城,眺望故鄉(xiāng)的泥土。爺爺?shù)幕貞涗浥c“我”的現(xiàn)實(shí)行程之間彼此照應(yīng),突出了今昔對比,而梅山歷經(jīng)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大躍進(jìn)”、新世紀(jì)以來的經(jīng)濟(jì)開發(fā)的七十余年來的歷史漸次鋪展開來。
“我”親歷的梅山是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而歷史是由爺爺?shù)幕貞涗洺尸F(xiàn)出來的。1945年春天由土匪整編成的抗日武裝與日軍慘烈的梅山伏擊戰(zhàn),1948年春天國共兩軍的拉鋸戰(zhàn),1958年的全國大煉鋼鐵,都讓梅山飽受重創(chuàng)。但是燒焦的土地隔段時間總是又長出了草木。1978年,爺爺退休回到梅山時,又是一片青山綠水好風(fēng)光。1988年冬天爺爺再次回到梅山,山嶺草木深深,曾經(jīng)一度絕種的野獸出現(xiàn)在梅山。直到恒通公司來開發(fā)之前,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盡管一次一次飽受各種蹂躪,但都憑借自身頑強(qiáng)的生命力自我恢復(fù)了。
但是,2004年開始恒通公司在梅山開發(fā)不到半年,就讓這片土地傷筋動骨,乃至喪失了自我修復(fù)的機(jī)能。梅山的環(huán)境破壞,造成人口死了一大半,但是在巨大經(jīng)濟(jì)利益的驅(qū)使下,“梅山人沒有告發(fā)我,當(dāng)?shù)卣矝]把這個死人事件當(dāng)回事。”最終還是“我”出于內(nèi)心的愧疚與自責(zé),撤銷項(xiàng)目,空手而歸。十年之后的現(xiàn)在,當(dāng)“我”重返梅山,看到滿山綠色,以為生態(tài)已經(jīng)恢復(fù),現(xiàn)場一勘查才知道原來“鋪在裸露山嶺上的不全是塑料草綠色網(wǎng),還有涂了綠色油漆的帆布”,梅山再也無法重回生機(jī)盎然的局面,經(jīng)濟(jì)開發(fā)的惡果超過自然的承受能力,甚至遠(yuǎn)比爺爺?shù)膽?zhàn)爭破壞力更大影響更久遠(yuǎn)。這里提出的問題可謂觸目驚心。
邦克(Stephen G. Bunker)曾經(jīng)用依附理論分析受支配的開采業(yè)邊陲地區(qū),相較于核心地區(qū)而言,這種貿(mào)易對低度發(fā)展的地區(qū)是不公平的貿(mào)易,而邊陲政府如果默認(rèn)這些不利貿(mào)易,會損害其公信力。這在梅山也顯示出相似的跡象,梅山從村長、肖鎮(zhèn)長到上級領(lǐng)導(dǎo)眼里只有掙錢與發(fā)展,完全沒有起到政府部門應(yīng)該起到的公共協(xié)調(diào)作用。而最可怕的是,村民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也認(rèn)可這種稱得上斷子絕孫的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而那只不過是飲鴆止渴,會使得不平等加劇,因?yàn)榘l(fā)了財(cái)?shù)拇迕駮w出到縣城里,留下的是千瘡百孔、了無生氣的廢墟。當(dāng)下的開發(fā)無視后代的利益,顯然是一種短視行為。GDP作為第一指標(biāo)的生活是片面的生活,導(dǎo)致的后果不堪設(shè)想。
但絕大多數(shù)村民幾乎鬼迷心竅般希望恒通公司重啟項(xiàng)目,甚至那個身體已經(jīng)被毒素變異了的原村長畢富生,已經(jīng)成了一個讓人不敢靠近的“毒人”還不忘要“我”帶著大家一起接著開發(fā)。這種對于發(fā)展的欲望與生態(tài)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張力,也可見開發(fā)與保護(hù)之間的矛盾。是什么讓人陷入到這種非理智當(dāng)中的呢?沃勒斯坦指出,發(fā)展有兩層含義,一種是生物有機(jī)體意義上的新陳代謝、有機(jī)循環(huán);另一種則是算術(shù)法則上的“增多”,是線性和單調(diào)的投射,按照其自身邏輯,可以延伸至無限。但如果僅僅以物質(zhì)(化簡為金錢)的擁有數(shù)量來計(jì)算,無窮無盡的發(fā)展到盡頭實(shí)質(zhì)上不過是虛無,就像梅山那些在污染環(huán)境中死去的人,賬戶上擁有巨額金錢,但生命已經(jīng)不在。但謀求發(fā)展的背后動機(jī)與需求則在于內(nèi)部的更大平等和經(jīng)濟(jì)增長以趕上“先發(fā)地區(qū)”,在小說中體現(xiàn)為住在城里,但這一點(diǎn)其實(shí)在文本中很微弱,因?yàn)閺那楣?jié)來看,并沒有顯示出有了錢之后,村民的生活過得更好,而是恰恰相反。發(fā)展本身內(nèi)在的訴求在于更多與更平等兩個基本理念,沃勒斯坦批判的是資本主義的片面發(fā)展模式,但是放置到小說中來看,發(fā)展究竟是指路的明燈還是幻象卻顯得奇怪的吊詭。因?yàn)榇迕窕旧隙际菍幙蔂奚h(huán)境乃至健康,也要發(fā)展的,這無疑是一種最終走上絕路的幻象。
小說沒有給村民的發(fā)展狂熱原因以強(qiáng)有力的說明,而 “我”卻是眾人皆醉唯我獨(dú)醒。這從資本的逐利本性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yàn)椤拔摇痹谛≌f中成了一個有著長遠(yuǎn)關(guān)懷的良心商人,甚至為此不惜觸犯股東、犧牲公司的利益。這在現(xiàn)實(shí)的功利邏輯中是講不通的,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我”實(shí)際上成了一個理想主義人格。促使“我”改變的除了由于造成村民死亡帶來的道德與良心譴責(zé)之外,最主要的是爺爺?shù)幕貞涗浰鶐淼慕逃c教訓(xùn)。小說情節(jié)的驅(qū)動力只有從這個方面理解才能構(gòu)成合理性的進(jìn)展線索:歷史照進(jìn)現(xiàn)實(shí),歷史中的經(jīng)驗(yàn)反襯出現(xiàn)實(shí)中過度與無節(jié)制開發(fā)的恐怖與邪惡,歷史上梅山的美好景色也召喚著重回青山綠水的沖動,歷史里屢經(jīng)戕傷而終究再次獲得生機(jī)的生態(tài)循環(huán)也預(yù)示了如果封山保養(yǎng),可能會迎來新一輪綠色的希望。
歷史在這中間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那就是需要將梅山被遮蔽的歷史打撈出來,給予更多人以啟示與教育,這可能比暫時的經(jīng)濟(jì)訴求更有長遠(yuǎn)的價(jià)值。最終,“我”重啟了梅山項(xiàng)目,但不是開采礦產(chǎn),而是綠色發(fā)展。為了促成項(xiàng)目的成功,“我”不惜給鎮(zhèn)里交“空稅”。這一切無疑是違反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企業(yè)運(yùn)轉(zhuǎn)規(guī)則的,身在其中的“我”和秘書雨晴都意識到,這樣做可能不出一年恒通公司就會破產(chǎn),但是“我”依然樂觀地一意孤行。小說在這里顯示出了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返梅山》雖然是現(xiàn)實(shí)題材,并且在表現(xiàn)手法上也基本上是寫實(shí)主義,但根底里卻是浪漫主義的。因?yàn)槿宋锏男袨閯訖C(jī)其實(shí)并不具備很強(qiáng)的說服力,“我”的舉動完全是憑著個人的道德感與犧牲精神的驅(qū)使,這并不具備普遍性。必須深刻揭示出村民急切發(fā)展的欲望根源,解決既有所發(fā)展又能環(huán)保健康的出路問題,這就需要更廣范圍內(nèi)政治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解釋。歷史的教育與教訓(xùn)這一維度原本應(yīng)該起到很好的補(bǔ)充作用,乃至作為整個情節(jié)根本性的推動力,但是這方面的著力仍然顯得不足。所以這是一個無法結(jié)尾的小說,因?yàn)樽髡邿o法在這種僵局中提出切實(shí)的解決之道,只能匆忙結(jié)束。不過,小說家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提出問題,至于解決問題的道路,有待于小說的警示與提醒所帶來的更多人的思考與行動。
責(zé)任編輯 哈 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