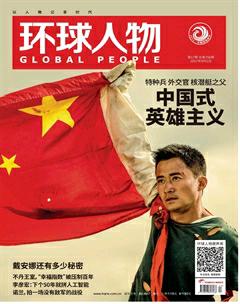郭柯,用真實超越悲悼
她們是另一種“返璞歸真”,不是從轟轟烈烈走向平靜,
而是從莫大的羞恥中上路,堅持走到最后。
會有一天,影院門口立起類似安檢門一樣的機器,觀眾經過此門,就會進入一種局部的無知狀態,業已記錄在大腦皮層上的、關于即將觀看的影片的信息將被擦除。他落座,眼前的人物與畫面都是第一次看到,他從零開始了解一個故事……直到離開影院,之前的記憶才會恢復,就像把寄存的瓶裝水取回手中。
會有這一天的——以今天的人對“逼真體驗”之追求,這種神奇技術早晚會出現。這也許正是郭柯想要的吧?觀眾走進《二十二》的放映現場時大腦里所帶的東西,那些來自媒體的描繪、來自個人印象和成見的東西,是他的大敵。紀錄片,尤其像《二十二》這樣的紀錄片,是最抵觸“前知識”的——慰安婦是一個近乎“國人至此,脫帽致哀”的題材;而老齡,又是頂頂無趣的人生階段。
老太太在片中的敘說,都像是為尚有一看的價值而辯解。冷酷的投資人是這個時代的上帝:觀眾憑什么來觀看老年慰安婦?能得到什么回報?他們的結論是,這部片子必須拍得痛徹心扉!必須讓人飆淚——悲悼的眼淚是最大的價值。你郭柯既然要拍,就得考慮賣。
好在郭柯有自己的堅持。
觀眾先看到人,她們的皺紋,她們佝僂的身子、囁嚅的嘴巴,她們作為老年人的行為特征——不斷重復同一個動作等。然后隨著影片推進,才慢慢了解到老人們難以啟齒的過去,在背影里看出另一層涵義,在聽到她們“不提了,不提了”的口頭語時,心中升起共情。
這才是我們認知世界和他人的正常順序,也是郭柯所希望的。而不是倒過來,像在藥鋪抓藥一樣,先問明白性能、療效、服用禁忌,再買回去自己吃。盡管郭柯必須向媒體妥協,沒有媒體,沒有那些排片、做海報、勾星評分的人,《二十二》想流入輿論的信息池都困難;但他又沒有妥協:片子結束于雪地中的葬禮——連一個預示著希望、新生、未來的畫面,一種撫慰人心的刻意,都沒有。
但就是這樣的結尾,讓影片產生了一種撫慰的力量。它似乎在說:你看,就連有過如此可怕經歷的女人,如今也終于活到平靜的晚年了……這是另一種“返璞歸真”,不是從轟轟烈烈走向平靜,而是從莫大的羞恥中上路,堅持走到最后。她們用寂靜的、私人的力量來抵抗觀眾“前知識”中儲存的那些大是非、大榮辱,為此,郭柯棄絕了一切“賣”的手段,如煽情的音樂、歷史影像等。老人把自己交給了他的鏡頭,他也對得起她們所犧牲的隱私。
得為郭柯慶幸,為票房上的意外斬獲。堅持的東西有了回報,對尚存樸素理想的電影人,是一種安慰。就連扭曲已久的“為了嘲諷看電影”的習慣,似乎都被糾正,而眼淚則出人意料地讓位于間或發生的會心一笑。22位慰安婦,到拍完時還剩8位,郭柯的片子讓人們超越了預期之中的悲悼。數字不重要,你我也都會死,可是你已如阿爾貝·加繆曾說的那樣,從他人身上“看到了正確的東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