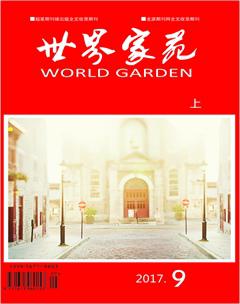鄉土文化傳承、延續的內動力
商婧媛
《論集體記憶》一書是奠定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關于記憶的社會學研究上重要地位的經典之作,縱然在當今看來書中的某些內容和觀點也存在瑕疵。但是,當人們需要撰寫有關記憶方面的文章時,仍是不可避免的細讀此書,其在記憶的社會學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由畢然、郭金華翻譯的這本書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編是記憶的社會框架,第二編是研究《新約》空間基礎結構的《福音書中圣地的傳奇地形學》的結論部分。哈布瓦赫提出了"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體和社會階級的環境中,過去是如何被記住的。摒棄了當時在歐洲流行的對記憶的幾種心理學解釋之后,他指出所有對個人回憶的討論必須考慮到親屬、社區、宗教、政治組織、社會階級和民族等社會制度的影響。為了證明自己的核心論點,他還指出,在穩定的社區生活中每個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記憶與秘密,而且這只向自己的成員揭示,這種"家庭記憶"并不只是個人記憶的組合。通觀此書,個體與群體的集體記憶情結是文化得以傳承、延續的重要紐帶,下面筆者將結合田野調查個案談一下對此書的些許感想。
(一)夢與記憶意象。在第一編的序言中,作者通過引用一個小姑娘失去記憶的事例,意在表達當我們處于新加入的社會中,為了恢復這些不確定、不完全的記憶,就必須至少向他出示有關的圖像,才能暫時重建他已脫離的群體和環境。反觀我們自己的記憶,正是當我們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們提及一些事情時,對之的記憶才會最大限度的涌入我們的腦海。(p68)大多數情況下,我之所以回憶,正是因為別人刺激了我;他們的記憶幫助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借助了他們的記憶。至少,在這些情況下,記憶的喚起并無神秘之處可言。(p69)這種以“圖像”、“話語”作為引子構建的記憶空間是我們在努力的通過這些現實事象來逐步激發的。每個人都會做夢,在夢中,我們感覺發生的事情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可是當我們醒來時,卻發現,這終究是夢。“如果純粹的個體心理希望找到一塊凈土,在那里,意識與世隔絕,形單影只,那就是夜間生活,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這樣一塊凈土。”(p74)從這里來看,個體貌似脫離了群體之后,它所產生的意象也幾乎完全脫離了社會表征系統,僅僅成為可構成各種意象組合的原材料。作者認為,夢建立在自身的基礎之上,而我們的記憶依靠的是我們的同伴,是社會記憶的宏大框架。(p75)這種社會記憶的框架的構建區分了夢和記憶的不同,但是細而觀之,我們不禁要問,建立在自身基礎上的夢,夢的機理源于現實群體生活;依靠同伴產生的記憶,同樣源于群體,對于同處在社會記憶的框架之中的元素,應該作何區分?答案或許在后面我們可以找到:個體與群體的互動,促成了集體記憶的傳承、延續。藕池村主要的經濟來源是農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因素,當地的板栗種植是其特色產業之一,奇怪的是當地并不種植藕,但是村名卻叫藕池,關于藕池的村名來源,當地有種藕如何不成活的傳說,但最后還是叫了藕池。如果我們把藕池的傳說看作是鄉民的“夢”的話,回歸現實之中,這是否是鄉民集體記憶的延續呢?不論種不種藕,有記憶的框架存在,群體的記憶生活就能繼續下去。
(二)語言與記憶。沒有記憶能夠在生活于社會中的人們用來確定和恢復其記憶的框架之外存在。言語的習俗構成了集體記憶最基本同時又是最穩定的框架。然而,這個框架又是相當松散的,因為它并不包括那些稍顯復雜的記憶,而只保留下了我們的表征中一些孤立的細節和不連續的要素。(p80)通過言語的表述與溝通,在建構了集體記憶的同時,也打開了個體與群體交流的一扇窗。鄉民自有他們的集體記憶方式,我們至始至終都是一個旁觀者。
(三)對過去的重建。作者在這一章節中提出,社會通過賦予老人保存過去痕跡的功能,鼓勵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仍擁有的精神能量都貢獻出來,用以進行回憶。(p85)在藕池村的田野調查中,我們小組選擇訪談的對象多為6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對于過去的記憶以及所釋放的能量遠非我們所能估計的。在訪談馬延恒老人時,通過短暫的交流和溝通獲取了老人的信任并促使老人打開了話匣子之后,他對于藕池村以前玩龍燈請水的習俗敘述的非常細致,乃至我們甚至有些懷疑被他帶到了當時龍燈請水儀式的現場。當然,作為親歷者,老人對于此習俗的詳細敘述是對他過去記憶痕跡的最大釋放。
(四)記憶的定位以及家庭的集體記憶。為什么我們經常感到大家的記憶具有相似性呢?作者在文中做了解讀,并不是因為幾個記憶彼此相似,他們才被同時記起,而是由于同一群體對他們感興趣,能夠同時會一起它們,所以才彼此相似。在藕池村的村落記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點就是玩龍燈時唱大戲。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不止一位訪談對象對我們提及了唱大戲的情景,“玩龍燈,唱大戲”這一特殊的民俗語境在鄉民的集體記憶中表現的淋漓盡致。被訪談人張興貴以及其他的兩位被訪談者在與筆者的交談中,提到玩龍燈唱大戲這一事象時,他們三人可以通過眼神的互動以及語言的交流對于唱大戲的曲目、地點等記憶內容闡釋的較為到位,這便是對記憶的定位起到了作用。也就是說,我們把記憶定位在藕池村民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發生在他們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再者,群體自身也有記憶的能力,比如說家庭以及其他任何的群體,都是有記憶的。家庭記憶有它自身生存的土壤,我們作為民俗工作者要做的就是能夠從這些記憶土壤中吸取養分。被訪談人下藕池村村民馬奶奶是寄居在女兒家的,已經年過80歲的高齡,但身體還算不錯,思維也較為清晰。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一開始溝通的幾個問題都碰了壁,問到如何過春節、清明節等問題時,老人多是以“老封建”的話語來回應,但是她明明卻還裹過腳,文化水平也并不是很高,這并不契合她所應當存有的記憶特征。當然,在場的還有她的女兒,正在用洗衣機洗衣服,恰好洗衣機壞了需要修理,筆者就順便充當了“修理工”的角色,在不經意中,她的女兒透漏出了她們一家人都信奉基督的信息。
(五)宗教的集體記憶與社會階級及其傳統。作者指出,盡管宗教記憶試圖超離世俗社會,但它也和每一種集體記憶一樣,遵循著同樣的法則:它不是在保存過去,而是借助過去留下的物質遺跡、儀式、經文和傳統,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會方面的資料,也就是說,現在重構了過去。(p200)宗教的集體記憶對藕池村的鄉民而言,也遵循著同樣的路徑,由六個自然村組成的藕池村,村中有相當比例的民眾信仰基督教,而且信教的人數與傳播的廣度亦有不斷蔓延之勢。鄉民有自己的神圣空間,他們在維護自身神圣空間的基礎上也在傳承、延續著他們的集體記憶。
“昨日的社會凝視著反射在過去之鏡中的自身影像,沉思默想,不能自拔,除非漸漸地,在同一面鏡子里映現出了其他的影像。也許這些影像不太清楚,人們也不大熟悉,但是,它們卻為那個社會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也許藕池人的集體記憶情結投射出了這樣一種記憶的框架:村落中日常生活中的習俗契合了鄉土社會和諧發展的方方面面,反觀之,豐富多彩的村落習俗及其蘊含的飽滿的集體記憶情結也成為了鄉土文化得以傳承、延續的內動力,它為我們呈現的是,小小的藕池,濃濃的記憶,厚厚的文化。
被訪談人:張興貴,男,57歲,初中文化水平。訪談人:張興宇、周明霞。訪談時間:2011年10月25日上午。訪談地點:下藕池村閻海武家門口
被訪談人:馬奶奶,女,80歲。訪談人:周明霞、張興宇。訪談時間:2011年10月24日上午。訪談地點:馬奶奶家中。
(作者單位:魯西南民俗博物館)